反思游学热潮:哲学视野中的成长
成长不只是父母和学校关心的实践问题,也不止是放弃理想与坚持理想的二选一。哲学家从各自的问题意识出发,同样会论及成长和教育问题,甚至将其视为自身哲学的关键环节。
为了给理想的城邦培养合格的卫士,柏拉图提出了一套文化审查方案。康德则秉承自己的批判哲学,提出了理性成长的三个阶段:独断论、怀疑论与批判理性。他认为,成长是勇敢面对应然与实然的裂隙,生活中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旅行是成长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近年来的“海外游学热”不仅常常是变相的购物玩耍,更对成长有害无益。
把诗人赶出城邦
哲学家对成长和教育问题的关注,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对话录《理想国》。在第二卷的后半部分,对话录的主角苏格拉底,探讨了年轻人应当接受什么样的教育问题。这种良善教育的心理学前提是:“凡事开头最重要,特别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它塑成什么型式,就能塑成什么型式。”
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方针就是要教孩子走正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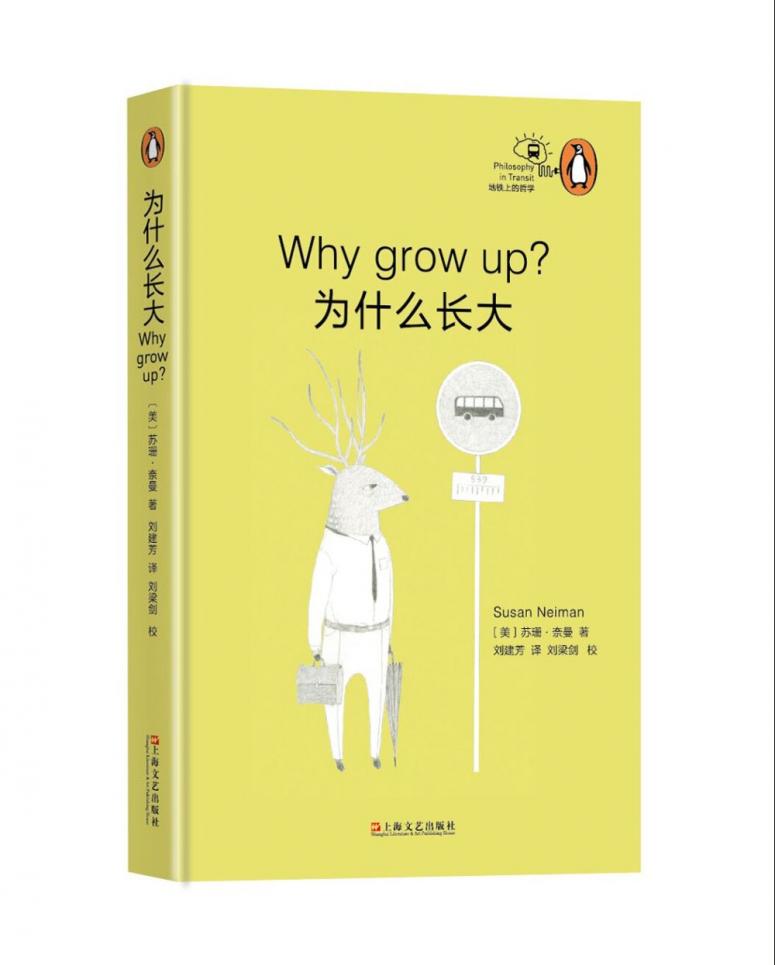
他要对童话故事进行审查。古希腊神话绝非只有真善美,故事的版本也有许多。在诗人赫西俄德的著作《神谱》中,世界最初产生的是混沌,接着是大地女神盖亚,盖亚的长子是天神乌兰诺斯。盖亚与乌兰诺斯交合,生下了众多子女,其中克洛诺斯“是大地盖亚所有子女中最小但最可怕的一个,他憎恨他那性欲旺盛的父亲。”
克洛诺斯反对父亲的起因,是母亲的不满。她将儿子们召集起来反抗父亲,其中唯有克洛诺斯慨然应允。他用母亲给的镰刀,割下了父亲的生殖器,成为新一代的神王。然而,克洛诺斯的暴虐不亚于父亲。他强娶了姐姐瑞亚,并在得知自己必将被子女推翻后,将所有儿女都吞下肚子。瑞亚心下悲怆,想办法将小儿子宙斯交托给自己的母亲盖亚。宙斯也不负众望,长大之后用计谋解救了父亲腹中的兄弟姐妹,打倒父亲。
这些充斥着乱伦与暴力的传说,有着深厚的根源与阐述空间。单纯用“人就是喜欢这些血腥低俗的东西”,是无法解释其旺盛生命力的。古希腊人不会机械地效仿神祇的做法,就像绝大部分《侠盗猎车手》的玩家不会拿着刀上街砍人一样。这段神话中显然能看出自然现象的起源,乌兰诺斯是天的人格化,盖亚是地的人格化。从凡人的伦理而言,乌兰诺斯与盖亚是母子相奸,但究其本源,不过是天地结合,化生万物的朴素道理。
但是,神话的表层情节中毕竟蕴含着父与子、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关系。在古希腊神王三代的传说中,权力的基础完全是暴力与强制,权力交替是青年人打倒老年人,举事的起因是老年人统治暴虐,青年人渴望权力。
《理想国》第一卷中的色拉叙马霍斯,对此给出了清晰有力的表述:正义是强者的利益。他说:“平常人犯了错误,查出来之后,不但要受罚,而且名誉扫地,被人家认为大逆不道……但是,那些不但掠夺人民的钱财,而且剥夺人民的身体和自由的人,不但没有恶名,反而被认为有福。受他们统治的人是这么说,所有听到他们干那些不正义勾当的人也是这么说。”
色拉叙马霍斯生平不详,这个名字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勇敢的斗士”,正符合他在《理想国》中的形象,一个年少气盛的诡辩者。即便是今天,色拉叙马霍斯这一类的言论也具有相当的市场。为了反击,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开始了对正义城邦的建构。
柏拉图的理想国由三种人组成:统治者、卫士、劳动者。统治者的德性是智慧,能够对城邦各项事务做出最好的决断,也就是常说的“哲人王”。平民只应当参与生产活动,供给衣食。卫士是军人,既要守护城邦不受外敌攻灭,也要维护城邦内的秩序。三者各安其位,便是正义。
开头讲到的柏拉图教育观,正是针对卫士阶层的。卫士阶层的教育有着明确目标,“培养美德”。接着,柏拉图简要勾勒了美德教育的两条宗旨:神必须是善的,不能做坏事,也不能是坏事的原因;神不能任意变形,也不能说谎,而必须始终如一。
在之后的篇章中,柏拉图也不吝笔墨,详细探讨了培养儿童过程中的种种细节,甚至连听什么调式的音乐也不放过。简言之,不能听靡靡之音,只能听古朴刚劲、奋发向上的作品。于是,柏拉图主张将不符合规范的诗人和音乐家赶出城邦。这一点在20世纪引来了无数高举“言论自由”、“艺术自由”旗帜的抨击,但也许他们和柏拉图讲的并不是一件事。
柏拉图对儿童心理学显然是不太关注的。正如美国哲学家苏珊·奈曼(Susan Neiman)在《为什么长大》一书中所说:“柏拉图之所以关注这些细节,不是因为他关心孩子,或者关心孩子会长成怎样的大人;他所关心的,更多的是城邦的发展,而不是城邦中的个体。”政治直接插入了古典哲学的成长观。
在柏拉图之后和卢梭之前的两千年中,很少有哲学家这样用心地关注教育问题,或许也与这种态度有关。重要的是宇宙秩序和对应的人间秩序,成长就是人成为秩序规定的样子,教育只是实现成长的辅助和强制手段。而按照今天的理解,成长必然涉及探索未知和内在的不确定性。

Susan Neiman
我们不知道,更不应该规定一名新生儿的未来。儿童不是未完成、缩小版或劣质版的成年人。自从人文主义以来,我们已经逐渐将这种成长观视为理所应当。但是,即便在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视野中,成长也从来不仅仅是成长,而是其哲学观念的重要环节。在这一点上,古典哲学家的遗产并未失落。
勇敢去认识!
作为启蒙运动的集大成者,康德对成长的看法远比古典哲学家更积极。他着眼于人的理性的发展。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人的成长分成了三个阶段:幼年的独断论阶段、青年的怀疑论阶段、成年的批判阶段。
首先要注意的是,康德所说的幼年、青年和成年并非生理概念。与性器官的发育不同,人不会在某个特定的年龄段自然进入理性的下一个阶段。事实上,这三种理性模式在大部分自然人的一生中都会运用。
电影《后会无期》中的一句台词,体现了独断论与怀疑论的区分: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康德说:“独断论就是纯粹理性没有预先批判它自己的能力。”独断论并非单纯的固执己见,面对明显的反面证据依然坚持自己的错误看法。相反,在某种意义上,独断论可以是一种相当幸运和幸福的状态。
如果成长环境不是特别恶劣的话,小孩子眼中的世界是充满着惊奇的,别人教授的原则和自己发现的道理,都显得非常真实。所谓童言无忌,并不仅仅是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行事没有理性;有时反而是孩子在刻板地运用心中的原则,以为现实与原则是同一的。随着知道的原则越来越多,孩子眼中的世界也就愈发宽广和规则。
显然,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儿童。在康德看来,曾统治德国哲学家半个多世纪的莱布尼茨思想就是独断论。正如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赵林所说,莱布尼茨认为“只要我们的理性能力提高到一定的水平……完全依据矛盾律从天赋的观念和原则中推演出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
但是,哪怕是受到了最好保护的孩子,美好的独断论阶段往往也不会持续太久。少年们很快会注意到,世界并不是它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教师、父母、媒体曾经为孩子的世界提供了认识的基础与依据,但孩子终将发现,这些权威人物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样无所不能,无所不知。
于是,怀疑论就自然产生了,代表着少年意识到了生命的不确定性。前一节讲到的色拉叙马霍斯就是一种比较粗浅和容易理解的怀疑论。事实上,按照康德的标准来衡量,大部分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只是处于遵循惯例的蒙昧状态,在少数运用理性的时间里也是在独断论与怀疑论之间徘徊打转。
在康德看来,真正的成熟标志是对理性的批判运用。“(理性的)第三步属于成熟了的、成年的判断力……怀疑论就是人类理性的一个歇息地,在这里人类理性能够思索自己的独断历程,勾画自己所处的区域,以便能够以更多的可靠性来进一步选择自己的道路,但它并不是固定居留地处所。”
乍看上去,这是一个相当浅白乃至无聊的教训。人不能叛逆一辈子,要成熟起来去面对大人的生活了。按照这样理解的话,成长就是一道选择题,坚持理想还是放弃理想,要独断论还是怀疑论?
康德对成长提出的要求更高:长大需要超越这道选择题。用苏珊·奈曼的话说,“彻底放弃理想远比遭受希望破灭的痛苦要好得多;直面深度腐朽的现实比沉湎于幻想要勇敢得多。”这才是康德那句著名的口号“勇敢去认识!”(Sapere aude)的真实内涵。
康德一生既没有离开故乡,也没有生育子女。大概也不会有人把《纯粹理性批判》当作育儿书来读,但他的成长观念早已贯穿于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的思想和实践中。美国心理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于1958年提出了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他将人的道德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以个人利弊为规范的前习俗期、维护人际和谐与权威的习俗期、形成普遍伦理原则的后习俗期。
尽管柯尔伯格的具体阶段与康德存在差异,但两人的划分依据是一致的。成长在于超越前一个阶段的局限性,实现理性的展开,在不确定的现实经验中不断寻求更高的确定性。
旅行与成长
柏拉图与康德眼中的成长大相径庭。柏拉图着眼于共同体的正义,个体成长是一个从属性和工具性的问题。这种观念在今人看起来或许有些封闭和刻板,但其实从未远去,也不应该脱离我们的视野。康德的视线转向内在,启蒙思想家对自我的挖掘与探索是古典哲学家远远不及的,但他们得出的结论也远远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乐观。理性不是阳光,不是只要摘取外在的迷信遮蔽,就会自动照亮每一个人和整个社会。
至少在理念层面,培养而非扼杀孩子的求知欲和表达,鼓励年轻人探寻和发现自我,是一个当代的共识。另外,成长也不是一个在18岁或者步入工作岗位后就戛然而止的过程。那么,除了课堂教学以外,成长还有哪些关键的要素呢?
一个要素是旅行。法国哲学家、教育小说《爱弥儿》的作者卢梭认为,旅行是成年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爱弥儿的学习计划中包括在欧洲大陆游历两年,要以徒步为主,学习各地的语言,考察各地的生活。
这种游学曾经盛行于20世纪前的欧洲大学,也与今天大学里的游学项目有一些相似性,但这种相似性仅仅停留于表面。卢梭对游学有着明确的目标:“仅仅是在不同的国家漫游是不够的,必须知道该怎么旅行……任何一个人,要是他只看见过一个民族的人,便不能说他了解人类,而只能说他了解曾经同他生活过的那些人。”
但是,不管是青年人的大学交换项目,还是一般意义上的旅游乃至旅居,都很少能达到卢梭的目标。在指导教师和导游的安排和带领下,人即使到了外国,也基本是躲在一个甚至比家乡还要严密的茧里。
学生和游客周围仿佛有一道空气墙,墙内是安插好的布景以及其他学生或游客。墙外并非现实世界,而只是一片虚无。组织得比较好的旅行团会努力将空气墙的范围做得足够大,里面的布景足够多,还会在墙面刷上足够逼真的壁画,让游客不会注意到自己所处的状况。差一些的旅行团则连这些装修工作都省了,让游客直面外面的虚无,比如80元游览桂州的购物旅行团。
旅行与哲学一样,应该让人“找不着北”(维特根斯坦语)。旅行本应是一个搁置在故乡的财富与地位,被抛到一个陌生、危险环境中努力求生和适应的机会。在某种意义上,旅行能让我们回到童年。
在火车、轮船、飞机普及化之前,上面描述的旅行不是特殊的理想情形,而是普遍的客观状态。用一个不精确的夸张讲法,在17世纪的欧洲,城墙以外的世界就像今天的亚马逊丛林或撒哈拉沙漠一样危险。当时的旅行者之所以要重构自己的信念,不是因为对文化多样性的向往,而是出于生存的必要。
但是,沉湎于一个早已逝去的时代并无益处,也非必要。旅行之所以能促进成长,不在于增加谈资和单纯的经历,而是因为它逼迫我们充分发挥理性。正如康德在《何为启蒙?》一文中所说:“如果有一本书照顾我的理解力,一位牧师照顾我的良心,一位医生规定我的饮食,我丝毫不用自己费劲。只要我能付钱,我就不需要思考,别人会帮我打理一切事物。”这段话出现在18世纪的德国杂志上,但与我们的体验并不遥远。
游学项目常常标榜“文化体验”、“开拓眼界”。且不说这些活动往往是挂羊头卖狗肉,比如“英式下午茶体验”和“牛津大学书店游”,即便是真正的听课乃至做研究,也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做着和在本校同样的事情,甚至会因此变得更加骄傲,仿佛去了一趟巴黎、牛津和海德堡便高人一等,连原本庸俗的观点都变得更加正确了。诚如卢梭所说,这样的游学“跑遍了整个的欧洲……仍然是没有看到任何一样可能使他们感到兴趣的东西,没有学到任何一样可能对他们有用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