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美国的白尾鹿
野鹿是英国平民翻身的希望,是自由的象征,是文明的灰色地带,是猎人、农民与印第安人矛盾的渊薮,也是西进运动真正的开路先锋。鹿许下了劳动致富的承诺,吸引着英国移民远跨重洋。
但是,野鹿不是绵羊,不能画地为牢,难以界定产权。猎人跟随着鹿的脚步,满不在乎地跨越人为划定的田产边界,乃至啸聚山林,与印第安人逐鹿边疆,直到总督最终决定用枪炮送来文明。
《天生狂野》从动物的视角出发,讲述了“野外”对北美殖民进程、社会制度与民族品格的重要影响。
去美洲,顿顿吃鹿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牛排大豪斯”。
1617年圣诞节刚过,你16岁了。你从小在英格兰西海岸的海港布里斯托尔长大,现在是时候思考未来的活计了。你面前有三份工作。
一是在城里找个师傅做学徒,好处是方便回家。但城里太拥挤了,一年到头,不知道放了多长时间的熏肉都吃不上几次。
二是跑纽芬兰的远洋渔船,鳕鱼和比目鱼管够,但半年时间都在船上,据说味道比鱼市还大。
所以,最吸引你的是第三个选项:弗吉尼亚移民项目。虽然你掏不起船票钱,那边前些年闹过好几次断粮,但你听说现在情况已经好多了,有不少波兰和德国的技工都过去了。
约翰·史密斯船长(John Smith),差不多十年前做过弗吉尼亚移民点的负责人。“新英格兰”这个名字,就是他给起的。前年,他故地重游,将经历写成了小册子《新英格兰状况》,里面有一首诗:“与其节俭度日、自降身价,不如花费一点时间去那尚未开垦的花园,去感受新英格兰的风貌,富裕丰饶在等着我们去整理自然的硕果;今天的美好预示着来日的希望,去那富饶的王国,修复时间和傲慢带来的衰朽吧。广阔的西部犹胜英格兰血脉已经占有的土地。”
诗人的文采当然是很好的,但整本书里最说到你心坎里的一句话是:“森林河湖为所有喜欢打猎的人提供了充足的猎物,还有野兽可供狩猎。”在英格兰,本就不多的森林早就被开垦成了放羊的草地,为海峡对岸的纺织作坊供应原料。残留的少数林地,几乎全被划为国王和贵族的私产。
鹿肉在英格兰是肉中上品。而在天高林阔、空气清新的新大陆,鹿肉不仅不是稀罕物,简直泛滥成灾。史密斯船长说,一个礼拜干三天就能吃饱饭,其他时间拿来钓鱼猎鹿,等有些积蓄了,再开个兽皮铺子,讨个媳妇。这样的神仙日子,给个男爵都不换。
400年前英国小伙的移民美梦,就做到这里吧。从哥伦布的年代至今,“人均资源量多”是北美洲一以贯之的招牌,而至少在20世纪初之前,兽肉都是资源丰饶的核心意象之一。19世纪中期,一位移民纽约的意大利移民在家信里写得非常直白:“老家一年三顿肉,美国一天三顿肉。”
除了刻在DNA里的蛋白质渴望以外,新大陆野生动物资源还有着更深层的意义。当时,英格兰已经是一个土地高度开发,乃至于过度开发的区域了。17世纪末,英格兰森林覆盖率仅有8%左右,与20世纪初的中国水平相当。狼早在16世纪初便绝迹英伦,熊、野猪、猞猁消失得更早,剩下来的野鹿、狐狸、野兔被圈在贵族的猎场中。
有一系列专门法律,旨在“保护王室园林和贵族私苑免遭人民侵犯或者说亵渎”。换句话说,英国的所有动物都是有主的,要么是贵族的玩物,要么是家畜。于是,新大陆的无主野鹿,俨然是自由平等的象征。
正如《天生狂野》中所说:“殖民宣传家们开始将两件事联系起来:一件是无主、待开发的野外生物,一件是每个新边疆都会有的自由观念,这种观念有敉平阶级的作用……野外生物标定了英属美洲边疆作为自由之地的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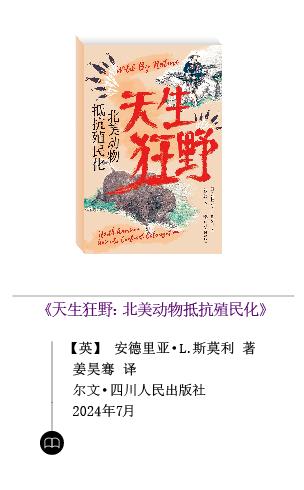
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主张,人天生就有享用天生万物的权利,通过对土地、矿产、野兽施加劳动,公共的自然权利转化为私有的财产权。在那个时代的英格兰乃至整个欧洲,洛克的产权论基本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因为早在几百年前,其他人就用锄犁或刀剑的“劳动”建立了财产权。普通人若想亲身实践这个化公为私的过程,新大陆似乎就是完美的场所。
18世纪末,美国作家吉尔伯特·伊姆利(Gilbert Imlay)为新大陆的野生动物献上一曲讴歌:“它们无忧无虑地漫游,俨然是这里的主人。天啊!多么自由,多么迷人啊。”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欧洲移民者的心之所向与自我认知。
不过,他们没有考虑野生动物自己的想法和行为。
鹿与猎鹿人的协同迁徙
野生动物的直接反抗,是无力的。哪怕是漫山遍野的狼,对殖民者人身构成的威胁也相当有限。不过,为了保护家畜,官员和居民都热衷于灭狼。建立农场的第一步,往往是将狼赶走。在这个意义上,狼与灭狼的博弈结果,规定了产权的边界。
从16世纪开始,北美各地政府屡屡出台悬赏猎狼政策,甚至由此创造出了一个有套利空间的狼头市场。专业的猎狼人会钻政策空子,在赏金低的县或偏远山区打狼,然后带到赏金高的县去兑换赏金。一些猎人为了做长久生意,还会放过产仔的母狼。尽管如此,灭狼事业的进展相当顺利。到了18世纪,狼在美国东海岸就基本绝迹了,灭狼潮有效维护了农场主和牧场主的生产环境。
狼并不会威胁英国移民固有的财产观念。虽然英国是海权国家,但英国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观念与大陆文明的农民并无区别,同样秉承“谁开垦,谁占有”的基本原则。打狼与清除林木、设立边界、引入牲畜、改良土壤、排出积水一样,都是传统开垦活动的组成部分。
鹿则对传统财产观产生了实质性的威胁。在某种意义上,野鹿是自由北美社会的灯塔与象征。早在11世纪,征服者威廉就在英格兰颁布《森林法》,规定偷猎者应处以刺眼或阉割之刑。北美东部的白尾鹿不仅数量多,在殖民者到来之前估计有2000万至3000万头,而且就连“贫困的劳工”也有完全的猎鹿自由。考虑到鹿对吸引移民的重要作用,殖民当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承认自由猎鹿的权利。
然而,看似无穷无尽的鹿群,短短百年间就被挥霍一空。到了18世纪中期,北美东海岸几乎看不见野鹿了,屡屡出台的禁猎令也于事无补。鹿不是凭空消失了,而是渐次向更偏远的深山转移。鹿走了,市场还在,需求还在,于是催生了一个迥异于定居农民的群体——商业猎鹿人。
白尾鹿是一种容易受惊的胆小动物,善于逃跑和隐匿。另一方面,鹿也有领地意识,不过主要是为了提前规划行动和逃跑路线。这就意味着,鹿的“领地”面积大,下至600市亩,最大可达45000亩,且边界模糊。
相应地,猎鹿人的“领地”也有类似的性质。猎鹿人的看家本领,是长时间观察和追踪,摸清鹿的活动路线与范围。鹿的行动路线很容易穿越多座农场的法定界线,猎人也不得不跟着越界。鹿会在猎人的逼迫下远遁,猎人也必须跟着转移。
可想而知,猎鹿人很快就成为了定居社会眼中的闲散无赖、官府眼中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前面提到的伊姆利说过,打猎“对勤奋的人来说,更多的是在浪费时间,而无真实益处”,这句评语有真实之处。因为猎鹿人的财富确实不多,不动产更是几乎没有。
但这主要反映了定居者的偏见。在他们看来,农耕才是本业,打猎实为浪荡。正如斯莫利所说:“英式殖民的特点是合法占有,有序定居,合理开垦,这种观念容不得鹿和以猎鹿为生的人。”进入19世纪后,打猎自由基本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私有猎场。
文明的开路先锋
鹿和猎鹿人带来的矛盾,不仅限于殖民社会内部,更引发了与原住民的接连冲突。
肯塔基州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中部,弗吉尼亚州以西,在18世纪是人烟稀少的边疆地带。其原住民有肖尼族、切罗基族等,欧裔人口则多为散居猎人,俨然是一片“天然大鹿苑”。印第安人和欧裔猎鹿人一样,没有明确的产权界定。这不仅仅是缺乏权利意识的问题,也是狩猎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内在要求。毕竟,白尾鹿是一种无法圈养的动物。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拨猎人之间没有矛盾。事实上,双方的猎场纠纷时有发生,为殖民当局带来了极大困扰。官员秉承息事宁人的态度,在1763年以条约形式进行了划界,但并未奏效。6年后,肖尼族突袭一伙欧裔猎人,宣称此地是“印第安人的牧场,所有动物和毛皮都属于我们”。1774年,弗吉尼亚总督率军征讨肖尼族,迫使其投降,放弃肯塔基和周围猎场的使用权。
这是殖民者蚕食印第安领土的一种常见模式。东方沿海鹿群西迁,猎人随之跟进,与原住民杂居,形成所谓的边疆。流动粗放的狩猎生活方式,意味着各方都没有绝对的权利,由此不断产生摩擦。起初,殖民当局通常会试着划定边界,但缺乏强制执行的能力和意愿。纠纷与冲突继续存在,不断发酵,直到官员在某一刻终于下定决心,要将问题彻底解决。被解决的一方总是印第安人。
但在这个过程中,边疆猎人也不是完全的胜利者。因为印第安人主动或被动离开后,殖民当局下一步要处理的就是农民与猎人的矛盾。这时,政府总是偏向定居者一方的。边疆猎人要么融入定居社会,要么继续向西迁徙,开启新的轮回。
19世纪末,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特纳(Frederick J. Turner)提出了边疆假说,主张美国制度的扩张:“越过一个大陆,征服广大的原野,在发展进程的每一个阶段将边疆的原始经济政治环境改造成复杂的城市生活。”
按照他的看法,边疆居民是将文明传遍美洲大陆的先锋。但如果去考察野生动物与各类人群的关系,我们分明会发现,特纳的视角不免偏颇。
边疆居民并没有传播文明的动机,反而是在逃避私有产权和法权的束缚。在定居者眼中,边疆居民“过无知、闲散、贫困的猎人生活……粗犷,近乎野人”。边疆居民是被鹿牵着鼻子走的,鹿的习性决定了猎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塑造了美国的边疆品格。或许,拒绝被殖民的野鹿,才是西进运动真正的开路先锋。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