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外交官的诞生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近代史得出的惨痛教训。但革新不仅仅是开放的态度,更是一门技术。
晚清首位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西方社会持全面赞同的态度,以儒家理想中的三代圣贤喻之。但由于通讯落后、组织粗糙、角色错位,他不是一名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官。这些缺陷在继任者曾纪泽身上得到了显著提升,他率领的使团为中法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
《远西旅人》强调,晚清外交人员乃至中国社会与西方的“遭遇”,不仅有接纳和排斥两种选项,更是逐渐化被动为主动,系统性地调动传统知识,从而对西方形成全新的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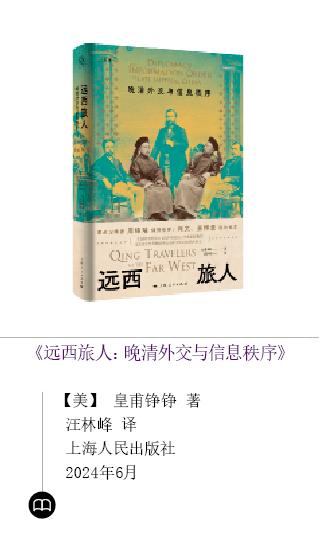
三代在西方
1877年年底,清朝的外交中枢——总理衙门,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波。当时的清朝驻英公使,是湘军宿将郭嵩焘。但在左宗棠剿灭阿古柏在即的当口,他竟然擅自对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表示:“中国获地西域,力实不及经营,徒废兵力而已。”威妥玛旋即将消息报告给了本国和中国政府。
有想法是一回事,在朝廷决策与谈判的关键节点发表这种言论,则不免失当。另外,同年5月,郭嵩焘在伦敦未经朝廷批准,就擅自接待了白彦虎派往英国交涉的特使。白彦虎与阿古柏一样是新疆叛军的首领,后窜入俄国境内。于是,朝中对郭嵩焘的批判此起彼伏,比如李鸿章女婿、清流干将张佩纶,指责郭嵩焘“太暗钝,易于受绐”。换句话说,缺乏政治敏感性。这为他一年后被召回埋下了伏笔。
郭嵩焘当年力劝曾国藩出山,在征讨太平军期间提议建立水军,后来做过署理广东巡抚,绝非颟顸之辈。他自作主张的一个客观因素,是信息沟通不畅。当年年初,英国要求中国承认阿古柏政权,成为清朝“藩国”,李鸿章对此大致认可。但左宗棠4月进兵以来连战连捷,阿古柏于5月暴毙,南疆收复在望,清廷的态度随之大变。郭嵩焘的看法则停留在年初,心中难免会觉得,战时可能会迁延日久。
另一个因素,是郭嵩焘本人的抱负,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传声筒。朝廷是1874年征召他的,当时他已经辞官七年,一直在湖南老家讲学,着力于研究明末王夫之、黄宗羲之论。朝廷的出发点相当具体,就是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
当时,日本借口琉球漂流民被台湾原住民杀害一事,悍然入侵台湾南部。清廷在事后复盘中认为,若有常驻日本公使,或许就能预先阻挡,免生事端。进一步讲,这种做法还可以推广到欧美各国,防患于未然。郭嵩焘先前任官期间就颇有远见,深入意识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由此获得了李鸿章等洋务派人士的赏识,他们向执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大力举荐。
但正如皇甫铮铮所说,郭嵩焘坚持:“认为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真正办法在于社会改革,在于教育、富民与赋民以权,而不是帮助王朝延续一个日益衰退的合法性统治。”他心里觉得,设立驻外使节只是细枝末节。但太后亲自恳请他出山,他实在不得已,只能接下这个“尽人可以差遣”的琐事。
于是,他出使期间花费大量精力去研究西方制度。他在1878年出席了国际法协会的年会。他旁听了英国国会辩论,在与后来担任驻德公使的李凤苞交流时表示,西方虽然没有三代圣王,但朝廷与臣民共治,亦可实现善政,而且比依赖君主德才的三代之治更加可靠持久。由此可见他的儒学底蕴。
早在出国之前,他就对中国的前景充满悲观:“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三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为自秦汉以来四千年流极败坏之久,累积之深,非是不能有成也。”在郭嵩焘的思想世界中,是古非今与开眼看世界不仅不相违背,反而是一体两面。1878年被提前召回之后,他没有回京述职,而是回故乡开设书院,宣传禁烟运动,希图改良地方,保育民气。
在这个意义上,郭嵩焘一直是一位可敬的理想主义者。无论身在何方,他的终极追求总是革新中国之“道”。而在朝廷同僚看来,他应当是一位宣扬中土教化,训导西洋蛮夷的使臣,就算不像苏武那样悲壮,也应有班超出使西域的手段。但这绝非郭嵩焘之志向。这种角色的错位,或许是郭嵩焘黯然归国的内部动因。
电报取代日记
外交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是国家利益,而在外交语境下,国家利益不仅涉及本国执政者的意图,更要考虑他国行为。站在郭嵩焘任职的时间点来看,他对西方列强行为逻辑的判断有一定现实依据。在他看来:“洋人蚕食诸国,阳开阴阖以收其利,从无攻城略地之事。”
早期西方侵略的主要诉求,是贸易特权、开辟商埠、设立外交代表。但从1870年代开始,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琉球、朝鲜、越南、缅甸等藩属国,先后被“文明”的英法与后起的日本侵占。此时,再要国人相信西方犹胜三代,那就很困难了。在1870年代至1880年代,驻欧公使基本不再公开谈论西方的制度与道德,而且忌讳国内刊物未经授权登载自己对“外国之政教风俗”的看法,甚至会要求总理衙门加以查禁。
与此同时,电报的地位大大提升,北京朝廷与驻外使馆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信息交流网络。在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期间,总理衙门与各国使馆之间往来电报达2000余封。电报提升了中央集权的上限。
在此之前,使馆成员向总理衙门汇报的主要载体是日记。使节将自己的见闻、感想和行为记录下来,发回国内。日记比较自由宽泛。1868年,旗人志刚跟随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出洋考察,写下的日记后来以《初使泰西记》之名出版。志刚虽为满人,却精研儒学,将考察视为格物致知的良机。于是,他的日记中记述了蒸汽机、电池、煤气灯、自来水的原理。他还以是否有益于国计民生为准则,区分了机器的良莠。从中颇能窥见晚清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郭嵩焘的日记《使西纪程》同样林林总总,有撞船事故的风波,有凯撒征战史,也有听来的时人看法。他在新加坡听英国官员说,苏门答腊岛西北角的亚齐原为荷兰属地,荷兰人强横压迫,导致岛民叛乱,最终推翻苏丹。《使西纪程》出版后,荷兰公使提出抗议,认为郭嵩焘偏听偏信英国人,污蔑荷兰。
对民间人士和后世史家来说,出使日记是很好的读物。《使西纪程》尽管遭到各方反对,以致被官方毁版,但民间版本一直在流传,到了20世纪更是广受认可。但从信息渠道的角度来看,日记时效性差,内容散乱,近乎随感,容易泄露和引发争议,朝廷与使馆也无从协调沟通。在这种情况下,使馆成员无法及时了解到国内情况,中枢决策也难以贯彻到驻外使团。
电报克服了以上缺陷。在曾纪泽这样忠于朝廷、洞悉全球形势、公正可信、具有政治头脑的外交家手中,电报让外交人员发挥了前所未有的能动性。1880年代初、中法战争前后的外交交涉,就是典型案例。
1881年,法国决定远征越南北部。为了挫败法国的企图,曾纪泽率领使馆人员翻译新闻报道和法国制作的越南地图,反复向总理衙门表明,法国国内对开战一事并非全然支持。他鼓励越南国王与英、美、日、德签订条约。他建议朝廷表现中国对越南的实质性影响,以对抗1874年签订的《第二次西贡条约》,后者规定越南受法国保护。
曾纪泽的努力不仅大大减轻了总理衙门的负担,也对中法交涉发挥了及时且积极的影响。最后,就连法国人也意识到曾纪泽的分量,要求清廷更换一名比较温和的公使。正如《远西旅人》中评价外交官角色:“越来越将自己视为政策制定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以电报为主的交流通信篇幅渐渐变长且更加频繁,更富有战略意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交流越频繁就越好。曾纪泽确实向国内提供了大量极具价值的资料,但他与中国其他驻外公使、他国政府和外交人员的往来信函,并未全部呈交总理衙门,而是存放在各自的使馆中,而且总理衙门对电报做不到完全管控。这就给他留出了宝贵的自由活动空间。
例如,他在一份英国杂志上撰文驳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宣称中国并非“不思改进”的暗弱之国,而是“先睡后醒”,中国将和平崛起,不会威胁世界。这种文章不同于郭嵩焘那样的煌煌大言,特点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驳斥列国兴起的反华新思潮。有趣的是,这篇文章是曾纪泽的自作主张。假如他事事都要向总理衙门申请,恐怕他无法有效承担起清政府代言人先驱的角色了。
改革不仅需要开放
对于近代以来的中西交往史,一个通行的模型是“冲击-回应”理论。该理论肇始于20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为了解释原始文明的出现,他以“阴阳”为比喻。
阴是社会平稳的状态,发展到极点就是故步自封,比如人类持续了几十万年的狩猎采集社会。变化来自于挑战,对原始社会来说,这种挑战常常来自自然环境。应对挑战的过程就是“阳”,社会进入创造与变化的时期,或者说阴阳共济,将外来的挑战者纳入自身。
按照这种看法,自然经济与专制皇权在晚清走到了尽头,挑战者是西方列强,中国社会应战的核心就是接纳挑战者的因素。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革新派战胜改革派,传统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的历程。
于是,郭嵩焘顺理成章获得高度评价。他看惯了晚晴中国的腐朽落后,对西方社会与制度怀有理想化的看法,向往以议会政治、万国公法为代表的现代秩序,极力表现出开放接纳的态度。但从他担任驻英公使的实际成效来看,他不是一位成功的外交官。
就算西方文明果真掌握了新时代的天命,但从欧美列强在中国的实际作为来看,外交官更紧要的任务是寻找西方各路势力之间的缝隙,用有利于中国的方式来解释东西方文明体系的差异,从而为中国谋利益。这项任务不仅需要开放的心态,更需要电报等通讯技术、专业化的信息处理人才、适当的中外舆论调节。这些便是《远西旅人》要讲述的“信息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