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大运河与徽商托起的帝国江都
摘要:公元1795年,一部名为《扬州画舫录》的小书开始悄然流行。这是戏曲作家李斗撰写的一部关于扬州社会的著作,书中内容乃是清代鼎盛时期扬州繁华的实录,举凡风土人物、山川园林、寺庙道观、市肆文物,乃至城市区划、城池水系沿革……林林总总,无所不备。字里行间,如同一座繁华大都市的文字庆典,可谓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
说起扬州,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历史上数不清的文人和画家,旅人和商贾;可能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抑或“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毫无疑问,作为一座中国古代著名的大都会,扬州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岁月感怀和充满诗意的浪漫想象。
的确,扬州这个名字很容易带来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联想。尽管一千个人眼中就会有一千个不同的扬州,尽管现实中的扬州与文学中的扬州其实是两个颇有不同的地理概念。但我们依然坚执地相信,扬州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那座城市,这里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文化,有优美的传说,有传奇的故事……总而言之,扬州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富贵温柔之乡,烟柳繁华之地。
历史上的扬州曾经有过两个黄金时代,一个是公元六世纪至九世纪的隋唐时期;另一个是公元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明清时期——自公元前五世纪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修筑扬州的起源邗城之日起,扬州一直处在两条重要商路交汇处的战略位置,而扬州人则一直生活在一个江河、湖泊和运河交错的世界。
吴王夫差使得扬州在政治地理上的地位得到确立,隋炀帝则将扬州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大都市,一直到唐末,扬州都牢牢地占据着国际贸易中心的位置,被后人称作“八世纪中国的宝石”。
当然,同样是因为地处交通要冲,每每遇到王朝之间的战争,扬州总会成为可能的军事目标,屡经兴衰就成为扬州的必然命运;而每次衰落必能迅速崛起,也成就了扬州作为一座国际大都市的内涵与气质。诚如姚文田所言:“维扬为南北要津,自秦汉以后,迄于戎马之冲,其郡县之废兴,疆域之分并,视他郡特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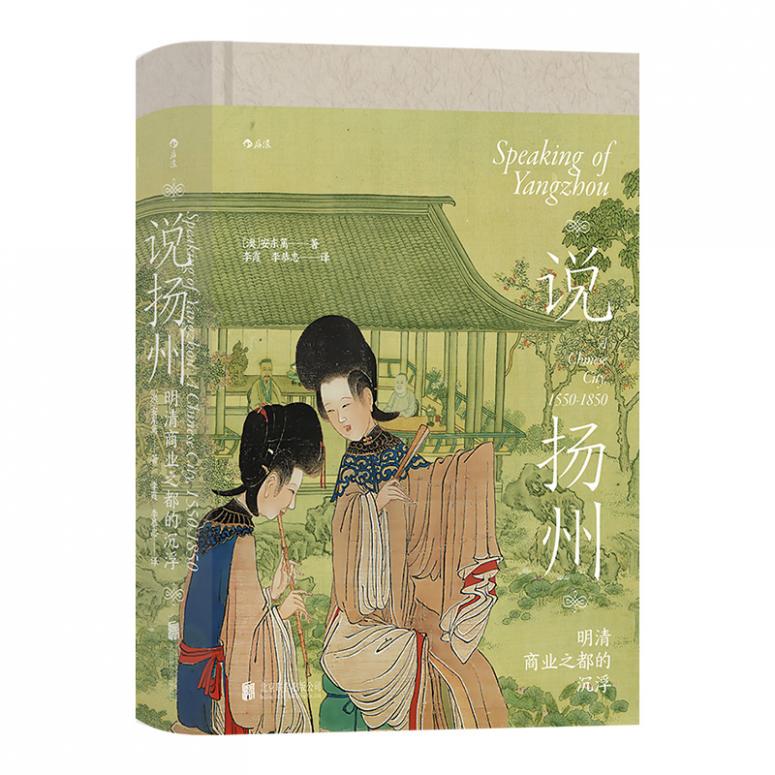
《说扬州:明清商业之都的沉浮》【澳大利亚】安东篱 著李霞、李恭忠 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5月
如果说明清之前,扬州的繁华得益于它的南北交通的枢纽位置和食盐专卖的盐税收入,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大运河与盐税依然决定着扬州的经济命脉。事实上,扬州一直处于古代中国城市化较低的地区,即便是在扬州最为繁荣的时期,扬州周边的农民也仍旧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扬州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人为结构的获益者,这个结构的存在取决于国家政策——扬州兴于这个结构,后来也同样衰于这个结构。
澳大利亚著名学者安东篱的《说扬州》,是一部关于扬州的“传记”。既然是传记,那就不单是讲述一座城的历史和一座城的生平事迹,同时也描绘这座城的“某种想象出来的人格特征,乃至获得某种性别,并成为自身历史中的一个角色”。
在安东篱的笔下,扬州已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转化为一个有血有肉、形神兼备的生命形体。作者的笔触不仅深入到扬州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而且对扬州建城的历史渊源、地理特征、城市性格的塑造,以及扬州的土著与移民、士人与商人、盐政与水利、城市与乡村等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与剖析。其中既有着宏观的学术性的阐释和论证,也不乏一些具体而微的鲜活、生动的细节,可谓优劣俱见,巨细靡遗,并重点再现了明清以来,扬州的城市面貌和时代精神。
大运河:沟通古代中国南北交通的命脉
扬州在中国历史文化版图中,始终占有着很高的地位,自不待言,这种地位来自财富、权力和文化活动的结合,而这些首先是与大运河的贯通分不开的。
从一定程度上说,扬州的地理位置其实并不优越,甚至还有些尴尬:它位于苏北的相对贫困地区,却拥有巨额财富;它远离帝国的贸易中心,却成为这个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它本地并无商人,却成为徽商的地盘;它地处江北,却以江南文化的面目示人……
安东篱将十七世纪的扬州与同时期欧洲的威尼斯相提并论,因为它们都能使人想起许多艺术家、文人、富商巨贾以及水道的形象,想起一种非常迷人的城市环境,一段充满色彩和浪漫的过去。这种比较并无不妥,它能够使陌生的环境变得熟悉,让欧洲人获得有关扬州的更为直观的印象。
扬州的悖论其实根植于它的历史之中,自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之日起,扬州就注定被纳入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黄金水道系统,并随着中国政治格局的变迁而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扬州地域上的不足因运河得到了弥补,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地理因素,自此成为这座城市历史发展的关键,并且不论在任何时候,帝国南方和北方关系的好坏,都将直接促进或者阻碍扬州的成长。
缘于运河之便,扬州成为东南漕运的咽喉之地,在以北方为重心的时代,控制或者利用南方的资源,扬州是为沟通南北交通的命脉所在。缘于江淮地带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所谓“守江必守淮”,每当帝国处于分裂的阶段,地处南北交通枢纽位置的扬州都会成为交战双方争夺的焦点。比如,三国时期的魏国之于吴国,南北朝时期的魏国之于齐国,五代时期的南唐之于后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宋朝之于金朝,以及南明小朝廷之于满清……而扬州也总是屡经兴废,但尽管如此,它作为中国古代商业重镇的地位却从未动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上的扬州之所以能够保持千年的繁华,大运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扬州的兴盛原本即是与大运河沟通南北交通密切相关的。在很大程度上,大运河决定着古代扬州的政治命脉和经济命脉:大运河兴,扬州兴;大运河衰,扬州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扬州既与大运河同生共长,自然也与大运河兴衰相连。
盐业贸易:决定扬州财富的基础
大运河对于扬州的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而食盐专卖对于扬州也同样意义重大,因为扬州不仅占据着大运河沟通南北中国的枢纽位置,也同样占据着南北中国盐业贸易的枢纽位置。
作为所有政府专卖行业中最富庶的两淮盐业的行政中心,扬州在远距离贸易网络中,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盐业贸易不仅是帝制晚期扬州财富的基础,同时也直接促成了徽商的崛起,如果将扬州的盐业贸易置于明清两代的历史背景之下,这一点就会看得更加清晰。
十六世纪中后期至十九世纪前期的扬州,是一座商业氛围极其浓厚的城市。因为有着漕粮、盐政和税关口岸的地位,扬州吸引着远近各色人等前来淘金。蜂拥而至的八方来客,使得扬州成为一个冒险家的乐园。
事实上,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在扬州经营食盐贸易的徽商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些来自徽州的流寓和移民家族既是扬州经济的主导势力,亦逐渐构成了扬州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修文庙,建园林,资助贫生,赞襄婴育……积极参与各项公益活动,努力打造徽商的正面形象,他们与流寓官员和文人汇合在一起,使得商人与士大夫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进而跃升为一个殊新的社会阶层。
食盐贸易既然是扬州主要的财富来源,对扬州的社会结构和城市文化自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尽管明清两代存在易代的断裂,而且扬州亦曾经过了“扬州十日”的惨烈伤害,但随着清朝的复兴,易代的裂痕迅速弥合,明清之间的食盐贸易和徽商传统依然显示出非常明显的连续性。
到了十八世纪,由盐业贸易成就的徽商进入鼎盛时期,正像陈去病所概括的那样:“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这些徽商以盐业贸易为纽带结合在一起,累积下大量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他们与同时流寓于扬州的文人和艺术家打成一片,与高层官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在他们共同的推动下,扬州的物质繁荣和文化繁荣达到了顶峰。
十八世纪扬州的著名画家方世庶有一幅《九日行庵文讌》的画作,描绘的是徽商马氏兄弟在其行庵中举办的一次聚会。参加者包括盐商、商绅、文人、画家,以及流寓官员,他们在同一座园林里参加文学活动,形象地说明了彼时扬州社会的许多方面,诸如“精英的构成;精英成员们喜欢的消遣活动;城市空间被投入园林建造;精心构筑的高雅文化风气,有助于抵消低俗、贪婪这种陈旧的商人形象”,如此等等,为我们思考扬州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扬州精英阶层的真实面貌提供了一个直观的标尺。
扬州梦的终结与回忆扬州梦时代的开始
公元1795年,一部名为《扬州画舫录》的小书开始悄然流行。这是戏曲作家李斗撰写的一部关于扬州社会的著作,书中内容乃是清代鼎盛时期扬州繁华的实录,举凡风土人物、山川园林、寺庙道观、市肆文物,乃至城市区划、城池水系沿革……林林总总,无所不备。字里行间,如同一座繁华大都市的文字庆典,可谓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
《扬州画舫录》的问世,既标志着“扬州梦”的具体化,也意味着一个记录了扬州梦的时代的终结,以及一个即将回忆起扬州梦的时代的开始。书中罗列的众多的名人雅士和书院园林,无不宣示着扬州之于中国城市的重要地位;而“扬州学派”在科场上获得的成功,则标示着学术为扬州带来的荣耀。
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十八世纪的扬州其实已经埋下了衰败的种子,正是从这个世纪的开始,世界已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先是太平天国运动阻断了长江的航运,运河淤塞,漕运废止,盐政的变动和宏观格局的变化,使扬州失去了原有的优势;继而蒸汽船和铁道先后出现,最终夺走了扬州远距离的贸易伙伴,盐业贸易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而随着盐业贸易的衰落,扬州移民社会中的精英阶层纷纷逃离,商绅凋落殆尽,扬州就此风光不再,终于回归为江北腹地的一座普通城市。
诚如安东篱所言,《扬州画舫录》深刻影响了后人看待十八世纪扬州的方式,而书中所描绘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场景,很容易使人陷入一种关于十八世纪扬州之繁荣的普遍观念之中。
扬州的历史其实更像是一个从鼎盛到衰落的故事,扬州的困境则象征着近代以来满清帝国的困境:曾经有过什么,它们现已不复存在。正像清代文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所写到的那样:“《画舫录》中人半死,倚虹园外柳如烟。抚今追昔,恍如一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