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与瘦马之外的明清扬州
摘要:扬州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丰富的文化联想:隋炀帝开凿运河、史可法壮烈殉国、奢靡无度的盐商、艳名远播的瘦马。而在宏大叙事与花边新闻之间,在方志、碑铭、诗画、古迹的角落里,还藏着一个准扬州土著朱自清口中的“好地方”。
扬州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丰富的文化联想:隋炀帝开凿运河、史可法壮烈殉国、奢靡无度的盐商、艳名远播的瘦马。而在宏大叙事与花边新闻之间,在方志、碑铭、诗画、古迹的角落里,还藏着一个准扬州土著朱自清口中的“好地方”。
专攻中国明清社会文化史的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Antonia Finnane),曾在1970年代末寻访扬州。她撰写的《说扬州》一书,从地方与空间视角出发,发掘和探究了明清时代扬州的微观结构,并剖析了扬州兴衰的深层制度逻辑。用她自己的话说,她要让扬州“获得某种想象出来的人格特征,乃至获得某种性别,并成为自身历史中的一个角色”。
一部城市传记
安东篱的书名,取自朱自清的同名散文。朱先生生于1898年,《说扬州》写于1934年。朱自清在开头写道:“自己从七岁到扬州,一住十三年,才出来念书。”因此,他有资格,也有意愿写一写自己看到的扬州。尽管朱先生在扬州生活了很久,但并不是一名扬州吹,对盛衰兴败看得很淡泊,也很明白。“现在盐务不行了,简直就算个‘没落儿’的小城。”
朱自清笔下的扬州,富有生活气息。对他来说,扬州早不见了传说中的“瘦马”,却是个不乏美食的地方,有高汤醇厚的面,有茶馆里五花八门的小吃,还有一种“烫干丝”的吃法。干丝就是切成丝的豆腐干,在彼时的北平就有“煮干丝”的菜品,应该就是今天饭店里常有的“大煮干丝”(也有写作“千丝”的)的早期朴素版本。它用高汤煮至入味,是一道正餐汤品。“烫干丝”则是一道清口的点心,干丝焯水后攒成圆锥形,拌入香油和酱油,再搁上虾米和笋丝即可。“说时迟,那时快,刚瞧着在切豆腐干,一眨眼已端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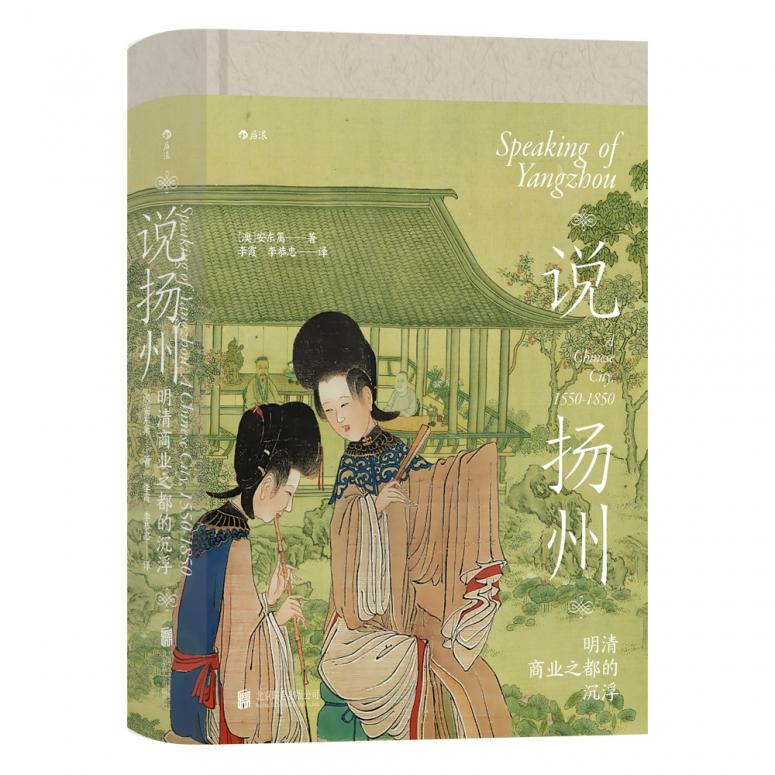
《说扬州:明清商业之都的沉浮》
不过,安东篱的着眼点却放在了文章的末尾。在《说扬州》的最后一段,朱自清说扬州城内外有许多古迹,“却很少有人留意;大家常去的只是史可法的‘梅花岭’罢了”。对平常读者来看,这段话大概类似于小红书上铺天盖地的“冷门景点推荐”。安东篱意识到,梅花岭与“很少有人留意”的古迹代表着宏大叙事与地方叙事的歧异。
梅花岭是扬州古城北门外的一座人造土丘,得名于岭上栽种的梅花。1645年,清兵攻破扬州,守城的南明尚书史可法宁死不降,去向不明,家人遂在梅花岭上设衣冠冢纪念。自此之后,不仅明朝遗民将梅花岭奉为圣地,就连乾隆皇帝都为史可法祠亲笔题写“褒慰忠魂”,宣扬封建忠君思想。
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更是撰写雄文《梅花岭记》,驳斥说史可法在城破时以法术遁走的怪论。“不知忠义者圣贤家法,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百年而后,予登岭上,与客述忠烈遗言,无不泪下如雨,想见当日围城光景,此即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
传统历史观中的扬州基本是一座忠义之城,其余则仅有瘦马名妓、画舫宴饮、盐商奢靡之类的花边内容,而且近代以来基本处于边缘地位。直到1970年代末,安东篱来到南京大学求学时发现:“中国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奇怪,我怎么会去研究扬州这样一个城市,因为它看上去远离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流。”
安东篱创作《说扬州》的目标,正是将镜头拉近,去考察明清两代扬州的城市布局、外围与延伸、不同的人群、财富的渊源、文化意识,以及最后的没落。因此,书中运用的资料类型相当多元,但这并不意味着《说扬州》是一本凌乱的漫谈。全书不乏穿针引线的明暗文脉,其中之一便是徽商。
徽商发源于安徽省南部的徽州府,尤其是歙县和休宁县。扬州是徽商重镇,徽州人在扬州的势力也远远大于本地人。在一幅绘制于乾隆八年(1743年)的扬州重阳节诗会画卷中,16名与会的高士中有9名徽州人,3名浙江人,湖南、湖北、陕西、苏州各1名,无一人的籍贯是扬州。这种状况并非特殊或个别。
事实上,徽州人不仅掌握着扬州的经济,更积极参与到城市建设与慈善事业中,重阳诗会这样的文化活动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甚至县志作者都颇有微词,写道:“如歙之程、汪、方、吴诸大姓,累世居扬,而终贯本籍者,尤不可胜数。若但以题名碑为据,而于历志相沿之旧,概行删去,且或载其父而遗其子,录其弟而外其兄,于情事不合,未便轻为附和也。”
从基层史学工作者的角度出发,由祖籍外地人士占据城市精英阶层的局面,确实很不利于开展工作。然而,与鱼米之乡江南相比,扬州的物产算不上丰富。扬州虽然是大运河邗沟段的起点,但也从来不是淮安、济宁、天津这样的漕运重镇,更比不上长江批发枢纽汉口。此外,扬州不仅不是首都,连省会都算不上。那么,扬州的财富渊源于何处呢?
盐商与盐场
热门古装悬疑剧《神探狄仁杰》中,有一个题为“漕渠魅影”的单元。武则天年间,有百年历史的地下武装组织“铁手团”,与扬州地方官员勾结,凿毁大运河上的盐船,人为制造盐荒之后,再把打捞上来的官盐私售牟利。这段故事像是把唐末黄巢,或者元末张士诚的行径嫁接到了盛唐。而且除了在乱世以外,靠盐致富的手段通常不会如此直白粗暴,但确实点出了扬州千年盛衰的关键:盐与官。
盐政兴,则扬州兴;盐政衰,则扬州衰。大量由盐船改造而来的画舫,正是这一规律的缩影。正如安东篱所说:“扬州是一个人为结构的获益者,这个结构的存在取决于国家的政策,只有善治才能确保其效率。”
扬州的财富来自淮盐。在明代初期,扬州只是一座平凡的小城,与南京、苏州、杭州不可同日而语,直到明朝立国百年之后的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北方边患贯穿明朝始终,无论是初期的大规模北伐,还是以守为主的中后期,边境都需要大批物资。按照朱元璋的设想,边防将士的口粮有屯田和开中两法。屯田就是士兵及其家属种粮自食,无奈土地贫瘠,产出有限;开中法是商人运粮到边境,换取朝廷颁发的售盐许可证(盐引),然后可以凭引购盐,贩盐营利。
借助产量巨大的盐场和贯通南北的运河,两淮地区的盐引成为了边境军粮最重要的交换媒介。当然,字面意义上的开中法非常繁杂,尤其是南粮北运这一环节。于是,商人用银两购买盐引,银两解运边境,边境就地购粮的“折色法”在成化之后逐渐成为主流。从此之后,盐商不再需要与边境直接发生联系,可以围绕盐引的购买、兑现、分租经营。
由于扬州坐落于运河畔,距离淮南盐场又比较近,于是自然成为了盐业帝国的枢纽。到了1617年,也就是努尔哈赤称帝的后一年,明军在萨尔浒惨败的前一年,明廷为鼓励盐引销售,推出名为“盐纲”的世袭版盐引,进一步增强了盐商的势力。
在明清易代的动荡年代,扬州既有史可法坚守不降之忠义,又有屠城十日之血案。但是,扬州不久便借助一套新的“人为结构”恢复了往日繁华,甚至更胜以往。与明朝不同,清廷无需将大量军粮投入到北方边境,但仍然需要两淮盐场的巨大利益。
清朝沿袭历代制度,将全国划分为多个盐区,食盐生产与流通由盐务官员负责,不得跨区销售。大部分盐区都只涵盖一或两个省的范围,但两淮盐区覆盖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大部与河南局部,几乎占据了川贵以外的整个长江流域加上淮河流域。两淮盐区的主管衙门,就设在扬州城内。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扬州与食盐的生产和流通息息相关。扬州经营的食盐主要产自江淮之间的沿海地带,大致覆盖了整个苏北海岸线。扬州距离最近的盐场也有100多公里。不仅如此,扬州甚至不是两淮盐区的批发中心,那是位于长江中游的汉口的定位。简单地说,扬州是一处“盐关”,盐起运时要在扬州纳税,检查有没有携带私盐,再就是举行祈福仪式。这一点更加表明,扬州兴于盐政,而非盐业。
除了占据全国收入约十分之一的盐税之外,盐商还会争相为军务水利捐款,名为“报效”。在康熙与乾隆历次南巡期间,盐商也会进献珍宝,甚至在私家园林中接待皇帝,换取“奉宸苑卿”之类的荣誉称号。安东篱对此做了精辟的概括:“皇帝的巡视创造了王朝与盐商之间的牢固纽带,产生了一种相互支持的制度。”
但是,扬州的繁华与盐工无关。北宋诗人张俞的名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也适用于盐工。康熙年间编纂的《两淮盐法志》中有一幅图,生动地展现了盐工的劳苦生活,图画表现的是名为煎盐的工艺。正中央是一个巨大的砖砌方灶,灶中是一名只穿短裤、肋骨突出的老年男子站在灶边,铲着掺杂着草木灰的食盐结块。灶旁的青年男子用手抓着短衫衣襟,好像在扇风的样子,还有一个小孩仰头看着长辈们劳作。画面右下角是另一个灶,灶中是盐水,一名女子负责搅拌,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坐在地上烧火。灶的四周有正着或斜着插进地面的树枝,撑起一片遮阳的草棚。
除了恶劣的工作环境,盐工被迫以低价向官府出售食盐。几千名盐工分得的收入,只及几百名盐商销售所得的五分之一。安东篱用“漏斗”来形容这种格局,每年几亿斤盐从漏斗的上方落下,出去时变成了数百万两银子。而且漏斗的密封性很好,银两基本全都落入了下面张着大嘴的盐商。
《说扬州》英文版发表于2004年,荣获2006年美国汉学界大奖约瑟夫·列文森图书奖。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濮德培(Peter C. Perdue)称赞作者“对扬州的社会史、环境史和文化史的广博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微观的视角,观察过去五个世纪里中国经历的重大变迁”。2007年,中华书局推出了中文第一版,今年由后浪出版公司推出了第二版,对旧版的若干翻译错误进行了订正,并补充了多幅彩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