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内外的婚姻与爱情
摘要:《之子于归》一书,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檀作文2007年系列讲座的讲稿合集,当时讲座的题目是“《诗经》中的婚姻与爱情”。作者一方面对周代的礼俗文化做了简要而恰切的介绍,以免造成误读,比如将《关雎》曲解为男青年水滨求爱;另一方面主张“介入性”阅读,也是将自己代入作品中的人物,体会和想象人物的情感世界。
《之子于归》一书,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檀作文2007年系列讲座的讲稿合集,当时讲座的题目是“《诗经》中的婚姻与爱情”。作者一方面对周代的礼俗文化做了简要而恰切的介绍,以免造成误读,比如将《关雎》曲解为男青年水滨求爱;另一方面主张“介入性”阅读,也是将自己代入作品中的人物,体会和想象人物的情感世界。
以《野有死麇》为例,作者探讨了《诗经》中的“镜头语言”与言外之意。除此之外,《诗经》在先秦时代的外交场上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正如孔夫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
谁是君子
《关雎》是《诗经》的第一首诗,中学课本里都学过。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一首君子追求淑女的情诗。一位公子听见水鸟的鸣叫,又看见一位漂亮的女孩子,想把她娶回家,想得连觉都睡不踏实。于是,公子向姑娘演奏音乐,逗她开心。
与一些充斥着生僻字的《诗经》篇目不同,《关雎》的字面意思不难看懂,只有“芼”字不认识。“荇菜”虽然不确定是什么植物,但也能猜到是一种水草。我代入的场景是小伙子在学校里的人工湖边对学妹一见钟情,打听到宿舍号后,就跑到楼底下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情非得已》。
唯一让我困惑的地方是,男子为什么要去采水草呢?荇菜是一种分布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水草,漂浮的圆形叶子形似睡莲,突出水面的茎秆末端开黄花,常用作家禽和家畜的饲料。那么,“参差荇菜”的三句复沓应该一方面是描述男子的劳作生产活动,一方面是形容女子摇曳生姿吧。如果是这样的话,男子的地位应该不高,那他怎么会用琴瑟钟鼓这样的贵族乐器呢?琴瑟倒还好说,钟是编钟,是若干沉重的青铜器按照次序挂在木架子上,是无法搬动的。因此,上一段中代入的生活场景肯定是有问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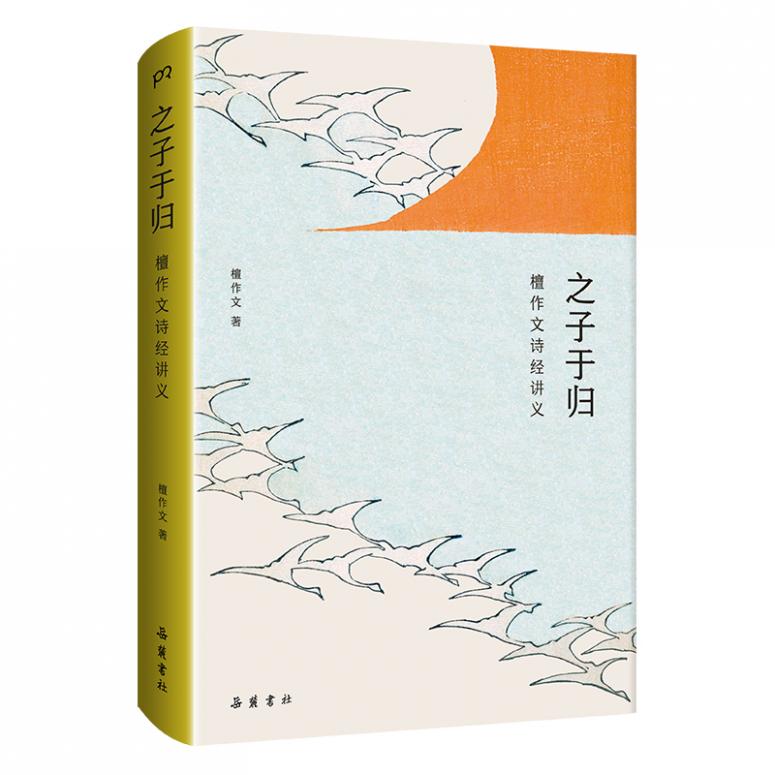
《之子于归:檀作文诗经讲义》檀作文 著浦睿文化·岳麓书社2022年6月
《之子于归》中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却合情合理的解读:《关雎》是天子之乐。也就是说,诗中所说的“君子”是周天子,“淑女”是王后,诗中场景也不是劳动人民的生产与交往,而是王室婚礼的步骤。
事实上,这种论断并非檀作文的别出心裁,而是传统《诗经》研究的通说。周代贵族女子结婚前要在官学接受三个月的培训。培训结束后会举办一场毕业典礼,其中一道程序就是新娘手持水草参与祭祀。在礼法森严的先秦,水草种类与身份等级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后妃采荇,诸侯夫人采蘩,大夫妻采蘋藻。”这样一来,解读《关雎》的基调便确定了下来。“琴瑟钟鼓”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几样东西本来就无需搬动,而是大婚助兴之用。
不过,我本来的印象也不算全错,因为《关雎》并不是枯燥刻板的流程教材。檀作文说得好:“《关雎》是想象之词,是用普通人的生活现实来虚拟和想象‘君子’和‘淑女’恋爱的过程和场景。”毕竟,王妃多为诸侯之女,婚前与未来的丈夫是无缘相见的,而在《关雎》中,两人却仿佛在河边相遇。通过压缩时间、空间与情感的距离,《关雎》为先结婚后恋爱的贵族男女绘制了一幅情意绵绵的爱情画卷。这便凸显了《诗经》熏陶教化的功能。
蒙太奇与走私爱情
当然,《诗经》中绝不缺乏平民婚恋的场景。“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这就是一个卖布的小伙子和卖丝的姑娘之间的故事。相比于《关雎》、《有女同车》这样注重礼仪的诗篇,《诗经》中的庶民情歌要生动得多,甚至会营造出电影般的氛围感。《野有死麇(jùn)》正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檀作文将这首诗的三段解读为两组镜头接一个动态场景。
第一组镜头发生在野外。男子用白色的茅草包裹一头死鹿,鹿大概是他亲手获取的猎物吧。紧接着,镜头切换到男女调情的场景:“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这是一种早期人类社会的常见习俗,至今仍有余绪。以生活在东北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族为例,在女方接受媒人的求婚后,男子要和媒人、母亲一起带着野猪肉去女方家里磕头行礼。
第二组镜头则仿佛是漫画定格。男子身边一侧是求亲用的野鹿,一侧是同样用白茅包裹的柴捆,这些柴要留到婚礼的时候用。届时,新郎要手执点燃的柴捆,牵着马去迎娶新娘。男子脑袋上冒出一个表示内心活动的气泡,气泡里是美得像玉一样的新娘。用檀作文的话说,这一段“类似于现代艺术批评常说的意识流、蒙太奇等手法”。
但全诗最有趣味的,无疑是第三段。“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檀作文给出的译文是:“轻轻来啊慢慢来,摸到围裙别乱来,别让大狗叫起来。”从口吻来看,这是女子在劝诫男子,地点应该是女子的家中。这个场景与前两组镜头不知隔了多久,但两人显然已经是干柴烈火。放在爱情电影里,这应该相当于女主人公闭着眼睛,男主人公的头缓缓俯下,四唇马上就要相接,然后画面一黑吧。在这样热烈的气氛中,想必看门的大狗也不至于不识趣吧。
在某种意义上,《将仲子兮》相当于把“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这两句挑出来,扩写成了同义反复的三段。每一段的大意都是:哥哥啊,不要翻墙来我家,免得碰坏了我家的果树,我倒不是吝啬财物,只是怕家人邻里说闲话呀。两首诗中的女子表面上是在规劝男子,却全无拒绝之意,反而满满是长相厮守的迫切愿望。换句话说,女子的意思是:“你可别让人发现了呀!”檀作文用“走私爱情”来概括《将仲子兮》的主旨,可以说是很精当了。
外交场上的赋诗言志
《诗经》有风雅颂三部,雅是宫廷宴饮的乐歌,颂是宗庙祭祀的配曲。而风据说是民歌,其中也有很大比重与婚姻恋爱有关,画面感也很强,因此似乎是比较通俗的。从来源来看,这是正确的,但从先秦时代的运用方式来看,即使是《诗经》中的各地民歌也发挥着更加严肃的作用。
有一年四月份,北方霸主晋国的执政韩起来到今天河南省中部的郑国,掌握郑国实权的六卿在都城郊外设宴款待韩起。韩起请六卿每人从《诗经》中选择一篇吟诵,“亦以知郑志”,也就是了解郑国的执政方针。
六卿依次赋诗,韩起一一应答。一场风雅而又严肃的对话就这样进行着。六卿之一的子齹(chuō)念了《野有蔓草》,诗中说道:“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从当时的场面来看,此诗当是赞扬韩起的风度,表达郑国愿与晋国长久友好之意。当然,两国关系不是“邂逅”,但韩起显然听懂了诗中的意蕴,于是回道,“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另一位郑卿子大叔则更加大胆,选择了《褰裳》。字面上,这首诗是一位姑娘对情郎的嗔怪与呼唤:“你要是想我,就过河来找我;你要是不想我,我难道就没有别人找吗(子不我思,豈无他人)?”韩起的应答颇值得玩味:“我这不是来了嘛,怎么敢劳烦你去找别人呢?”子大叔起身作揖。除了最后的告别之外,这是主宾应答之间唯一的起身动作。
韩起评论道:“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这段对话虽不至于剑拔弩张,但显然是在试探。至于试探的到底是什么,子大叔为什么要起身,韩起从中听出的是求救还是威胁,那就只能由历史学家去考辨了。
这段对话出自《左传·昭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526年,春秋已经进入末期。不到30年后,韩赵魏三家便攻灭智氏,预示着三家分晋的格局与战国时代的降临。而在韩起来访时,郑国早已不复春秋初期的风光,只能摇摆依附于晋、楚、齐这些大国之间。就在一个月前,韩起还向郑国索要玉环,幸亏被孔子称赞为“古之遗爱”的国相子产据理力争,才免于丧宝辱国。不过有趣的是,子产一上来就说,我并非轻慢晋国,对晋国也没有二心,我会始终如一地侍奉晋国。可见当时两国关系的基调。
但正是在这样一场大国执政与小国重臣的正式会面上,交谈的媒介竟然是《诗经》,而且是被孔子批判为“声淫”和“乱雅乐”的《郑风》,也就是郑国本地的民歌。不仅如此,赋诗言志的场景远非仅有这一例。据《海国图志》作者——清代文人魏源的统计,《左传》中列国宴饮赠答有70余条。六卿赋诗之前20年的七子赋诗也是一大盛会。来访郑国的晋国执政赵武,也就是戏文中大名鼎鼎的“赵氏孤儿”甚至从诗中推断出了赋诗者的结局。
正如檀作文所说:“《诗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当时外交的辞令……意思表达错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一个人掉脑袋事小,搞不好还会导致灭国。”这正是孔夫子“不学《诗》,无以言”的本意。
孔子不是让大家掉脑袋,更不是剥夺普罗大众说话的权利,而是强调外交场合的参与者必须熟读《诗经》,尤其是能够在恰当的场合中撷取恰当的词句,代表自己所属的氏族或国家表达恰当的意思。换句话说,《诗经》是贵族需要灵活熟练掌握的应酬素材库。
《诗经》中涉及贵族婚恋的作品,往往需要对历史文化背景有相当的了解。这种诗非得逐字逐句去查阅《毛诗序》、《礼记》、《说文解字》等典籍,再参考近现代学者的考据论辩,否则就连盲人摸象都算不上。对于这些诗,《之子于归》中给出了详实而易读的礼俗背景介绍,示范了解读《诗经》的正途。
但另一方面,《诗经》中也有许多篇章并无精微典故,望文生义也不至于曲解。不过,诗毕竟是凝练的,也未必是按照整齐划一的时间顺序。于是,檀作文会引导读者想象诗中描绘的画面,尤其是试着填补画面之间和画面以外发生的事。正如他在全书的结尾所说:“我们以俗世情怀,以心会心,突入古人的情感世界时,也更容易发现中国文学中固有的激情与尊严、浪漫与灵秀。”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