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透镜下的人类文明因子
摘要:他在耶路撒冷城内大肆夸耀自己的强大,还嘲笑罗马人:“夺取加利利的村庄都那么费劲,甚至有攻城器械在村庄围墙下被毁掉,就算给他们插上翅膀,他们也飞不过耶路撒冷的城墙。”在他的煽动下,奋锐党控制了耶路撒冷城。但是,起义军随即接连发生内讧。等到韦斯巴芗(Vespasian)将军兵临城下之际,耶路撒冷已经被内斗、倾轧和清洗所占据。
用作者沙洛姆·萨洛蒙·瓦尔德(Shalom Salomon Wald)自己的话说,写于2004年至2009年的《文明兴衰与犹太民族》,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实验”。
作为一名以色列智库专家,沙洛姆的目标是博采古今史家的理论思考,运用于犹太民族的数千年文明史,发掘包括政治领导力在内的核心文明驱动力。然而,这并不是一本为以色列人定制的文献综述。相反,书中探讨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具有普遍意义,又在具体历史的映照下折射出别具价值的思考。作者对“犹太人的贡献”与“对犹太文明的贡献”的辨析正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弱势者的领导艺术
公元70年,犹太人起义已有四年之久,曾两度击败进剿的罗马军队。在过去的历史上,犹太人曾遭受过众多外族的奴役,巴比伦人甚至在公元前587年毁掉了位于耶路撒冷的圣殿。但在第一圣殿毁灭70年后,第二圣殿便重建于耶路撒冷。
公元6年,耶路撒冷所在的犹太地区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奋锐党人之后便一直主张武力驱逐征服者。不久前,一个名叫约翰的人从基斯卡拉(Gischala)来到了耶路撒冷。基斯卡拉是犹太省北方加利利地区的一座小镇,是当地最后一座投降的犹太城镇,而约翰正是守城的领袖。
他在耶路撒冷城内大肆夸耀自己的强大,还嘲笑罗马人:“夺取加利利的村庄都那么费劲,甚至有攻城器械在村庄围墙下被毁掉,就算给他们插上翅膀,他们也飞不过耶路撒冷的城墙。”在他的煽动下,奋锐党控制了耶路撒冷城。但是,起义军随即接连发生内讧。等到韦斯巴芗(Vespasian)将军兵临城下之际,耶路撒冷已经被内斗、倾轧和清洗所占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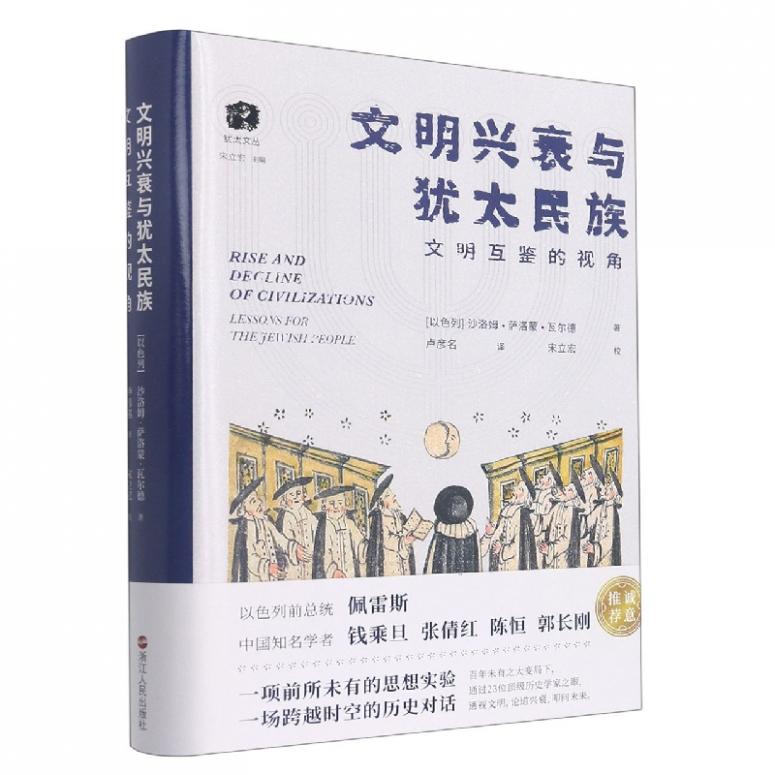
《文明兴衰与犹太民族:文明互鉴的视角》【以】沙洛姆•萨洛蒙•瓦尔德 著卢彦名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
耶路撒冷的命运已经注定,但犹太民族却因为一个戏剧性的事件而获得了转机。德高望重的拉比约哈南·本·扎卡伊(Yohanan ben Zakkai)藏在棺材里出城,面见韦斯巴芗。罗马统帅问约哈南想要什么,拉比回答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亚夫内(Yavneh)。我会去那里授徒,我会在那里祭祀,我会在那里履行神圣律法规定的一切义务。”刚过了两三天,罗马皇帝去世并传位于韦斯巴芗。韦斯巴芗回国即位,留下儿子围城,最终击破城墙,毁掉第二圣殿。
第三圣殿再也没有建立起来,犹太大流散拉开了序幕。从罗马人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次寻常的镇压行动,约哈南也只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但他对犹太人的历史意义远非尔尔。
在亚夫内,他颁行了大量教令,一个重要目标是为了在耶路撒冷城外维持原有的重要仪式,或者换个角度说,是将仪式活动与作为物理空间的耶路撒冷圣殿解绑。例如,犹太历的新年是七月初一,那一天要三次吹响羊角号。吹角原本仅限于耶路撒冷城内,约哈南则规定可以在所有犹太宗教法庭进行。
另如,犹太历的每个月始于新月升空,因此就要安排专人观察月相。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观月人必须到城内犹太公会大祭司的住处汇报。约哈南则规定,以后观月人只需到当地公会处报告即可。另外,新皈依者也不必向耶路撒冷圣殿奉献了。
作为一种极其重视严谨生活方式与祈祷仪式,而非停留于教义和圣书的宗教,约哈南的行动可谓意义非常。正因如此,沙洛姆说约哈南“也许是第一个能想象出没有圣殿的犹太教的人”。这或许体现了犹太人所谓的“适应能力”,但从奋锐党长达数十年的反抗来看,犹太人并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民族。
自从公元前20世纪的赫梯帝国开始,中东与近东便一直是帝国迭兴征伐的战场。犹太人本身不曾建立帝国,统御万民,但总归能在帝国的夹缝与更替之间求得生存。纵然一时覆亡,也有机会在旧奴役者本身被消灭之后放归故土。
然而,罗马帝国彻底抹杀了独立或半独立犹太政权的腾挪空间。不论奋锐党人是真想自己解放自己,还是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变化,他们都失算了。约哈南的选择虽然屈辱,但从他后来致力于调整犹太传统,以便适应新格局的情况来看,他确实是一名优秀的精神与政治领袖,为犹太民族之后上千年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中世纪欧洲,犹太人中不仅有银行家,也不乏优秀的政治家。这一事实常常被忽略。罗斯海姆的约瑟尔(Josel of Rosheim)出生于1480年,自从27岁时为遭到驱逐的犹太村民辩护开始,他终生致力于维护德意志地区犹太人的权利,直到74岁时骑马去海德堡(Heidelberg)为另一桩犹太人驱逐案辩护,死于途中为止。
他取得的成绩与查理五世皇帝的处境有关。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大公、西班牙国王与勃艮第伯爵,他统治着中欧与南欧的大片领土,也掌握着广大的美洲殖民地,揭开了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的帷幕。但新教改革与德意志诸侯的挑战让皇帝左支右绌,为了重振帝国权威,皇帝愿意授予犹太人特权,以获得其支持。约瑟尔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利用皇帝的需求和中世纪法律固有的机会,让犹太人成为直属皇帝的臣民,以此抵御地方统治者的迫害与剥削。
约瑟尔一生中的高光时刻,是1530年在奥格斯堡(Augsburg)召开的帝国会议。他不仅要为个别的犹太人迫害案辩护,更要在全帝国的国王、公爵和主教面前,以书面形式确认犹太人的权利。他援引自然法的原则,批驳“犹太人不适用于基督徒的道德与法律”的传统观点,并将申诉的主要方向设定在经济领域,尤其是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交易规范。这都体现了他灵活而富有创意的外交手腕。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约瑟尔类似于美国1950年代至1960年代民权运动中的律师。有趣的是,除了黑人自己以外,美国南方犹太人是民权运动中最积极的群体,犹太人律师和学生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流散时代犹太政治人物,沙洛姆给出了精当的概括:“他们的生平可以说明散居海外的领导人的机遇和对他们施加的限制,并显示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缺乏资源和强制手段的情况下是如何运用其权力的。”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民族,中国人未必能深切体会,甚至未必会欣赏这种“蒲苇之韧”。但如果将目光从国家政权层面外移或下探,泱泱大国的公民也不难看到约哈南与约瑟尔身上值得借鉴的领导艺术。
何为犹太人的贡献
《文明兴衰与犹太民族:文明互鉴的视角》的中文书名起得非常艺术,原本的书名则直白得多,意思是“文明兴衰对犹太民族的借鉴意义”。作者沙洛姆·萨洛蒙·瓦尔德,任职于耶路撒冷犹太民族研究所,是一名智库研究员。在导语中,他说这本书试图“将从通史中收集到的因素应用于犹太人的过去和现在……它提供了建议和假设,而不是对深入研究的总结”。更具体地说,作者考察了23名历史学家的观察或理论,从中归纳出文明兴衰的外在条件与内在驱动力,而本文前面讨论的政治领导力正是驱动力的一种。
乍看起来,《文明兴衰与犹太民族》或许像是一部大部头的文献综述,但只要稍读几章,读者便会发现全书一以贯之的旨归。不妨这样说,这本书介乎《资治通鉴》与《贞观政要》之间。因此,2007年至2014年担任以色列总统的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会为此书作序,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沙洛姆是一个江湖骗子式的国师,将犹太民族或以色列国当作唯一的考察对象。在探讨文化成就问题时,他提出了一个敏锐而尖锐的问题:“当我们谈到‘犹太人的贡献’时,我们是指作为一种文明或宗教的犹太教的贡献,还是犹太人个体偶然性所做的贡献?”
这本质上是一个普遍性的发问,“犹太人”可以替换成任何一个群体,比如“阿拉伯人”、“辉格党”,或“闽南人”。
一个很容易想到的回应,是基于对活动性质的区分。显然,一名拉比学者对犹太教义的阐发是对犹太文明的贡献,而一名犹太人小贩的销售额不算。奥地利籍犹太人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主要也属于对心理学的贡献,尽管犹太人身份或许对他的视角有一定的塑造作用。
但由于文化交融,判断有时也不是那么好下的。比如,11和12世纪的西班牙有一位名叫卡西米娜(Qasmina)的犹太女诗人。她有三首诗留存至今,其中一首颇有《诗经·召南·摽有梅》中的味道:“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一日,卡西米娜照镜时忽有所感,于是写道:“我看见一座果园,果子已经到了收获的时候。但我看不见园丁向果子伸出手。青春已逝,我独自等着一位我不愿说出姓名的人。”
她的诗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这是因为她生活的西班牙南部当时由穆斯林统治,阿拉伯文是通行的文学语言,当地的犹太人雅士也不例外。对漂泊四方的犹太人来说,交融本是常态。
17世纪荷兰籍犹太人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则提供了一个富有张力的案例。他是一名彻底的反叛者,24岁时就被逐出教门。在《神学政治论》中,他说出了一段在当时显然大逆不道的话:“摩西不是由欺骗,而是由于非凡的德性,深深地得到了一般人的倾服,以为他是超人,相信他是借神的灵感来说话与行事;但是,即使是他,也不能免于有人出怨言与对他有不好的看法。别的君主们是更不能免于此了。”
他的矛头不仅指向小小的荷兰犹太人社群,甚至不仅仅是犹太教的观念。既然《圣经》中领受十诫的先知摩西都不曾假借神的名义奴役众人,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又有什么资格妄言:“服从王权是《旧约》和《新约》中皆有的明证与严令。”
斯宾诺莎唯愿通过自然真理与哲学,追求真理。难怪英国历史学家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会在《激进启蒙》一书中,将斯宾诺莎称为“天启宗教、公认观念、传统、道德以及……神授政权之根基的首要挑战者”。
从斯宾诺莎之后,不愿为犹太民族做贡献的例子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