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明中的两种海洋
摘要:希罗多德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他6岁的时候,乘着大破波斯帝国之威,雅典确立了希腊霸权。他去世前6年,雅典与斯巴达争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在他去世时,埃及已经接受波斯统治长达百年。再过100年,年轻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踏上了征程,直到征服的兵锋止于今天主要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畔。换言之,希罗多德见到的是古埃及文明的末端。
农耕民族古埃及人看来,海洋与沙漠同样是坚不可破的屏障,直到入侵者的到来打破迷梦。而对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来说,海洋则是贸易通道与生命线。英国地理学家詹姆斯·费尔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在《地理与世界霸权》中从地理与人力交互关系的角度出发,剖析了早期人类文明中海洋的两种形象。
他选择用“支配”一词,而非“强迫”来描述环境与历史的关系,为人的知识与意志留下了必要的空间,未必可以用简单化的“地理决定论”来框定。
以海为墙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将埃及形容为两个“海湾”:“一个由北方向南伸的海湾,在北面冲刷着埃及,伸展到埃塞俄比亚;另一个海湾则是从南方伸入,向叙利亚延展。”
对于从希腊乘船来到埃及的希罗多德来说,这种比喻是很自然的。他从扇形的尼罗河三角洲边缘上岸,走陆路抵达“扇面”端点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然后便进入了狭长的尼罗河道,这就是他眼中的第一个海湾。另一个海湾便是红海、西奈半岛到地中海东岸了。
希罗多德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他6岁的时候,乘着大破波斯帝国之威,雅典确立了希腊霸权。他去世前6年,雅典与斯巴达争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在他去世时,埃及已经接受波斯统治长达百年。再过100年,年轻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踏上了征程,直到征服的兵锋止于今天主要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畔。换言之,希罗多德见到的是古埃及文明的末端。
“两道海湾”的疆域,大致成型于公元前15世纪的新王国时代。军人法老图特摩斯一世(Thutmose I)及其孙儿图特摩斯三世,致力于向北扩张,最远控制了几乎整个地中海东岸,直到今天的土耳其边境。这也是埃及海军大发展的时代,以应对来自地中海的“海上民族”侵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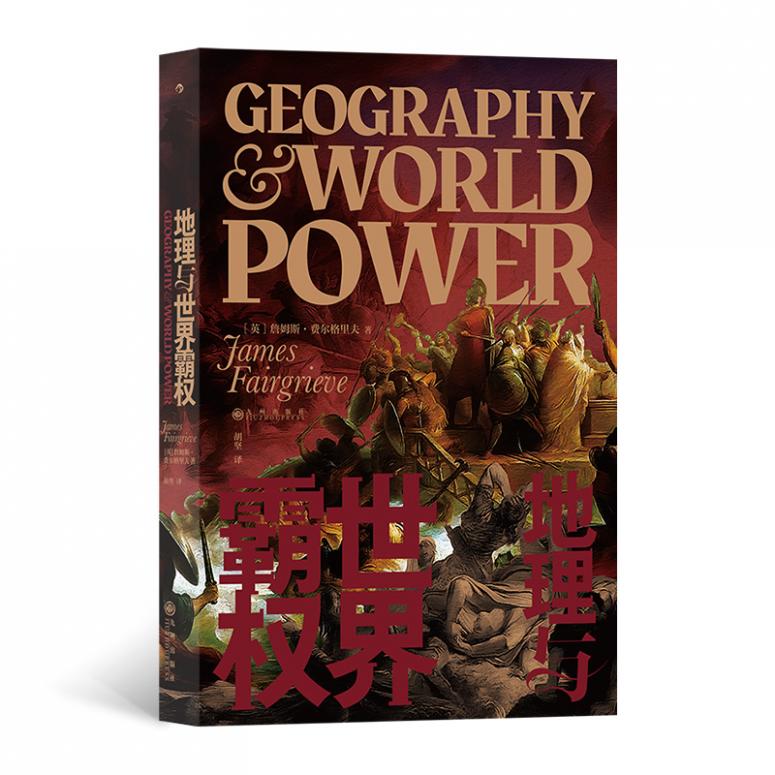
《地理与世界霸权》【英】詹姆斯•费尔格里夫 著胡坚 译后浪·九州出版社2022年6月
公元前12世纪,拉美西斯三世(Rameses III)法老在尼罗河上游修建了一座神庙,上有一段铭文写道:“我用大小战船让河口固若坚墙。船首船尾皆有勇士持械护卫,船上装载着来自全埃及的兵卒。”
在前一个世纪,曾与小亚细亚半岛强权赫梯帝国(Hittie Empire)大战的拉美西斯二世,迁都于尼罗河口地带的培-拉美西斯(Pi-Ramesses)。在传统印象中,一座古埃及城市位于尼罗河的一侧,有四四方方的王宫与神庙,不远处便是浩瀚无垠的沙漠。培-拉美西斯则大异其趣,河汊蛇行蜿蜒,河中岛星罗棋布,神庙与王宫也只能因地制宜。
发现古城遗址的20世纪奥地利考古学家曼弗雷德·比埃塔克(Manfred Bietak),将培-拉美西斯称为“埃及的威尼斯”。与尼罗河上游的旧都底比斯(Thebes)相比,培-拉美西斯不仅是法老家族的发源地,也因其位置而方便征战和外交,彰显了埃及文明在新王国时代的进取气象。
那么,海洋对新王国时代之前的埃及文明意味着什么呢?费尔格里夫给出了简洁的概括:“埃及的北边是大海,在人们对海洋尚且一无所知的时候,海洋像沙漠一样提供了巨大的保护。”对于早期的埃及文明来说,“三面高墙”是一个更恰切的比喻,唯一的大缺口是东北方向。来自西亚的各个民族,可以经过地中海东岸和西奈半岛进入埃及。
比如公元前17世纪涌入的喜克索斯人(Hyksos),他们甚至在尼罗河下游建立了一百多年的统治。“喜克索斯人”的意思是“外来者”,并非单一民族,而是在一个长时段内陆续迁入的众多西亚民族的统称,或可类比于东汉时期内附的南匈奴、羌人与乌桓。但直到喜克索斯人到来之前,三面高墙都保护着早熟的埃及文明,金字塔便是“墙内”时代的杰作。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埃及在和平与繁荣中安然度过了上千年。中央机构的老化与地方大员的自立,曾让埃及陷入长达百年的动乱。在这样的封闭地理单元中,希罗多德记录的一则埃及神谕所言不虚:“埃及是尼罗河泛滥和灌溉的这一整块土地,而埃及人就是居住在埃列凡提涅(Elephantine)以下,并且饮用尼罗河水的那个民族。”埃列凡提涅意为“象岛”,是尼罗河上游的一座河中岛,濒临阿斯旺(Aswan)市区,与著名的阿斯旺大坝离得不远。
喜克索斯人最终被埃及人逐出,但不久之后出现的新威胁则更加猛烈,直接拆掉了三面高墙中的一面。这就是盘踞在东地中海的“海上民族”。他们的具体族群身份众说纷纭,但对埃及人来说,他们只是侵扰的“北国人”。
一篇纪功的埃及铭文写道:“法老像旋风一样攻向他们,在战场上健步如飞。对法老的惊恐之情进入了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船被当场打翻,他们也被打倒。他们失去了心脏,他们的灵魂飞走了。他们的武器散落海中。”这与中原王朝面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态度何其相似。
难怪拉美西斯三世会强调“墙”的意象。当技术与文明的发展克服了大自然提供的屏障之后,埃及人必须用“大小战船”建立起人工的屏障,为尼罗河浇灌的沃土补上新的院墙。这就是古埃及海军的目标与作用。
与上述铭文配套的壁画,正体现了这一点。画面最右侧,是占据全图宽度四分之一的法老本人,法老脚下有四个中等大小的人,应该是将军或大臣,他们都在岸上张弓射箭。画面中间是埃及人的战船,船上的小人在与画面左侧的“海上民族”交战,阻止对方从尼罗河三角洲上岸。
以海为墙,造船补墙的思路源远流长。李鸿章在日本吞并琉球之后,力主筹建北洋海军时这样表述海军的功能:“是此项水师果能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这既是现实的战略考量,也体现了文明发展的惯性,或者费尔格里夫所说的“动量”。
但是,人类对待海洋的态度并不只有这一种。比古埃及兴起稍晚的腓尼基人(Phoenician),正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海洋通道
腓尼基文明兴起于公元前25世纪,大致与分布于我国鲁豫晋陕各省的龙山文化同期,稍晚于古埃及。几乎在所有方面,腓尼基人都是埃及人的反面。
古埃及的典型社会形态是大河两岸的大一统文明,腓尼基人则一直分属不同的沿海城邦。
埃及人以务农为生,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面包,正如德国历史学家H. E. 雅各布(H. E. Jacob)在《了不起的面包》中说:“埃及全国都像是一个长长的烤炉一样,既要负责养活生者,又要滋养亡灵。”代表腓尼基的物品则是一种紫色染料,原料是一种骨螺的黄色分泌物,经日晒后变为紫色。
事实上,“腓尼基”这个词本身就有“深红色”或“椰枣”的意思。有一些品种的椰枣晒干了以后正是紫色。由于骨螺染料着色力强且不易褪色,深受各地权贵欢迎,直到19世纪中期才出现了能与之匹敌的苯胺紫,苯胺紫同时也是全世界第一款合成染料。
当然,腓尼基人售卖的产品可不只是染料而已。希罗多德记载了一个故事,说腓尼基人曾从尼罗河上游的底比斯城掳走了两名女祭司,一个被卖到了利比亚,一个被卖到了希腊。而且腓尼基的人口买卖是成规模的,以至于希腊的一个地方给被拐妇女起了个“鸽子”的绰号,因为当地人听不懂她们讲话,就笑话她们讲的是鸟语。
这只是腓尼基人无数贸易路线中的两个而已。随着贸易的拓展,腓尼基人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最西侧已经接触到了大西洋,而最著名的一处当然就是汉尼拔(Hannibal)的故乡,曾与罗马人争霸数十年的迦太基(Cartage)。
费尔格里夫认为,对腓尼基人来说,“海洋是建立贸易路线的一种工具……海洋本质上是一条通道”。通道观念并非凭空出现,也不是所有沿海民族都把海洋当作通道,日本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日本形成“海国”观念,大致始于江户时代中期,之前则多以“陆国”自居,海洋在明治之前的日本史中仅居于边缘。
在奋力开辟海上通道之前,腓尼基人所处的地中海东岸早已是陆上通道。从两河文明(主要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去埃及有两条主要道路:一条是专门挑河谷走,路程远但比较好走;另一条是横穿叙利亚沙漠,路程虽近,却需要掌握在沙海中赶路的本领。无论走那一条路,腓尼基都是必经之路。
当然,陆上通道本身不会立即让居民掌握航海技术,但能让他们不断接触到新的刺激,也知道了两侧的大帝国是他们不可能战胜的。狭小的地域不足以养活增殖的人口,众多的天然良港更为冒险的水手们提供了安全的基地。
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腓尼基人会将目光投向大海就不奇怪了。至少从公元前15世纪开始,新王国的埃及向北征讨时,腓尼基人就已经被视为海洋商人了,他们的海洋冒险史必定还要远早于此。
这就是费尔格里夫所说的“支配”。他举了一个例子:“人类可以通过挖一条沟渠来支配从山坡上流下来的一条溪流,用石头筑坝以防止流水漫到沟渠外面,也可以铺设管道,按自己的意愿引取部分或者全部溪水。”由此可见,人对自然环境的支配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方面是客观条件与物理规律的约束,另一方面是人的知识、劳动与选择。
换句话说,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利用能量的具体方式。这种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张力贯穿于《地理与世界霸权》全书。比如,书中刚讲了地中海对早期航海者的种种便利,下一段就大谈:“腓尼基人最初可能来自巴比伦尼亚,是当地驾船和做买卖的老手,那里的晴朗天空吸引了人们对天文学的兴趣……新环境的刺激又会促使他们去往新的方向……驾船出海,驶向蛮荒之地,并且愈行愈远。”
尽管地理因素对历史的支配作用远远达不到“决定”的程度,但支配的力量确实是非常持久的。直到20世纪上半叶,黎巴嫩山民还有一句劝告后辈的话:“要下山,不要上山。”在这里,下山常常意味着远渡重洋去讨生活,就像3000年前去西班牙建立殖民地的先人一样。只不过,在汽船与海外工作机会的加持下,现代黎巴嫩人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世界,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从委内瑞拉到挪威。现在,巴西和阿根廷都生活着100万以上黎巴嫩人,而黎巴嫩本土也不过有400多万人口。
这种勇气无法让腓尼基人建立帝国霸业,却自有一股凛然的威严。正如费尔格里夫所说:“经常驾驶着几叶扁舟远航沧溟大海的腓尼基人,不仅培育了高尚的勇气,也养成了热爱自由的天性。”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