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打败拿破仑的流行病
摘要: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弗兰克·M. 斯诺登(Frank M. Snowden),在《流行病与社会》一书中,详实而生动地讲述了这段血淋淋的故事。尚未称帝时,拿破仑为了夺取利润丰厚的殖民地远征海地,结果因黄热病铩羽而归。十年后,痢疾与斑疹伤寒又接连摧折50多万征俄大军。
流行病不止是一种自然现象。值得人类研究的流行病,大都与人造环境、社会条件与政策行为息息相关。在战争中,尤其是规模庞大的近现代战争中,这种关联常常以一种鲜明而血腥的方式呈现出来。拿破仑正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弗兰克·M. 斯诺登(Frank M. Snowden),在《流行病与社会》一书中,详实而生动地讲述了这段血淋淋的故事。尚未称帝时,拿破仑为了夺取利润丰厚的殖民地远征海地,结果因黄热病铩羽而归。十年后,痢疾与斑疹伤寒又接连摧折50多万征俄大军。
正如斯诺登所说:“流行病……揭示了每个社会所独有的脆弱性,研究它们就是要探索这个社会的结构、生存环境与政治特权。”
军中大疫
战争与流行病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史书中关于军中瘟疫的记载比比皆是。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乘破蜀之威,顺流东下,围攻位于今天重庆西北部的钓鱼城。尽管宋军损失惨重,但元军攻城四月有余不克,恰逢蒙哥驾崩,南宋政权的西方门户由此得保。
关于蒙哥之死,现代读者最熟悉的说法大概出自《神雕侠侣》:“杨过低头避过,飞步抢上,左手早已拾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呼的一声掷出,正中蒙哥后心。杨过这一掷劲力何等刚猛,蒙哥筋折骨断,倒撞下马,登时毙命。”这是金庸先生为了增加趣味而原创的情节,不仅将地点从钓鱼城搬到长江中游的襄阳,还为主角杨过平添高光时刻。
当然,蒙哥中飞石而死的说法并非捏造。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主张,杀死蒙哥的是守军的投石机。或许是为尊者讳,《元史》只说蒙哥6月“不豫”,7月“崩于钓鱼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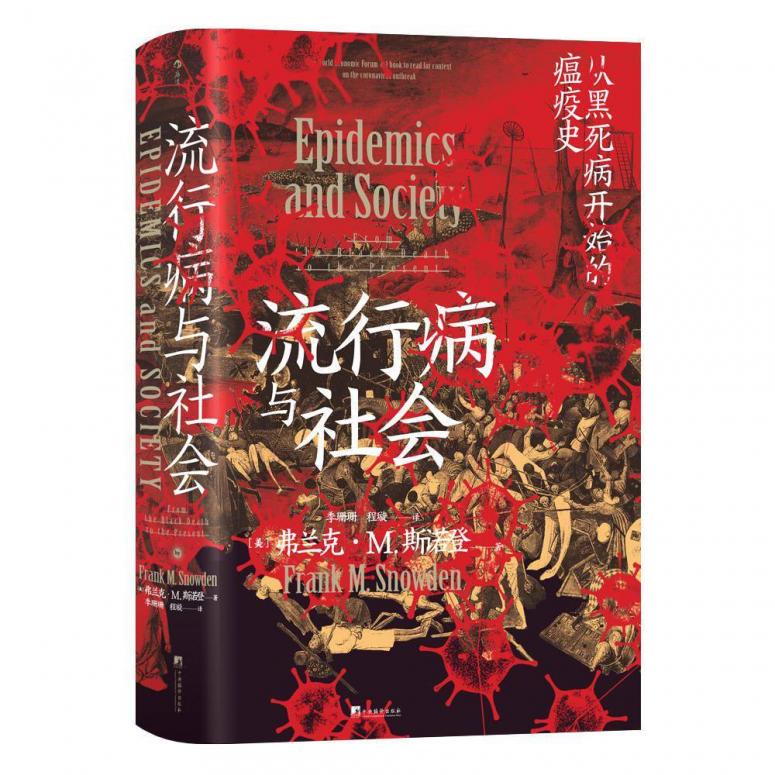
《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开始的瘟疫史》
不过,《元史》中多次强调的另一面,或许更能揭示元军失败的原因。蒙哥在东征前曾询问勋贵群臣,南方瘴疠,是否适合蒙古人久居。虽有这样的担忧,但蒙哥还是决意亲自督战。随从蒙哥东征的金朝降将史天泽的传记中,这样记录元军:“己未夏,驻合州之钓鱼山,军中大疫,方议班师。”尽管蒙古水师随后大破宋朝援军,但先有大疫,后有崩逝,元军只得放弃伐宋。
这只是瘟疫打败大军的无数例子中的一个。而且受限于古人的医学认知,史书中对流行病的描述只有“大疫”这样极为宽泛笼统的描述,对原因的追溯也只是“夏暑且至”、“南土瘴疠”而已。因此,读者往往只能留下一种抽象乃至宿命论的淡漠印象。毕竟,生老病死,天地风水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客观状况。除了慨叹之外,实在很难透过苍白的书页唤起任何强烈的情绪。
但进入近代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诊断能力的提升、写实记载的增多,战争与流行病的黑色关系血淋淋地摆到我们双眼之前,一方面强行调动着我们的情绪官能,另一方面也为战胜疫病带来了一丝希望的光芒。正如斯诺登在《流行病与社会》中所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兴起的大规模征兵开启了‘全面战争’的时代……为斑疹伤寒、痢疾、伤寒、疟疾和梅毒等传染病的流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事实上,拿破仑生涯中有两次最重大的失败,都是直接缘于流行病。
一场是1802年至1803年的海地远征。肆虐的黄热病摧毁了拿破仑开辟新财富之路的美梦,甚至让时任终身执政的拿破仑抱怨道:“该死的糖!该死的咖啡!该死的殖民地!”
另一场失败,是1812年的入侵俄国。尽管冬季的严寒和辽阔的荒原都是拿破仑折损50余万大军的关键因素,但若论直接的杀手,当数痢疾和斑疹伤寒两种。当时的军医、士兵、将军们留下了大量一手资料,让现代学者能够近距离地考察战争与流行病之间的关系。
蚊子的乐土
加勒比海上,古巴东侧有一岛屿,名为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意为“小西班牙”,得名自1492年上岛并建立殖民地的哥伦布。17世纪,法国夺取岛屿西部三分之一,命名为圣多明各(Saint-Domingue),大力发展以黑奴为劳动力的种植园经济。
凭借糖、咖啡、棉花、烟草等大宗经济作物,圣多明各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富庶的殖民地。当然,再多财富也与黑奴无关。在恶劣的劳动、生活与卫生条件下,鲜有黑奴能在岛上活过5年。而岛上的白人死亡率同样高企,这是因为岛上肆虐着黄热病。
西半球的黄热病,是通过黑奴贸易从非洲西部和中部传来的,主要传播媒介是蚊子。蚊子偏爱在浅小水体中产卵,甘蔗田、水土流失造成的大片海岸沼泽、种植园内的无数生活器皿,正是理想的环境。生产车间中还有不少罐子装着浓度适中的糖浆,恰好为蚊子幼虫提供了野外环境中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富养环境。
不仅如此,无数黑奴和为数不少的白人殖民者,为雌蚊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血液,供给着产卵所需的宝贵蛋白质。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在海地建成了8000多个蚊子与黄热病的天堂,也就是种植园。
上述状况一直都存在,而且黄热病症状猛烈,重症患者会起全身皮疹,皮肤因黄疸而发黄,还会有混有凝固血液、形似咖啡渣的呕吐物。在19世纪初,黄热病的病死率估计在15%到50%之间,但这并没有妨碍圣多明各成为“安的列斯群岛的巴黎”。
与天花一样,黄热病是一种获得性免疫和交叉免疫的传染病,患者只要得过一次类似疾病并康复,之后便不会再次感染。输入海地的大部分黑奴,小时候都得过登革热,由此获得了对同类瘟疫黄热病的免疫能力。同理,对从未接触过类似疾病的欧洲人来说,海地自然成为畏途。但岛上的欧洲人毕竟稀少,也会有意识地分散居住。于是,海地虽然条件恶劣,但尚可维持。
1801年冬季,装载着5万以上大军的法国舰队陆续抵达海地,一场黄热病的狂欢拉开了序幕。此时,大革命之后的解放浪潮早已平息,秩序、胜利与财富成为了法国的新箴言。新任终身执政拿破仑,决定重新征服富庶的圣多明各殖民地,恢复种植园经济的运转。
拿破仑和他任命的远征军司令勒克莱尔(Charles Leclerc),本来打算在雨季来临之前打垮起义军政权。可惜在神出鬼没的黑人游击队面前,速战速决的战略失败了。进入4月后,病死者与日俱增。除了欧洲士兵缺乏抵抗力以外,拥挤肮脏的军营环境甚至比种植园更适合蚊子的生长。毕竟,就连黑奴也不至于直接在废弃房屋上厕所,士兵们会直接把废弃房屋当作厕所,还会草草掩埋大量携带着病菌的尸体。医院不仅床位短缺,医生也不知道任何有效的治疗手段。
事实上,现代医学直到今天,对治愈黄热病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在当时的医学理论指导下,医生们会为患者服用由水银和泻药制成的催吐剂,甚至会从静脉直接注入药剂。可想而知,这些“治疗”很可能反而会加速患者的死亡。
不仅医生对黄热病束手无策,就连勒克莱尔也陷入了绝望。他在一封写给拿破仑的信中写道:“疾病的进展如此可怕,我无法计算它将于何时结束。本月,仅法兰西角(海地北部主要海港,当时是法军指挥部所在地)一家医院每天就有100人死去……仅凭一支减员五分之四、生还者也丧失了战斗力的部队,我身为将军还能做什么呢?”1803年11月,仅存的法军以囚犯身份登上英国军舰,此时,勒克莱尔已经病死整整一年了。
俄国不止有冬将军
海地远征的失败,葬送了拿破仑重建北美洲殖民帝国的野心,十年后的俄国战役更是直接敲响了拿破仑帝国的丧钟。1812年6月,将近60万法军进入俄国境内。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两种流行病接连吞噬了大部分法国将士。同年12月,只有1万人回到了当初渡河征俄的起点。
与黄热病不同,痢疾无法通过获得性免疫和交叉免疫来抵御。不仅如此,痢疾是有无症状感染者的。这意味着,等到医生注意到问题时,痢疾往往已经暴发了。这正是法国大军团在8月遇到的状况。针对这种细菌性肠胃传染病,我们现在会动用抗生素,辅以补液疗法,缓解脱水症状。但在当时,腹泻不止的士兵常常会狂饮伏特加,希望借此“清理肠道”。结果,到了8月底,每天就有4000名法军死于痢疾,法军对俄军的数量优势荡然无存。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向来稳重的俄国老将库图佐夫(Mikhail Kutuzov)决定与法国皇帝决战,博罗季诺会战(battle of Borodino)爆发了。在这场惨胜中,法军付出了3万人的代价,勉强超过痢疾造成减员12万人的零头。9月4日,虽胜犹败的法军进入莫斯科。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痢疾将军”不断扩大战果。等到10月15日,只剩下10万人的法军,撤出了被皇帝付之一炬的沙俄故都。除了骚扰不休的哥萨克骑兵和围追堵截的俄国正规军以外,法军还要面对另一位可怕的对手——斑疹伤寒。
相比于依赖苍蝇传播的痢疾,通过虱子传播的斑疹伤寒似乎本不应该取得近10万人的斩获。正如斯诺登所说:“虱子作为病媒的效率太低……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密切接触,才能维持感染链和传播链。”但在严寒的催迫下,法军士兵身穿厚重的皮毛衣服,再加上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烤火吃饭,和衣席地而睡,恰好为虱子提供了安乐窝。
斑疹伤寒的症状复杂而可怕。患者在初期就受高烧折磨,之后更会从肩膀一直疼到屁股,浑身散发出氨气的味道。同时,患者会失去对肌肉的控制力,出现癫痫和谵妄的症状。在认知失调和绝望情绪蔓延的双重作用下,自杀者越来越多,军队秩序也濒临瓦解。
拿破仑总参谋部成员费岑萨克将军(Raymond de Montesquiou-Fezensac),留下了这样的可怖记述:“一个人倒下后,他的战友们就把他身上的破布扒下来自己穿上。营地的夜晚犹如激战后的战场,一觉醒来,你就会发现昨夜躺在身旁的人们,已成了并肩而卧的尸体。”一名幸存的中士甚至暗示,法军中出现了人相食的状况。
规模空前的拿破仑征俄战役,充分表明了战争与流行病的双向因果关系。恶劣的卫生与饮食条件是流行病的温床,流行病也会决定战争的进程。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