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福尔摩斯协会会长之死: 没有结果的调查是不是好故事?
正如古典音乐和大部分流行音乐里,往往要求在不和谐的“紧张”之后有一个“解决”,读故事时大概也会有一种对结果的期待,不管是现实还是虚构的故事。就拿最近一审判决出来的吴谢宇案来说,相关人员和吃瓜群众们从一开始就在追寻“结果”:他到底有没有杀人?他到底为什么杀人?还有,对他杀人应该予以怎样的道德审判?但上面三个事实、解释、判断层面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结果。多年之后,这个案件可能依然会滋养着无数以“补写结果”为目标的衍生作品。
但是,把“没有结果”明明白白地亮出来,只是把已有的材料和推理的过程摆出来,这样算不算是一个好的故事呢?一位伦敦福尔摩斯协会前会长的离奇死亡,以及后人对他的破解记录,是一个绝佳的回答。
本格密室杀人案
柯南·道尔爵士是福尔摩斯小说的作者,也是当时收入最高的作家。如果随便在街上找一个人问,你最先想到的侦探是谁?答案十有八九是福尔摩斯。但这样一位鼎鼎大名的作家,至今没有一本真正权威的学术传记问世。
一个重要原因是,柯南·道尔的继承人特别重视他的“名誉”。只因为一位传记作者用“一位在街上闲晃的人”来形容柯南·道尔(这还是引用了柯南·道尔在作品中的原话,本是一种常见的传记写作技巧),柯南·道尔的一个儿子就马上推出了《真正的柯南·道尔》作为反击,另一个儿子更是公开向传记作者提出了决斗挑战。后来,柯南·道尔的小女儿琼女爵成为了父亲手稿、书信等资料的保管人。这批资料对任何一位有意撰写柯南·道尔传记的人都是无价之宝,而它们也牵出了一场财产纠纷和命案。
理查德·兰斯林·格林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道学家”,曾任伦敦福尔摩斯协会会长。他与1997年去世的琼女爵关系良好,曾在女爵生前有幸看过这批材料,而且手持女爵遗嘱的复印件,上面写着柯南·道尔资料将在她去世后赠予大英图书馆,供全世界研究者和爱好者免费阅览。因此,按照道理,格林应该会收到资料上架的消息,但一直杳无音讯。直到2004年3月,佳士得拍卖行发布了一条拍卖信息:格林翘首以盼的资料将逐件进行拍卖,拍卖者是柯南·道尔的两位远房亲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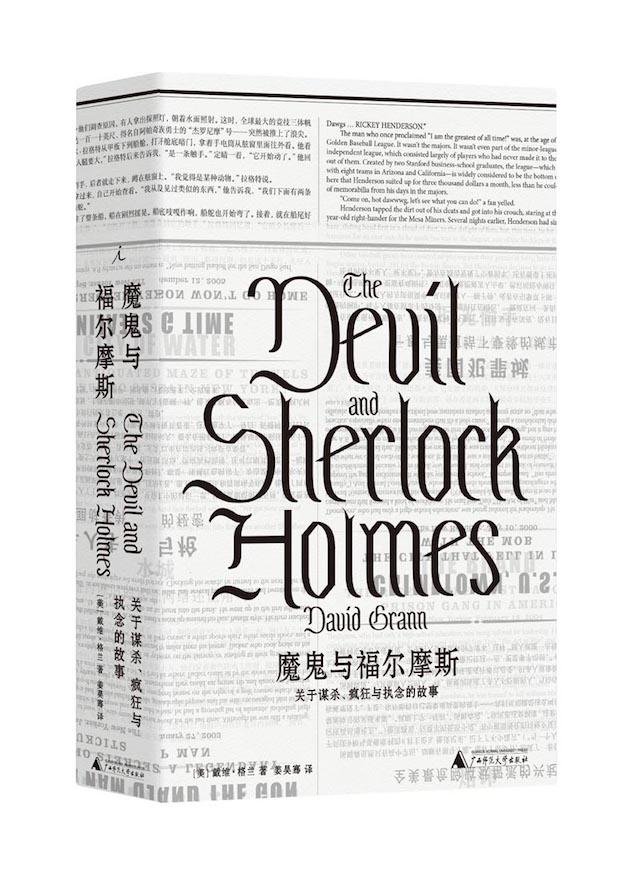
格林怒不可遏,坚信这场拍卖是非法的,并且拿出了证据,要与拍卖行和拍卖人抗争到底。然而,就在当月,格林被发现死于家中,脖子上勒着一条鞋带。
这起案件至今是一场悬案。《纽约客》杂志调查记者、《迷失Z城》一书的作者戴维·格兰通过对众多相关人士的采访和资料收集,写出了《神秘事件》一文,文章最后一句话却是死者妹妹的一段话:“现实不是侦探小说,没有答案也没办法。”不过,同名话剧《神秘事件》2019年倒是在美国上演了,编剧别出心裁地请出福尔摩斯本人,最终破解案件,给了格林案一个圆满的结局。
哪一种结局更好呢?或者说,有结局更好,还是没有结局更好呢?在阅读和翻译《神秘事件》这篇文章时,我基本上是处于这般状态,一个个结局的一角被掀开,然后盖上“未必”的火漆印章,直到最后所有卷宗都被放到一个档案袋里,封好口之后,在上面写了一行整整齐齐的字:我觉得真相是永远无法知道了。
首先,作者拜访了曾与死者最好的朋友之一,约翰·吉布森。吉布森也是一位铁杆福尔摩斯迷,在格林去世后还参加了警方的听证会。警方没有发现闯入迹象,于是认定是自杀。吉布森则举出了一系列证明警方“辜负”了死者的证据,比如死者生前曾对他说,一个美国人要害死他,而且勒死死者的是很罕见的鞋带,而非粗绳索。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一位熟练的推理小说家应该可以写出一部中规中矩的密室杀人案。
从封笔到降神
从11岁开始,格林便熟读了每一部“福尔摩斯”小说,后来更是积极研究柯南·道尔的作品与生平,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一部足以传世的柯南·道尔传,因此自然与琼女爵攀上了关系。
到这里为止,密室杀人案的戏码都还走得下去,尤其是加上了格林的另一位好友欧文·多得利·爱德华的证据。他坚信曾与自己一同呼吁终止拍卖的老友是被谋杀的,而且杀人者是某个财路被挡的恶人。现在好了,连作案动机都有了。正常来说,应该进入推理环节了吧:凶手只有一个!

《四个神秘的签名》,英国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于1890年所创作第二本以名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为主角的推理小说。
接下来,作者采访了一个匿名的美国人,此人也是格林的生前圈内好友。他不仅透露了一个重要细节:琼女爵在去世之前的几年与格林闹掰了,据传是有人在挑拨离间。但他讲述的另一个故事直接扭转了全文的方向,从本格推理转向了社会派。
福尔摩斯为柯南·道尔带来了巨大的名声和财富,但也让他背上了负担。他曾亲口说,“创造谜题和构建归纳推理链”的不断循环让他心生厌倦。他渴望写一些新的东西,一些更严肃的文学作品。于是,以中世纪为背景的历史小说《白色军团》问世了。
但是,在《福尔摩斯探案集》已经有了一万个版本的今天,这部作者心中的“巅峰之作”至今连一个中译本都没有,一时半会儿大概也不会有。当时,《白色军团》也受到了冷遇,作者只得回到福尔摩斯的创作中。仅仅过去两年时间,1893年,柯南·道尔就交出了《最后一案》。在福尔摩斯诞生6年后,作者毅然决定封笔,而且在日记中愉快地写道,“福尔摩斯已死”。
有过这样经历的作家并不少,毛姆就是其中一位。当代中国读者最熟悉的毛姆作品,大概是《月亮与六便士》《刀锋》《人生的枷锁》。但是,让他成为当时少有的依靠写作赚得巨大收入和名望的,并不是这些长篇小说,而是短篇小说,尤其是30岁前后写的大量火爆话剧。他初入文坛时写过揭露社会现实的小说,也写过历史题材的小说,但都没有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之后总算依靠磨练多年的剧本笔力实现了市场的突破。在十年的剧本生涯中,他尝试过写比较严肃的剧本,结果立即被市场打脸,最好的结果不过是叫好不叫座。他也多次流露出不想再写剧本的愿望,但还是屡屡回归。正如他本人所说,“多年后,我成了一名畅销轻喜剧写手,也失去了(被视为有前途的文坛新星的)殊荣。”
毛姆在纠结了十年后,终于顺利退出了剧本圈。但柯南·道尔不仅在《最后一案》十年后迫于公众压力,在《空屋探案》(1903年)中以当初只是为了躲避莫里亚蒂一伙追杀而假死为由,让福尔摩斯回归,而且一直创作“福尔摩斯”系列作品到1927年。他的女儿琼认为,福尔摩斯是他们一家的诅咒。
福尔摩斯赖以成名的是理性推理,这也是一战前推理小说的主流。这一派作品的基本特征在《推理小说十诫》和《推理小说二十法则》中得到了凝练的表述,比如“必须明确、公正地将所有线索呈现给侦探与读者”、“故事中不能掺有恋爱成分”、“必须经由合理的推理缉凶”、“凶手不得以大型犯罪组织为后台”、“必须贯彻唯一的真相,并为此向读者提供线索”……
但在对战争的血腥和毫无理性有过切身之痛后,福尔摩斯之父在生活中也开始拥抱理性的反面。比如“道学家”丹尼尔·斯塔斯豪尔曾写道,柯南·道尔开始相信鬼神,而且参加了多次降神会,还宣称与自己死去的弟弟有过交流。让他声名扫地的一件事,是大力宣扬1917年的一张伪造超自然生物照片。
这原本是情有可原的事情。遭受个人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地震之后,人难免会更容易从思维转投灵与肉的怀抱,柯南·道尔如此,一战后的推理小说界同样如此。雷蒙德·钱德勒取代柯南·道尔,成为了新一代硬汉侦探的旗手。
但是,格林无法接受自己心中的英雄有这样的污点。多年来,他一直在收集一切与柯南·道尔有关的物件,其中就有宣扬唯灵论的小册子和各种神秘研究。除了这些让他无法说服自己为柯南·道尔辩白的资料,更令他心焦的是琼女爵的遗赠迟迟没有露面。他的一个朋友说,“他把整个肉体、整个心灵都用来研究(柯南·道尔)。”
杀人的执念
故事讲到这里,一个新的主题已经隐隐出现:执念。读者的执念。柯南·道尔十年间收到的读者反馈并不都是亲切的问候,更多的是赤裸裸的威胁。而正如爱德华所说,“如果生命中只有福尔摩斯,那是很危险的。”
虽然没有资料,但研究的脚步不能停下来。他写了一篇柯南·道尔偷情秘闻,但不久被发现证据不确实,只好在期刊上发文道歉。这篇文章写于2002年,也就是格林去世前的两年。
琼女爵文献流落到佳士得拍卖行之后,他的福尔摩斯之魂再次爆发。他真正扮演起了福尔摩斯的角色,通宵达旦地研究这些文件为什么属于大英图书馆。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但无论他如何尝试,就是不能建立起完整的证据链。他记得柯南·道尔的一名子女在一份录像带里说资料要捐给大英图书馆,朋友找到后反馈说里面没有这段话,结果惹来了格林在电话里的一顿臭骂。那时距离格林去世仅有几个小时。
这条线索指向的“谜底”是自杀。杀死他的不是某个“美国人”,而是他自己的执念。更有甚者,他的朋友吉布森还推断这是一出伪装成他杀的自杀,目的就是构陷那个他心中坚信的恶人。这条线索同样有证据支持,比如格林专门留下了三个电话号码,宣扬美国人要害自己等等。
与之前的“密室杀人”戏码相比,“执念杀人”的情节更为跌宕起伏,而且也更有内心的深度,给出了一个比谋财害命更加深刻的动机。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写下去的话,这会是一篇精彩而圆满的推理故事。
可惜,后续调查几乎破除了这种可能性。比如,那三个号码中有两个是记者的,还有一个是佳士得工作人员的。另外,拍卖的文档是琼女爵去世前夕分给三位亲属的,虽然在道义上尚有批判的空间,却是完全合法的。
最后的写法相当于给前面精彩的“立—破—立”结构来了一个釜底抽薪,不仅把最后的一个本能赢得满堂彩的结局抹杀,甚至让整个案件都失去了立足点——原来格林死前的最后一项事业竟是一场巨大的乌龙。
由于琼女爵跟他关系破裂,他原本就没有希望自己在女爵生前看到这些资料。他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琼女爵的遗赠“遗嘱”上。但女爵死后没有动静,他盼望的资料竟然还要被拍卖,他便发起了人生的最后一场战斗。可惜,这只是因为女爵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写了新遗嘱,偏偏他还死在了遗嘱合法性结果公布之前。于是,开头以为是悬疑剧,最后竟然生出了荒诞剧的味道。
难怪有豆瓣网友说这篇文章“完全是个噱头报道,写得连小报水准都够不上”——因为“并不存在‘找完线索可以来推理了’这种绝对性时刻……并不存在唯一的确切无误的真相”。
回到开头的问题,这种“没有结果”的故事算不算是好故事呢?就其本身来说,作者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毕竟就像历史学家一样,有多少材料出多少菜。但是,调查过后又不能不出点成果,所以这种“中间产物”式的作品就产生了。
国内有一个能够与此对标的(系列)文章:没药花园对吴谢宇案的追踪报道。她在2017年《头顶烈日,站在黑暗中》就提出了自己的明确判断:“这是一次非理性带有自毁性质的谋杀。”而且她最近表示,“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改变观点”,这样的判断来自几年来的持续关注。我相信,格林案存在一个“完全体”的话,这应该就是它应有的样子吧。只是,未必每一个犯罪案件,或者研究课题,或者政治风波都会有适当的客观条件(资料披露)和主观条件(坚持追踪的人)等到那一天。
当然,永远有一个潜在的指责: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在玩弄多视角和客观笔调,掩饰自己的猎奇爱好,又用“我做过调查并且完整呈现出来了”来做挡箭牌呢?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