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饮食的千年流变
一个民族的饮食习惯——吃什么、喝什么,乃至如何吃、如何喝,无疑会对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个人性格和行为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传统的俄罗斯民族以黑麦面包为主食,号称“黑麦王国”,千百年来,黑麦始终居于俄罗斯人饮食结构的核心位置,这一方面取决于俄罗斯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又与俄罗斯的政治特征和宗教生活密切相关。对于身处恶劣环境中的俄罗斯人来说,由酸面团制成的黑麦面包虽然难以消化,却有助于抵御饥饿,黑麦面包不仅给他们带来营养,同时也是一种神圣礼仪的象征。
美国美食作家、食品研究专家达拉·戈德斯坦的新著《黑麦王国》,是一部关于俄罗斯饮食文化千年流变的作品。在这部堪称俄罗斯饮食简史的小书中,作者分别从俄罗斯的自然环境、土地特征,以及俄罗斯人的饮食习惯、餐饮结构等多个方面入手,围绕着黑麦面包,对俄罗斯黑麦王国的形成及其演变进行了细致梳理,让我们一窥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从而呈现出一段源于木勺而非权杖的俄罗斯历史。
作者用二元对立与简单的并置排列的方式,来讲述俄罗斯的餐饮故事:匮乏与丰盛,盛宴与禁食,贫穷与富裕,克制与奢靡……从中揭示出俄罗斯民族的社会结构和食物消费方式,展现了俄罗斯人在遭受逆境时所催生出的一系列惊人的烹饪手法,赞美了他们应对困难的聪明才智,以及从贫穷中保留下来的味觉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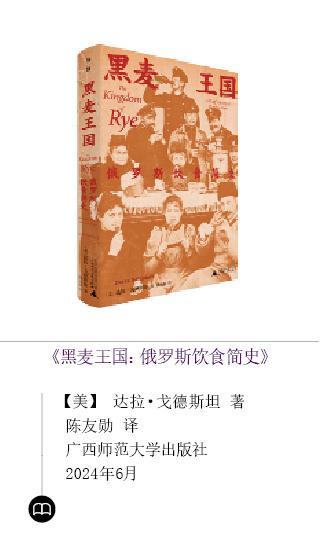
黑麦面包既是一种食物,又是一种信仰
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地处北温带,因其纬度较高,漫长与寒冷的冬季为其气候的主旋律。除了极少部分草原上肥沃的黑钙土地带之外,俄罗斯的土壤大部分都非常贫瘠,一般作物的生长季节相当短暂。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大多数俄罗斯民众始终生活在温饱的边缘。气候变化的无常,使他们无法预测每年的收成,更不知道能否解决一家人的温饱问题,而他们的生活也不得不“摇摆于饥饿与一场可能会被过早的霜冻、干旱、冰雹、虫灾或人为破坏的年收成之间”。
俄罗斯最早的历史记录始于公元852年,其中记载了几次严重的饥荒,细节的描述令人毛骨悚然。公元10世纪早期,黑麦由亚洲传入基辅罗斯,时隔不久,便成为俄罗斯人最重要的食粮来源。完整的黑麦粒或被煮成粥,或被磨成面粉,做成黑麦面包,不新鲜的黑麦面包被制成一种名为格瓦斯的饮料,而制作格瓦斯剩下的麦芽浆则被当作发酵剂,用来制作更多的黑麦面包,由此完成了一套完整的循环。
在俄罗斯人眼中,经过发酵和烘烤的黑麦面包,象征着这片土地的味道,将黑麦和水混合,转化为可以充饥的面包,本身就是一种赋予生命的力量。他们敬畏上帝,转而崇敬黑麦面包,将其视为连接上帝和人类的媒介。他们珍爱黑麦面包,用圣餐仪式加以象征,他们甚至决不容忍对一丁点面包屑的浪费,因为他们认为,魔鬼会把一个人扔掉的所有面包屑都收集起来,一旦积累到一定的重量,就会在这个人死后取走他的灵魂。
黑麦面包也会被用来预示生育和富足。在俄罗斯人的婚礼上,新娘会被要求到装有发酵面团的木桶上去坐一下,亲友们则会将面包屑撒在新婚夫妇身上,用以祝福他们吃喝不愁、衣食无忧。作为一种基本的和绝对必要的食品,俄罗斯人对黑麦面包的崇敬既是生存所需,继而又上升为一种宗教信仰。出于俭朴与节食的考虑,东正教会则将这种信仰转化为具体的戒律,他们将一年中的将近200天定为斋戒日,禁食肉、鱼、蛋和各种奶制品,从而使贫困和饥饿变成了一种美德。
这种长期的斋戒与土地最贫瘠的季节刚好吻合,实际上是为了缓解食物匮乏的压力。其中越是生活困顿的家庭,越是严格信守戒律,因为他们在心里已经将匮乏等同于虔诚。但即便只剩下最后一条黑麦面包,俄罗斯人依然会慷慨地分给乞讨者,他们知道应该为乞讨者保留一点尊严,不能让这些乞讨者苦苦哀求,因为在以后的岁月轮回中,他们的角色很容易颠倒过来,帮助乞讨者渡过难关,就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频繁的饥荒使得俄罗斯人产生了某种宿命论,这种宿命论则使他们超越了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他们面对饥荒时变得更加从容。
食物短缺是创造力的催化剂
在俄罗斯,大自然代表着一种至关重要却又不可预知的力量,饥饿和频繁的饥荒,是为俄罗斯历史的寻常故事。然而,艰难的生活环境并没有阻碍俄罗斯人对美好的追求,他们克服重重阻力,在简陋中营造美味,在匮乏中活出丰盈,让俭朴的生活闪耀出富丽的光芒,借以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
俄罗斯世俗饮食的所谓“三位一体”,原本是由伏特加、泡菜和黑麦面包构成的。这三者的美味都依赖于发酵,伏特加由黑麦、大麦和硬质冬小麦等谷物发酵醪蒸馏而成,泡菜是乳酸发酵的结果,酸性发酵则在黑麦面包的制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三种发酵饮食,构成了制作俄罗斯传统美食的核心要素。
俄罗斯传统菜肴的特点是与砖砌炉灶的设计密切相关的,其间比较有代表性的菜肴,无不源于砖砌炉灶。这种砖砌炉灶于17世纪初开始进入俄罗斯普通家庭,它们用砖块或碎石建成,而且灶台上总是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黏土,除了极少数富裕家庭之外,它们大多没有烟囱,以至大量烟雾在空气中弥漫。这些砖砌炉灶体积巨大,既能做饭,又能取暖,炉灶周围则是农家小屋最觉温暖的地方。女主人将面包或馅饼放进炉灶里烘烤,一家人坐在旁边围炉夜话,构成了一幅俄罗斯农家共享天伦之乐的温馨画面。
俄罗斯传统的烹饪手法以蒸煮、烘焙、烘烤、炖煮和煎炸为主。食盐曾经是餐桌上的稀有之物,有一则民间故事这样写道,“傻瓜伊万”在一个小岛上发现了一座巨大的盐山,他把盐装到自己的船上,航行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希望与当地人做交易。但当地人却不知盐为何物,国王甚至将盐视作“白沙”,不屑一顾,直至伊万在国王的菜肴里偷偷地放入了盐,国王才领略到盐的美妙,于是用与盐等量的黄金和白银来奖励伊万。盐才终于在俄罗斯流行开来,成为俄罗斯人制作美食的最重要的调味品,而面包加盐,则成为俄罗斯人接待来客的最珍贵的食物。
俄罗斯人的另外一种重要食物是土豆,它于18世纪早期传入俄罗斯,起初却并不受人重视。1765年,俄罗斯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鼓励人们种植这种食物,局面才有所改观,但直到1840年,土豆仍然没有被俄罗斯人完全接受。随着饥荒的到来,沙皇便强迫农民种植土豆,终至引发了农民起义,史称“土豆骚乱”,政府不得不动用军队镇压。后来政府选择了以宣传的形式进行温和劝诱,事情才有了转机,并最终使土豆变成俄罗斯的一种常见作物。
进入20世纪之后,作为俄罗斯大众主食之一的土豆不仅存活下来,而且发展得很好,甚至成为必不可少的园艺作物,可以说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食品。因为土豆能够给人提供一种安全感,所以只要土豆丰收,一般俄罗斯家庭就不会挨饿,至此,土豆已经正式内化为俄罗斯的本土口味的食物。
从美式快餐的引入到传统美食的回归
苏联时期的到来开创了一种新的、具有革命意义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方式摈弃了贵族的、外国的或资产阶级的性质。最直观的表现是菜肴名称的改变,比如,为了纪念沙皇而命名的“尼古拉维斯基什池”,变成了简单的“碎卷心菜汤”,杜巴利奶油汤变成了“奶油花椰菜汤”,贝沙梅尔白酱变成了听起来就觉得大倒胃口的“白色浓奶酱”,而美式鲟鱼则变成了“番茄酱鲟鱼”……
不过,无论菜肴的名称如何变换,都改变不了食物匮乏的事实。由于餐饮服务的食谱改由国家统一规定,人们几乎失去了任何创新或提高饮食质量的动力,就连餐厅的名字也令人沮丧,通常以一个数字命名一个餐厅。与饮食相关的三大问题,即可定义彼时的时代特色:一是持续的粮食匮乏;二是人们对高档食品的渴望;三是人们在处理家庭烹饪和粮食供应之间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非凡创造力。
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排队,因为国家开始为一些紧俏食品发放配给券,排队就成为人们购买这些食品的常态。精明的购物者们似乎都明白,这些食品随时有可能出现,也随时有可能消失,所以不要在商店正常营业时等待,而要在午餐休息时去排队,庶几增大买到这些食品的几率。事实上,是“地下交易”或人脉关系决定了彼时大多数人的饮食质量,虽然商店里看起来空空如也,但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渠道买到,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1980年代后期,快餐店悄然出现。始作俑者是麦当劳,它在莫斯科开设了第一家分店,就此拉开了西方饮食强势进入俄罗斯的序幕。莫斯科的麦当劳分店位于普希金广场的一个黄金地段,距离克里姆林宫步行仅需20分钟,可谓极具象征意义,成千上万的人排队就餐,只是为了成为第一批品尝美式汉堡的食客。很快,其他国家的快餐店和俄罗斯本土的快餐店也纷纷出现,有意思的是,在麦当劳金色拱门标志的底部,贴有苏联之星和锤子与镰刀的标志,成为俄罗斯集中型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一道奇观。
美式快餐的引入,给俄罗斯的餐饮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然而,进入新世纪之后,俄罗斯传统美食开始卷土重来,伴随着俄罗斯命运与西化派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对传统美食的渴望成为一种时尚。这当然并非单纯的怀旧那么简单,更多的俄罗斯人将本土的传统美食视为“我们的”,并引以为荣,而与之相对,这些俄罗斯人同时又将餐厅里充斥的大量西餐视为“他们的”,这两个概念可以从个人关系以及更具有政治色彩甚至是民族主义的层面来理解。
民族菜肴正在逐渐回归,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当下的俄罗斯人来说,关注“我们的”食物,决不单纯是一个消费需求的问题,实际上也包含着恢复俄罗斯烹饪遗产的强烈愿望。这不仅是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扇窗户,同时又是“为烹饪和文化的过去打开了一扇新的门,从而与未来产生富有意义的联系”。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