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艾丽丝·门罗逝世, 小镇文学青年可以走多远?
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度过了平静而辉煌的写作人生。她的小说,用她本人的话来说,写的是“那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孤独的、个人的、表面之下的故事”。这位被誉为“加拿大契诃夫”的小说家,以毕生的写作实践,为短篇小说正名。她于20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后,这位作家一直常驻加拿大的乡镇。直到2024年5月13日,门罗在位于安大略省霍普港的乡间宅院以92岁高龄逝世,她都鲜少离开这片加拿大故土。人们难以想象,在那人烟稀少的偏僻之地,一个人竟可以把自己的文字经营得如此细密、精致且丰满。
美国著名评论家角谷美智子评价门罗:“行文流畅,文风表面质朴无华,实则结构精美复杂,在时间之中往复穿梭,在现实与记忆之间转换;故事神秘展开,揭开笔下人物生平的全貌景观(在关键的转折点中突出个体人物生活史中的开端、停顿与逆境),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碎细节。”
一如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以其生活过的南方乡土为素材,虚构出约克纳帕塔法县,并以之为小说中人物活动的舞台,门罗的文学世界根植于加拿大乡镇的风土人情。在后现代文学方兴未艾之际,门罗转向人物的内心,“食物、琐事与家务”,这些时常被人忽略的东西却是她书写的对象。
门罗以短篇小说闻名,这在仍倾向于以篇幅定高下的北美文学出版界并不常见。1950年代初试啼声时,她也想写出像劳伦斯(D. H. Lawrence)的《儿子与情人》那样伟大的书,但繁重的家务抹杀了这种可能。不过,几十年如一日写作短篇小说的经验让门罗发现,作为独立的文体,短篇小说有着殊异于长篇小说的特点。
一部优秀的短篇小说应该像一颗钻石,折射出主人公人生全部的色彩。门罗的小说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与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相提并论,他们的作品都能在短短几十页里,呈现出其他作家用几百页都写不尽的厚重情感。
她的目光穿透布满尘垢的小镇日常,描绘着小镇女性在出走大城市与坚守乡土间的徘徊。门罗的这一主题,击中了本世代中国读者的心。高速城市化的当下是他们成长的背景,故其心灵亦时常被出走与回归的循环撕扯。
正因此,门罗从不缺少中国读者,不仅文学爱好者读她,许多专业作家也从门罗的小说中寻找教益。门罗的作品几乎成为理解何谓好的当代小说的最大公约数。她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学价值,也在于我们可以透过阅读她,了解这个日渐疏离的世界。

2013年10月10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门罗书店在庆祝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荒芜中写作的加拿大作家
1931年7月10日,门罗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的休伦县。这座小城市坐落在休伦湖与伊利湖之间的休伦半岛上。若沿着21号公路一路进入休伦县,途中便能看到有翠鸟般颜色的北美大陆。
这片大陆空旷而寒冷。置身其中,为自然环境的酷烈所困,人们很难从容地欣赏风景本身的壮美。自移民横跨大洋来到此地定居起,人与自然之间亦敌亦友的关系,始终是加拿大文学的母题之一。在门罗的挚友、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看来,若与北美五大湖相比,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湖畔派诗人歌咏的湖区,只能算是一些水洼。建国伊始,在和自然、和野心勃勃的邻国斗争的过程中,加拿大人的集体无意识中逐渐涌现出某种屯田戍边者的孤立无援感。很大程度上,这种感觉就是加拿大文学的加拿大性之所在。
门罗也会和她的文学前辈一样,选择荒野作为小说的故事背景。譬如,创作于1994年的《荒野小站》,就是以书信与回忆录为载体,讲述了1852年冬北休伦县一个拓荒者家庭支离破碎的过程。小说中,西蒙与乔治两兄弟来到加拿大,终日面对蔓长的灌木、丛生的荆棘。他们不得不从零开始驯服这片顽劣的土地,砍伐树木,辟出小径,划定路标,建起容身的小木屋。
屋子建好后,西蒙便考虑成家。经由牧师担保,西蒙向多伦多劳动收容所的负责人修书一封,请求对方介绍一位妻子给他。许多移民家庭就是这样成立的,因为几乎所有移民都是荒岛上的鲁滨逊,竭力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已经耗尽他们全部心力,他们早已无心谈情说爱。
于是,安妮便来到了这对兄弟身边,成为了西蒙的妻子。然而婚后不久,西蒙意外被一根树杈砸中,当场身亡。这之后,安妮便发了疯,门罗描写道:“给了她豌豆和马铃薯去种在树桩间,她也不种;门口长满了野藤蔓,她也不清理。大多数时候,她连火也不生,吃不上燕麦蛋糕或粥……那些见过她的人说,她的衣服因为在灌木丛里穿梭而弄得又脏又破,身上全是荆棘的划痕和蚊虫的咬痕,她不梳头发也不扎辫子。”
冗长乏味的日常生活,转瞬便被突如其来的意外打断。这是一个典型的加拿大故事,同时也是门罗祖先的故事,充满着疯癫、死亡、厄运、恐惧等哥特式元素。旷野用它的敌意包围我们,使我们愈发依赖家作为支持物的存在,亦使我们愈发珍惜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联结。很多时侯,门罗会将此种联结提炼为某一个自然意象。譬如,她用“荨麻”象征年少时朦胧的情愫。这种情愫并非刺痛,不那么剧烈,它只带来渗入我们肌肤的一阵阵隐痛,就像蝉鸣渗入一块裹满青苔的石头。
写作《荒野小站》之际,门罗在小说领域已经颇具盛名,描绘这片她所熟悉的故土,自然得心应手。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荒野,它不再只是背景,而是如珊瑚般拥有自己的小生态的一个主体。
门罗有爱尔兰与苏格兰血统,从这些来自边地的祖先身上,她继承了一种敏锐的文字触觉。此种触觉,可以用来感受生活中的震动,即使这震动如一只花蚊子轻轻停在水面上那么细小。她的心灵之所以与加拿大的荒野产生共鸣,也正得益于这种触觉。
出生时,门罗本名艾丽丝·安·莱德劳(Alice Ann Laidlaw)。她的父系祖先可以归溯到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苏格兰诗人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霍格原是牧羊人,通过阅读自学成才。他以“埃特里克牧羊人”之名发表过不少诗文,同时也与其时最杰出的一批苏格兰作家,如历史小说《艾凡赫》的作者瓦尔特·斯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过从甚密。
但到门罗父亲罗伯特·埃里克·莱德劳(Robert Eric Laidlaw)这一代,我们似乎很难发现一位未来的大作家即将在这个家庭诞生的迹象。罗伯特在乡间经营着一家狐狸与水貂养殖场。大萧条时期,他的生意破产了。一家只得在贫民窟里艰难度日,周围的邻居都是些私酒贩、妓女和无所事事者。
12岁时,门罗身为教师的母亲患上帕金森症,经济条件更加雪上加霜。年幼的门罗不得不接过家庭的重担,照顾母亲以及弟弟妹妹。门罗对母亲的感情很复杂。她明白作为长女的责任所在,但在潜意识中,门罗仍免不了想要挣脱因母亲缺位而堆积到身上的无止境家务。母亲保守的价值观也束缚着年少的门罗,在门罗看来,母亲是那种典型的19世纪出生的人,正派、刻板、勤奋,对他人及自我的道德要求都近乎苛刻。
2013年,在接受《卫报》采访时,门罗表示:“我认为,当你长大后,你必须摆脱母亲的欲望和需要,走自己的路,我就是这么做的。当然,她处于非常脆弱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权力地位。所以这一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当她非常需要帮助时,我确实会远离她。但我仍然觉得我这样做是为了救赎。”
碍于家境,门罗甚至无法完成在西安大略大学的学业。起初,她靠着一份两年期的奖学金苦苦支撑。但当奖学金耗尽,1951年,门罗终因无力支付学费退学。不出意外的话,她日后的人生也将重复这些灰暗的境况,一遍又一遍地得而复失,如同被困在一部黑白默片里。
然而,当她拿起笔,便渐渐有了点石成金的力量。这些日常生活中的阵痛,被转化为一篇篇技艺纯熟的小说。不论是荒芜的自然,还是荒芜的生活,在她眼里,都是潜在的书写对象,小说家的眼光帮助她从现实中抽身,以便在一个更高的位置观察现实的本质。这个位置就像救生员所处的位置,在那里,小说家可以看到日常生活的平静水面蕴藏的诸多张力,看到溺水者的身上,如同果核般缓缓胀开的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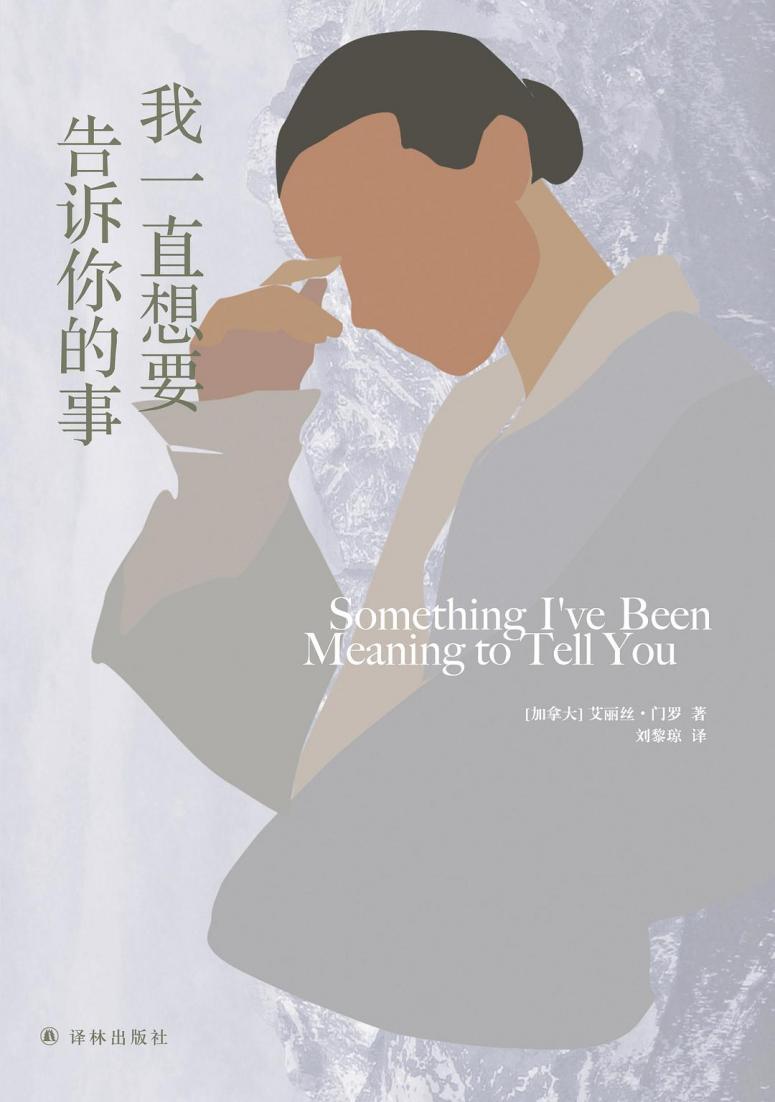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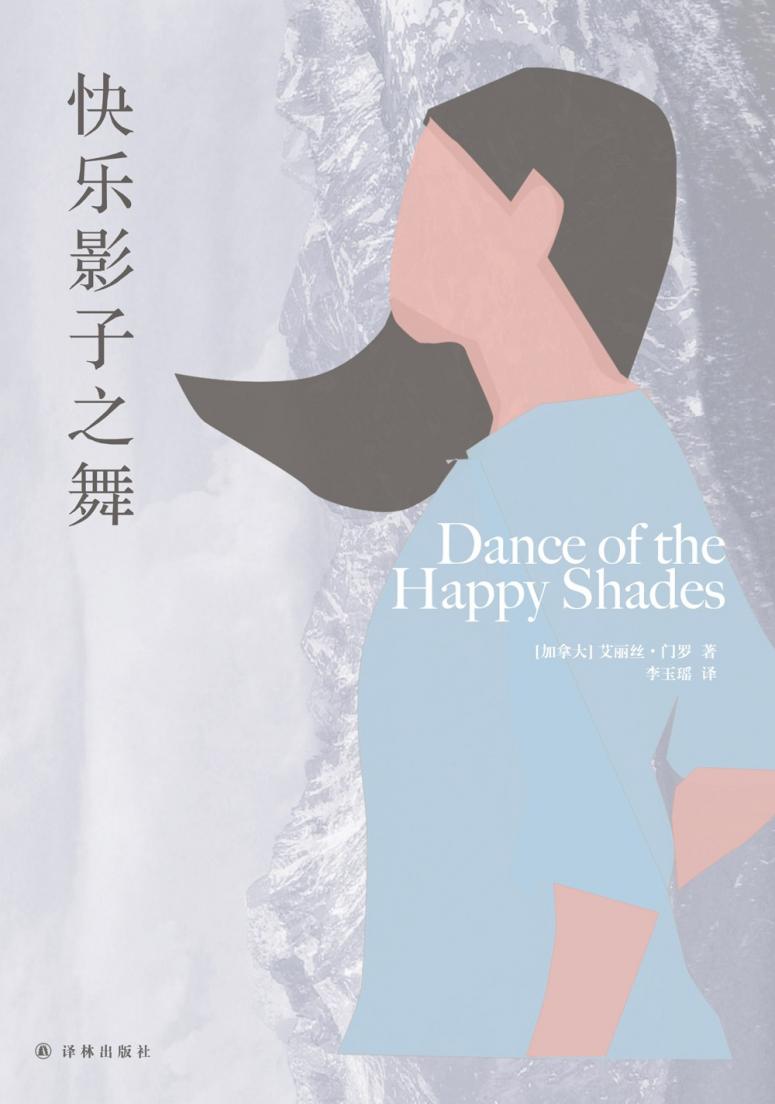
“我能写出更好的书”
这个来自偏远小镇的女孩,究竟是如何能够踏上写作之路的?在面对《卫报》采访时,门罗曾不无反讽地说道:“一个人能出生在没有人写作的地方是幸运的,因为那时你可以说,显然我比高中里的其他人写得好。你根本不知道竞争有多激烈。”
十几岁时,门罗就有练笔的习惯。1950年,她甚至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影子的维度》。不过在当时,加拿大文学很不受重视。人们普遍认为,加拿大没有独立的文学,有的只是英美的唾余。
阿特伍德1972年出版《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时,尽管已然经过战后20余年的发展,但1970年代想要谈论何谓加拿大文学依然很艰难。《生存》于2004年再版时,阿特伍德在序言中写道:“加拿大作品,即使在加拿大也都默默无闻。在行家眼里,它常被视作无聊的玩笑,自相矛盾,让人大打哈欠,或被当成虚拟甜甜圈中的那个空洞。”
我们不难想见门罗开始创作时加拿大的文学氛围。那是被阿特伍德视为“枯燥乏味”的1950年代,但同样是加拿大开始腾飞的时代。参加二战为加拿大赢得了融入世界体系的机会,这个国家将不再是被遗忘的寒冷角落。
不过,彼时的门罗并无余力关心国家的宏大叙事,被贫穷压得喘不过气。为赚取生活费,她辗转于烟草公司、餐吧与图书馆,做着时薪微薄的兼职。退学后,她的生活也没有变好。
以现代眼光看,门罗几乎过早地进入了婚姻,但门罗说1950年代的加拿大十分保守。“如果你 25 岁还没结婚,你就是个失败者。我从高中的经历中感觉到,我不是每个人的心头好。我想,好吧,有人喜欢我——真是个奇迹。”于是就在退学当年,她便与西安大略大学的同学詹姆斯·门罗(James Munro)结为伉俪。
婚后,两人迁居到西温哥华的邓达拉夫。在那里,詹姆斯找到了一份百货公司的工作。入职时,年轻的丈夫想要进入图书部门。人事告诉他,读书是赚不到钱的,他应该先从男士内衣部门的工作做起。
门罗夫妇从未放弃开一家书店的想法。攒到足够的启动资金后,1963年9月,他们搬到加拿大西海岸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首府维多利亚市,并在耶茨街开设了第一家门罗书店。这家书店至今仍在营业,只是时过境迁,它已不再是当初那间窄小的独立书店。
加拿大记者艾伦·福瑟林汉姆(Allan Fotheringham)称,门罗书店是“加拿大最宏伟的书店,也可能是北美最宏伟的书店”。如今,若我们想要造访门罗书店,就应该去维多利亚市中心的皇家银行大楼,这是它自1984年以来的地址。
站在书店门口,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高大罗马柱占满游客的视线,大团大团暖色灯光从橱窗透出来,像一件在暴雨中颤抖的斗篷。艾丽丝·门罗的文学声誉,提升了门罗书店的商业价值。尽管她早在几十年前就离开这里,仍有雪片般的粉丝来信,每日寄到门罗书店。
詹姆斯·门罗曾向媒体透露,妻子正式决定走上写作之路,正是因为她在书店轮班工作时翻阅了那些用再生纸印刷的平装书。“有一天她生气了,说,‘我能写出比这更好的书’。”詹姆斯表示,“她可以。这是毫无疑问的。”
门罗最开始选择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理由,与另一位生活在美国的短篇小说大师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别无二致。这两位作家都早婚早育,琐屑的家务劳动只能留给他们碎片般的写作时间。有时,卡佛只能在洗衣店里,将头脑中涌现的闪念记在碎纸片上。门罗也惟有在孩子午睡时,才能拥有一段完整的写作时间。但与卡佛不同的是,詹姆斯始终支持门罗的写作事业。为了能让门罗挤出更多时间写作,他会主动承担家务,去做饭,、带孩子。
“做晚饭不是詹姆斯的强项,但他会做肉丸,好吃的肉丸,而那是他唯一会做的。”门罗说,“但他还是做了,我去了书店。一开始非常困难,因为我周围都是这些书,书会让你不想写作,但我能够忽略它。”
慢慢地,门罗也发现了短篇小说的优势所在。对她来说,这一文学体裁更加浓缩,可以在短短几万字内呈现一个人的一生。短篇小说的有限篇幅,使得她可以反复修改它们。这些作品仿佛与门罗一同经历成长、衰老的过程,直到达至完美。在人生中不同阶段,她都会重写自己的代表作。小说《家》,于1974年、2006年、2014年分别推出不同的版本。《权力》则有八个不同版本。
1960年代开始,一直到与詹姆斯·门罗的婚姻结束前,门罗已创作出了一批佳作。1968年,这些作品被汇编成她首部短篇小说集《快乐阴影之歌》出版,并获得当年的总督文学奖。这是加拿大文学的最高奖项,由第15任加拿大总督、小说家约翰·巴肯,以及第一代特威兹缪尔男爵(John Buchan,1st Baron Tweedsmuir)于1937年设立。
《快乐阴影之歌》甫一出版,门罗就成为加拿大文学的一颗新星。嗣后,门罗一直保持着强劲且稳定的写作节奏,平均每4年有一部新的短篇小说集问世。
1978年,《你以为你是谁?》再获总督文学奖。门罗成为极少数两度获奖的作家之一。与此同时,她的作品也被影视界青睐,从1988年的《玛莎、露丝和艾迪》起,不断有门罗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门罗那极富地域色彩的写作,逐渐为她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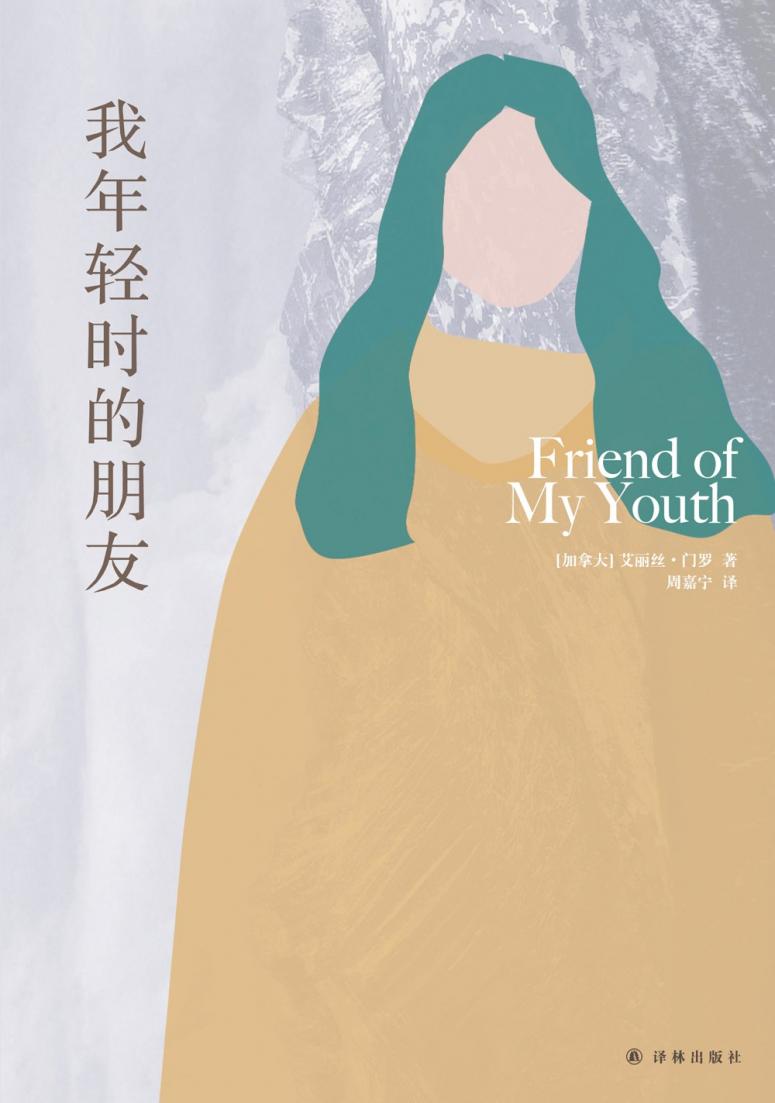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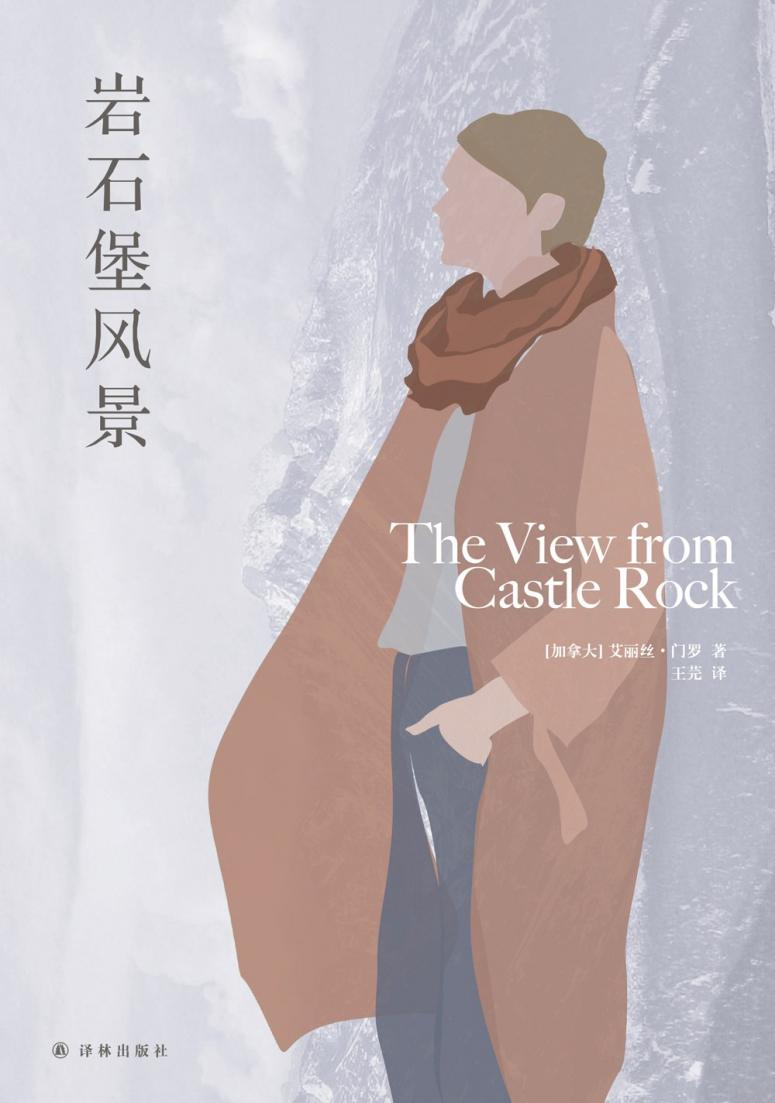
女孩与女人的生活
阿特伍德认为,门罗是“国际文学圣人”。1970年代以来,她就是《纽约客》杂志的常客,每次她的小说刊登,总能收获编辑与读者的一致赞赏。早在2005年,《时代》杂志就将门罗选为当年的百大人物。《时代》评价门罗道:“艾丽丝·门罗今年73岁,她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的小说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和尊重他们已经拥有的事物。”
声名卓著如门罗,却直到暮年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认可,这几乎像是一次追认。2013年6月,门罗获诺奖前,决定宣布封笔。这一年门罗81岁,心脏病、癌症与老年失智阻碍着她继续编织蛛网般精密的小说文本。自然,糟糕的健康状况也不允许门罗前往瑞典,故这一荣誉只能由其女儿珍妮(Jenny Munro)代为领取。
事实上,早在2006年,门罗就曾向记者坦言,写作这条路对她来说已经到了尽头。“我生命中有多少时间花在了这条路上,我还能做些什么,我从其他事情中汲取了多少精力?现在想起来很奇怪,因为我的孩子们长大了,他们不需要我在身边,但不知为何,我感觉我只活出了生命的一部分,还有另一部分我还没有活出来。”
回首往事,这位年届八旬的老作家发现,自己仍处在逃离与回归的永恒轮回之中。年轻时,门罗希冀着婚姻能够将她拉出原生环境,她匆匆变换自己的姓氏,来到这个国家的另一端,过着以往梦寐以求的城市生活。但这段婚姻最终还是无疾而终。
1950年代时,门罗曾是詹姆斯眼中的模范主妇。两人生育了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另外三个都长大成人。大女儿珍妮成为了艺术家,二女儿希拉·门罗 (Sheila Munro)和母亲一样选择了作家之路,小女儿安德莉娅(Andrea Munro)则是一名瑜伽教练。
尽管詹姆斯很多时候都表现出耐心与关怀,但这段婚姻却一直存在诸多隐患。詹姆斯是一个典型市民阶层男性,有时会显得专横跋扈。成长背景的差异,导致他与门罗的感情愈发不和睦。而1970年代北美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也使得门罗不再甘心被当作一名业余写作的家庭主妇。他们的婚姻终结于1973年。
在与詹姆斯离婚后,门罗回到休伦湖畔的故乡。她开始尝试用写作养活自己,其间不断撰稿,又在西安大略大学做驻校作家。这段驻校经历,将门罗带入了她的第二段婚姻。她遇见了大学时就认识的地理学家杰拉尔德·弗雷姆林(Gerald Fremlin)。
仅仅只是一起喝过三杯马提尼,门罗就决定与他共度余生。她的确做到了。婚后,这对夫妇一直住在位于弗雷姆林的家乡克林顿市郊区的农场里,直到2013年4月,弗雷姆林以88岁高龄病逝。
熟悉的风景再度激发起门罗的创作欲。“我陶醉于这片风景,陶醉于几乎平坦的田野、沼泽、硬木灌木丛,陶醉于大陆性气候和极寒的冬天。”她1996年给自己的小说选作序,“砖房、摇摇欲坠的谷仓、偶尔出现的有游泳池和飞机的农场、拖车停车场、沉重的老教堂、沃尔玛和加拿大轮胎,这些都让我感觉很自在。我会说它们的语言。”
重新置身于加拿大乡镇寒冷的夜色中,这个曾经的女孩如今已成为了母亲。可她究竟该如何扮演母亲这一角色?终其一生,门罗都感觉自己生活在母亲的阴影之下,她在小说《渥太华山谷》中写道:“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我的母亲。当然,她就是我想要得到的人;我踏上整个旅程就是为了接近她。目的是什么?标记她,描述她,照亮她,庆祝她,摆脱她;但这没有奏效,因为她像往常一样逼近我。”
在女儿希拉·门罗眼中,那个过分著名的作家母亲,既点燃了她写作的激情,也让她认清了自己的局限。希拉面对门罗时的复杂心絮,与门罗当年面对她那专制且有着道德洁癖的母亲时的心情别无二致。
2001年,希拉在回忆录《母亲和女儿的生活》一书中写道:“把艾丽丝·门罗当成我的母亲,这太不合时宜了,她是一个偶像……除了崇拜它、忽视它或将其打碎,我们还能对偶像做些什么呢?”
当希拉从母亲的小说中辨认出自己的形象时,她惊叹于母亲细致入微的观察与解剖刀般精准的剖析。家庭生活的内在张力,始终是门罗的主题。然而在希拉看来,母亲那双艺术家的眼睛是如此无情,以至于她的成长被灌录进母亲的文字,成为文学史的脚注。
也许正如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所写,在其十四行诗中,他曾劝谕一位贵族青年道:“你是你母亲的镜子,她在你身上/唤回了自己可爱的青春四月天。”门罗身后,她的文学血液依然在子女的血管中,在读者心里,搏动着。某种意义上,透过阅读,我们成为了她的血亲。她的生活,她的文字,将作为一份见证,告诉我们,在贫瘠与荒芜的日常中,写作仍然可以保有它古老的尊严。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