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创作生涯50周年:用写作抵抗南非种族隔离的幽灵
对已满84岁的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来说,2024是值得纪念的一年。50年前的1974年,凭借处女作《幽暗之地》,库切登上南非文坛。
彼时的南非,尚处在种族隔离时代。童年的库切见证了种族隔离时代的开始,这使得他在成年后一度想在祖国之外定居。1962年到1972年间,他前后旅居英美两国将近10年。他先在伦敦的IBM公司担任计算机程序员,一直到1965年赴美修习文献学与古英语博士学位。这段苦涩记忆,被他写进了2002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青春》。
在前途未卜的白领生涯中,《等待戈多》的作者、爱尔兰戏剧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小说,如同一束救赎之光,照彻他昏暗的未来。1969年,凭借对贝克特小说的文体学分析,库切获得了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博士学位。在此之前,他已开始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任教,并希冀通过这一教职申请到美国永久居留权。
愈演愈烈的反越战运动,打破了库切的规划。1970年3月,他因参与布法罗教职工反对警察入驻校园的和平请愿而被捕。针对包括库切在内的45名教职工的非法入侵罪指控,最终于1971年撤销,但这件事让库切本就艰难的居留申请雪上加霜。
1971年末,库切不得不回到南非。翌年,他成为了母校开普敦大学的英语系讲师,并且在教学工作之余完成了一部从布法罗带回开普敦的长篇小说。这部初试啼声之作便是《幽暗之地》,一部由两篇中篇小说连缀而成的长篇。在《幽暗之地》中,越战的残酷与南非早期殖民史互为参照。库切的旅美经历,让他能够用一种冷静中立且国际化的视角,切入南非的历史与现实。
自此,库切笔耕不辍,逐渐成长为当下英语文坛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在1980年代写作的《等待野蛮人》《迈克尔克·K的人生与时代》等一系列作品,使其获得国际性的声誉。
《幽暗之地》出版25年后的1999年,经历了1994年民主转型的南非已然决心走出种族隔离的阴影。这一年,库切完成了颇具争议的长篇小说《耻》。这部小说,如今被批评界公认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亦是他对转型时期南非诸多社会危机思考的结晶。
在大洋彼岸重新思考南非
和许多美国大学一样,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有着让人惊叹的图书馆馆藏。库切正是在该校图书馆的一个角落,发现了那份蒙尘的档案,它记叙着库切家族的一位祖先——雅各布斯·库茨(Jacobus Coetsé)的故事。雅各布斯出生于1730年,是库切家族在开普殖民地开枝散叶后成长起来的第三代成员,也是家族中第一个离开开普敦、探索南非内陆的人。
自1652年荷兰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好望角建立开普殖民地起,管理该殖民地的荷属东印度公司仅将此地当作贸易站经营。东印度公司不希望人们向南非内陆殖民,在他们看来,那片土地荒凉且野蛮,没有开发价值。但随着养牛业的发展,开普人口持续增长,世居于此的荷兰牧民逐渐被广阔的内陆地区吸引,不断向其中渗透。
雅各布斯是这些拓荒者中走得最远的人。他一路走到奥兰治河流域,深入如今的纳米比亚南部。在那里,他见到了一种他称之为“骆驼马”的生物。它们摇晃着纤长如探照灯光柱的脖子,啃食树顶的叶子。现在,我们称这些生物为长颈鹿。
从内陆回来后,雅各布斯来到了一个武器展上。他讲述着在那片严酷土地上遭遇的一切,讲述着那里奇异的生物,以及“黄皮肤,长头发,身穿亚麻布衣服”的原住民。
雅各布斯的经历,引起殖民地总督瑞克·图尔巴(Rijk Tulbagh)的兴趣。1761年,图尔巴特准进行了一次官方远征,由雅各布斯担任向导和翻译。雅各布斯·库茨关于这两趟旅程的描述,被当地官员记录了下来。200多年后,当后代库切读到它,首先想到从这份冷淡的官方叙述中剥除的部分。在他看来,祖先的这两次远征残酷且充满种族主义意味。
越南战争阴影下,彼时身处美国的库切,较之往常更能理解殖民主义的残酷性。表面上看,是一种冷战意识形态在支持着美国的越南战略,但真正为这一战略提供养分的,乃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在库切的小说里,这种傲慢有时近乎虐待狂。
不过,与殖民时代不同,1960年代是一个年轻人集体反叛的时代,而他们的反叛最终为在越南的这场永无止境的战争悲剧画上了句号。到1967年,民调显示,57%的美国人反对越战,甚至连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也表示:“美国必须小心,不要用自己的历史、政治、文化和道德标准来解释发生在他国的事件。”
反战游行、黑人民权运动,将美国社会撕裂成针锋相对的各个派别。库切正是在美国内部一片动荡的时刻,完成他关于贝克特的博士论文的。尽管美国正陷入其现代历史中最紧张的时刻,库切仍希望获得一个教职,以留在美国发展文学研究事业。得克萨斯大学并没有空缺,他的老师便让他去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寻找机会。
布法罗是一座海港城市,位于纽约西北方400英里处。1968年,此地约有53.3万人口。与库切求学的得克萨斯州一样,布法罗的主流民意相当保守,罗马天主教徒占人口比例达50%以上,连续多年的经济低迷,更是催化出底层市民当中的民粹主义与排外倾向。
后来,在面对记者采访时,库切这样回忆1968年的美国:“空气中有一种偏执,尤其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容易被认定为知识分子、左翼人士、世界主义者,因为得克萨斯州和布法罗的普通百姓憎恶这几类人。”尽管如此,当库切在1968年进入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任教时,这所大学仍尽力维持着自创办起就一直存在的学术自由传统。
库切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事实上,在因签证问题被迫离开美国之前,他始终保持着对这所大学的忠诚。如同一座孤岛,库切和他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事们漂浮在偏执与狂热的浪潮之中。这种孤立感让他们逐渐凝结成一个共同体。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布法罗大学内学生的反战抗议活动也日益频繁。在这危急时刻,布法罗大学校长马丁·梅耶森(Martin Meyerson)非但没有直面问题,反而给自己在1969至1970学年休了长假,将学生与校方之间日渐激化的矛盾扔给毫无管理经验的副校长彼得·F·里根(Peter F.Regan)。
1969年11月,里根宣布,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采取可能的必要的外部或内部安全部门进入的措施”,以制止校园内无节制的暴力对言论自由的损害。在学生与教职工们看来,里根邀请警察入驻校园的强硬措施,不过是以维护言论自由之名,行威权统治之实。这些措施不但没有缓和校园内的情势,反而使之进一步恶化,直至1970年2月25日星期三,暴力冲突导致校园内27人严重受伤。最终,20名学生被勒令停学。
作为回应,3月15日中午12点45分,包括库切在内的45名教职工,在校长办公室内静坐抗议,要求警察撤离校园。里根丝毫不理会教师们的诉求,他拒绝出面协商,只是让当时的副校长爱德华·多提(Edward Doty)转告静坐的教师们,若他们不在5分钟内离开,就会因擅闯罪被捕。

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
他们就这样安静地坐着。库切在其中显得尤为安静,他淡漠得好像一尊石膏像,就留在此处等待警察将他带走。出于尊重,他们没有被铐上手铐。翌日,这45名教师被集体控告藐视法律和非法入侵罪,面临1年刑期或1000美元罚款。库切成了一个可能触犯美国法律的人。
1970年3月的事件,让他彻底丧失了留在美国的可能性,但他的写作生涯正是在1970年的布法罗开始的。这是布法罗馈赠给他的礼物,动荡的空气催生出库切作为作家的才华。1983年在面对《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詹妮弗·威廉姆斯(Jennifer Williams)的采访时,库切回忆道:“1970年1月1日,在纽约州布法罗市,我开始写自己的第一本小说。1970年我的新年计划就是写一本书。我对自己说,如果不在今天坐下开始写,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坐下来写?”
彼时,他没有想到,两个月后,他就将被卷入这场反战运动之中。布法罗校园内严酷的日常为《幽暗之地》提供了舞台,在这之上,库切将他往日所阅读到的关于南非早期历史的口述材料,与当下的政治现实糅合在一起。历史变成了映照现实的镜子,现实则变成了重估历史时的坐标。两者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这部长篇小说最初的经纬。
但库切要真正完成它,仍需等到1974年,等到他回到哺育他长大的开普敦。而那遥远且缄默的非洲风景,将重新润泽他的笔尖。
在世界最边缘的地方写作
1985年8月13日,在给友人希拉·罗伯茨(Sheila Roberts)的信中,库切回忆道:“我在美国连续待了六年,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我想原因有两个:一、我与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童年回忆,因此缺乏他们成长中形成的文化厚度;二、我对任何美国景观都没有感觉。”
他热爱为其提供自由宽松学术环境的布法罗大学,但身为一个来自地球最南端土地的异乡人,库切未必喜欢布法罗冗长的冬季与肮脏的积雪。常常是昨天的雪尚未化尽,又添了新雪,一片素白层层叠叠地将城市封缄起来。
他也不习惯大都会的生活节奏。在给朋友的信中,库切抱怨,仅仅在纽约待了16个小时,他就“再也不想见到那个地方了”。
故而当1971年回到南非,他的心中仍有对这片故土上风物的眷恋,这份眷恋多多少少中和了他对1970年代南非政治状况的厌恶。“人在其一生中只能爱一道风景。”库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们可以欣赏很多景物,但那种深入骨髓的感觉只能属于一个地方。”
在库切看来,南非的美是属于永恒的,仿佛从造物伊始就从未变更。在2002年的一档访谈节目上,他提及开普敦附近一处尚未被开发的海滩。海滩名为迪亚斯,它的美便是极具南非特性的:“这条海岸线的美丽并不是一种安静的美,它崎岖不平且危险,它并不符合初来定居者对美的感知。在他们的日记中,他们不断地用‘狂野’来形容这段海岸线。当然,这对他们这些航海家来说是危险的,到处都是散落的沉船。但是你可以摆脱现实,撤退到这里来,它存在于时间之外,也被剥离于历史之外。”
漂泊在外,图书馆就是他的暂憩之所。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奥斯汀或布法罗,库切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徜徉于书海的机会。徘徊在异国他乡的图书馆中,他总是会留意那些17、18世纪游客所写下的开普游记。
如今他回来了,可以不再透过这些朦胧的文字想象开普,而是重新置身其中。一个现实问题亟待解决,因为长期失业,初回南非时,库切几近破产,却还要养活他的妻子和孩子。
在库切亲戚的帮助下,库切一家暂时在一间空房子里安顿下来。这间房子位于马莱斯代尔农场里,邻近库切儿时生活过的百鸟喷泉农庄和卡鲁农场。它年久失修,没有水电。羊毛养殖产业衰落后,农场的原主人德里克·苏恩(Derek Scheun)就搬离了此地。
库切一家在农场里过着简朴的生活。每天,库切和妻子菲利帕都要去砍柴、挑水、用煤油炉做饭。他们买不起家具,他们的孩子只得睡在地板上,以报纸为床。一家人在这荒废的农场里,度过了难得的悠闲岁月。
菲利帕后来在发表于《淑女》杂志的一篇游记中回忆道:“在春季和秋季,卡鲁农场的生活是很理想的。天气既不太热也不太冷,花在春天开放,在秋季凋谢。这个世界是如此美丽,没有任何无聊的感觉。”
在马莱斯代尔农场,库切一面重新开始《幽暗之地》的写作,一面在南非的大学中寻找合适的教职。很快,他的母校开普敦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1972年,库切成为了开普敦大学的英语系临时讲师。
库切重回开普敦大学时,英语系的领导层正发生人事更替。系主任盖伊·豪沃思(Guy Howarth)于1971年退休,继任者大卫·吉勒姆(David Gillham)的学术旨趣与豪沃思截然相反。
吉勒姆坚持由利维斯(F. R. Leavis)开创的“实用批评”方法。他希望英语系的课程专注于英语经典文学的教学,不要把课时浪费在他认为完全不值得教的南非文学上。
库切回忆道:“豪沃思教授的继任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校工清除和烧毁豪沃思教授多年留下来的成吨的学生的散文和诗歌作业。这些材料原本塞满了办公室的所有橱柜。豪沃思教授设计的荣誉证书、学位课程、长长的阅读书目、对参考书目和文本研究的重视,都被抛出了窗外,取而代之的是稀疏的利维斯教学大纲。”
巧合的是,在布法罗大学,库切是唯一一个有非洲背景的人;而在开普敦大学,他则是该校唯一一位在美国受过学术训练的讲师。因此,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南非,库切因其身份或因其特立独行,而始终处于边缘。他也渐渐习惯了在边缘中写作。
而如果说南非自然风景的特性是粗砌而严酷,那么南非在1970年代、1980年代面临的局面同样是严酷的。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让南非内外交困,面临国际制裁。198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各地都不断有学者、政要为释放曼德拉而奔走呼告。拥有近200年历史的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则宣布终止向南非提供短期贷款。其他组织纷纷效仿,这导致南非融资环境变得异常恶劣。
国家内部,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愈发难以调和。边陲之地南非,最终宿命般地陷入孤立无援。这个国家和库切一样,必须在边缘之中寻找自我。这一痛苦的寻找之旅,还需耗费一代人的时间。
新南非如何从“耻”中救赎自身?
就像金砂必须淘洗才能见真容,将库切的小说放在时代舞台上加以检验,仍是有必要的。作家创作小说时所面对的时代,就像一只筛子。我们展读小说时,就需要将小说放到这筛子上,以筛去叙事所夹带的杂质,如此,才能见到作家在创作时真正的介怀所在。
1999年,库切出版了长篇小说《耻》。这 部小说获得了当年的布克奖。这是他自1983年因《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获奖以来第二次夺得此项荣誉,也使得他成为布克奖史上首位两次获奖的作家。此时距离南非1994年普选已过了5年,而4年后,库切就将为南非拿下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边缘如今蜕变成了中心。自1980年代以来,围绕库切的创作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话语体系。他的小说成为无数评论与论文的来源。到1990年代中后期,库切已拥有了无可置疑的国际性声誉。
对于一个南非作家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在他之前的南非文学界,几乎都只有地方性的影响。库切却凭借其小说精炼、干脆的语言,极富实验性的结构方法,让南非英语文学走向世界。
1996年,在获颁纽约斯基德莫尔学院名誉博士学位时,致辞人罗伯特·博伊斯教授(Robert Boyers)认为:“J·M·库切是一位小说家、政治思想家、评论家、理论家、语言学家和权力解剖学家。”
他对库切说道:“您的作品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生动而内敛,直接而简约,既有风格又有知识分子的勇气。您的创作来自南非的经历,带着其特有的压力与执着,您没有像持不同政见者那样在写作中大谈特谈道义和虚假的英雄事迹,您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谈论特定历史所发挥的力量,同时又不局限于单一的时间或国家。”
《耻》正是这样一部小说。它的创作,始于曼德拉当选总统翌年的8月19日。
自《幽暗之地》始,库切就习惯在无人打扰的清晨时分开始一天的创作。他会先在稿纸上用钢笔写作,以便随时修改,然后再将这些文稿用电脑誊清。他的每份手稿都会详细标注创作和修改时间,我们可以利用它精细还原库切创作的每个节点。
8月19日清晨,库切从抽屉中取出一沓开普敦大学考试用纸,开始将《耻》的开头行诸笔尖。在录入电脑前,他所写下的文稿就如同一堵为爬山虎所覆盖的墙,字里行间攀满了红色修订符号。仅仅第一段,库切前后改动就有13次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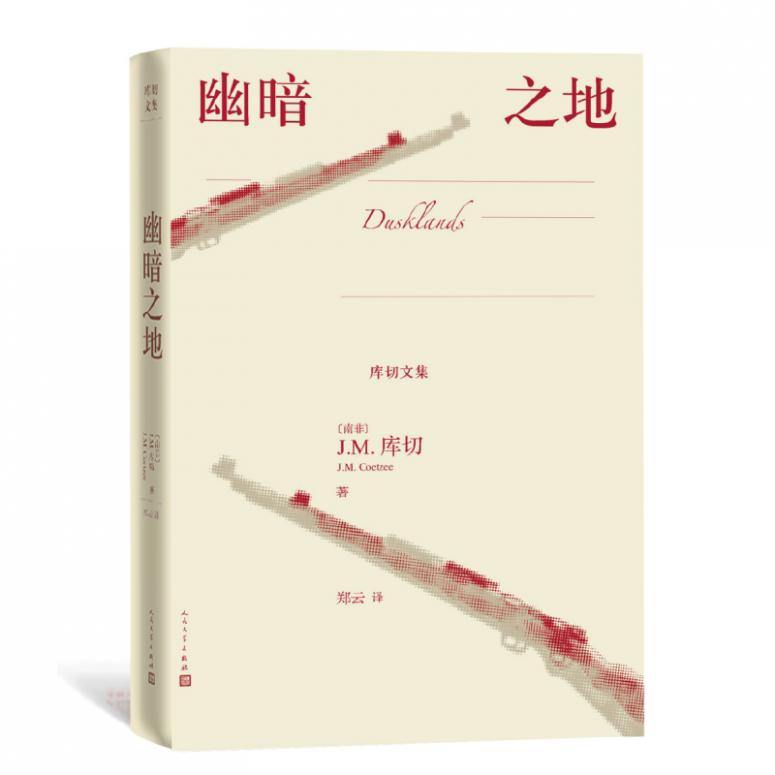
《幽暗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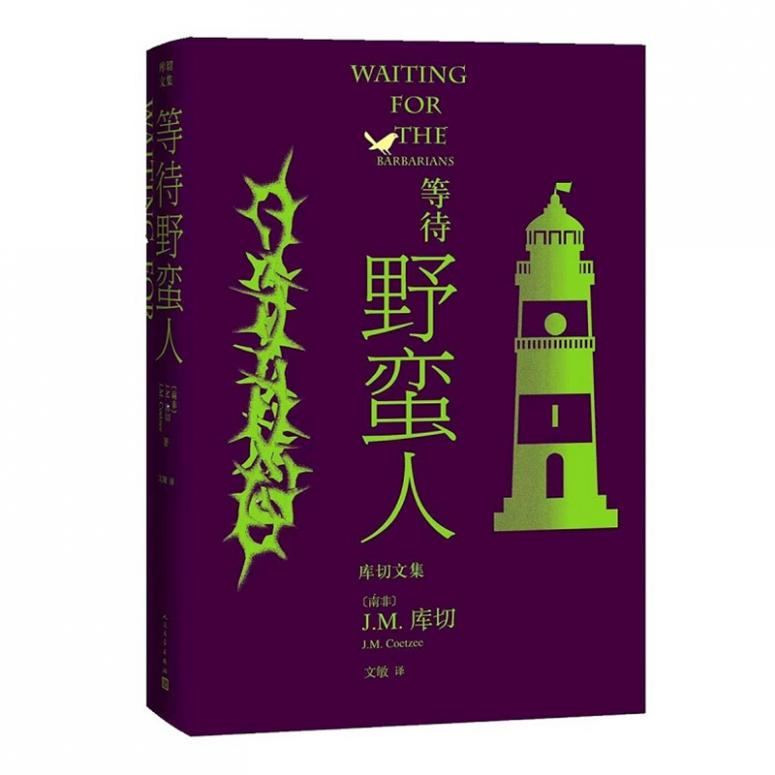
《等待野蛮人》
库切的精心构思很快就有了回报,《耻》的出版引起了评论界的巨大反响。这部小说几乎抛弃了之前库切惯常使用的后现代叙事技巧,而是切实用淡漠中立的线性叙述去切入一个有关罪与罚的故事。
小说主人公卢里原是开普敦的一名大学教授,他因与学生间的性丑闻而被驱逐。起初,身败名裂的卢里离开城市,和女儿露西平静地生活在农场里。不久,露西被一群人强奸。关于这群人的族裔,库切故意写得非常含混,仅仅暗示他们可能是黑人。露西因为这次经历而怀孕,但她拒绝引产,也拒绝出面控告袭击她的人。她告诉父亲卢里,自己已决意要和这个孕育在体内的“耻”共同生活下去。
小说最后,露西说了这样一段话:“不错,我同意。是很丢脸。但这也许是新的起点。也许这就是我该学着接受的东西。从起点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不是从‘一无所有,但是……’开始,而是真正的一无所有。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
如何理解《耻》,在刚刚经历了转型阵痛的南非几乎成为了一个政治命题。南非批评家大卫·阿特维尔(David Attwill)指出,卢里在关于他性丑闻的听证会上拒绝忏悔的行为,似乎暗含着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批评,在卢里眼中,“从制度上驱动的忏悔与和解,是对私人生活的另一场攻击”。
在其编辑的《遭遇〈耻〉》一书中,美国作家比尔·麦克唐纳(Bill McDonald)介绍:“《耻》的批评者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南非作家,他们指责库切在国家进入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时刻,刻意唤起旧的种族主义恐惧与种族紧张关系。”
甚至,在2000年4月5日提交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口头报告中,《耻》被非国大视为一部种族主义的作品。在他们看来,小说关注的似乎是非洲白人的无家可归感,以及黑人在后殖民时代不受控的“野蛮”。
对此,库切的好友、哈佛英语系教授、后殖民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向记者表示:“《耻》是一部开缝儿的作品,而不是一部缝合的作品。”
在给朋友的信中,库切提到,南非的内阁正为如何理解《耻》而争论。但面对政治性的非议,他却始终保持沉默。或许,《耻》已达到其目的。透过这部小说,一道原本就存在,但却一直被忽视的裂缝出现了。唯有撕开它,这个国家才得以在直面“耻”的同时重塑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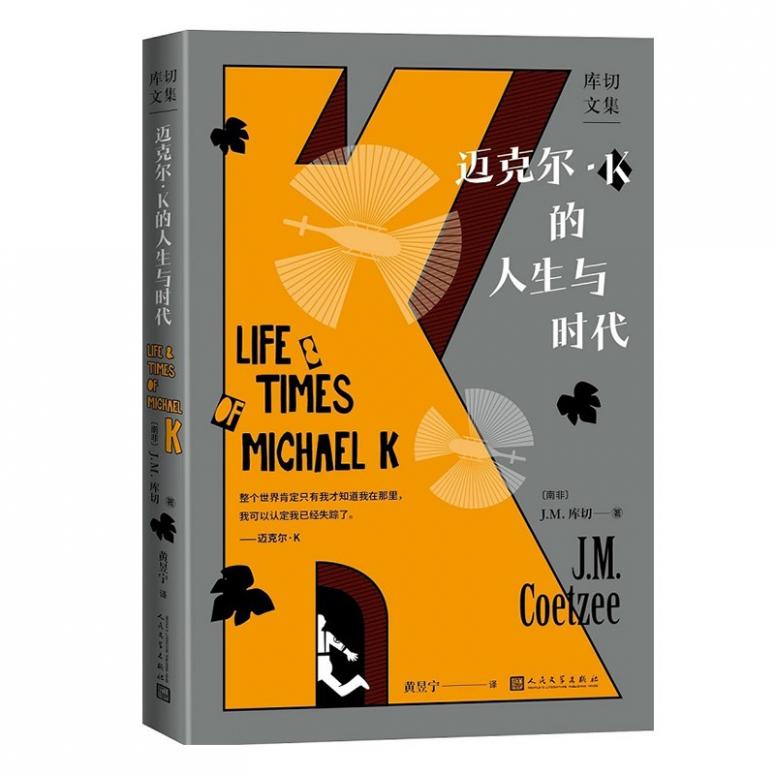
《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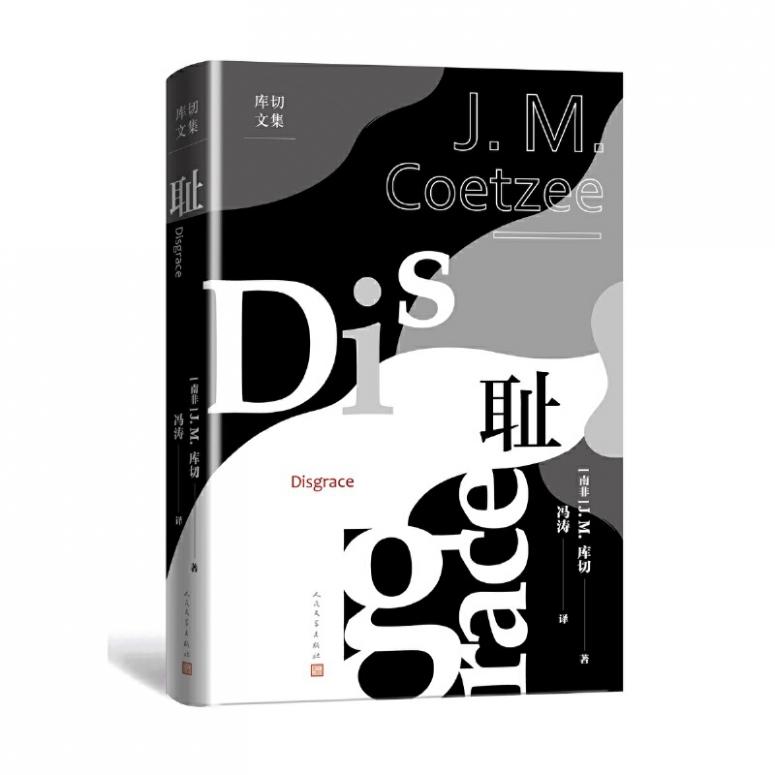
《耻》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