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中国为方法认识世界:列文森55周年冥诞
在55年前的1969年4月6日复活节假期,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失去了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这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讲座教授约瑟夫·列文森,在俄罗斯河(Russian River)上同家人一道划独木舟时落水身亡,享年48岁。
列文森身后,影响力仍持续增长。列文森留下的少量著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学走上学术道路。因此,1987年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简称AAS)设立了“列文森图书奖”,以纪念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其中不少获奖图书已成为经典。
本年度的列文森奖亦已于2月评出,韩书瑞的《碧霞元君:十一至二十世纪华北的熟悉感与物质文化》获奖。不过,2023年前,相较列文森的学术地位,中文世界对列文森的译介仍很不充分。
如今,我们终于得见列文森著作的全貌。2023年末至2024年春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华盛顿大学讲座教授董玥主编的《列文森文集》。这套书包括其生前作品、遗著,以及纪念文集《列文森: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
而夺走列文森生命的俄罗斯河是旧金山湾区第二大河流。其下游在春夏季时水流平缓,被公认为休闲胜地。惟在冬季,这条河才会变得汹涌、混浊。
列文森一家来此地露营时,大雨刚过。俄罗斯河水位上涨,列文森依旧坚持按计划与他的两个孩子同乘独木舟漂流。他们的独木舟遇上暗流,如枯叶般倾覆了。他的两个孩子穿了救生衣,很快便游到河中岛上等待救援。列文森虽谙习水性,也抵挡不住寒冷的疾流。他最终消失在孩子们的视线中。
几天后,搜救队在距离事故现场9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他的遗体。这场意外,为列文森本该更璀璨的学术生涯画上休止符。他的葬礼,于4月13日在他工作生活过的伯克利及剑桥举行。追思会并不意味着追思的结束,而仅仅意味着追思的开始。他的同侪,诸如专研二十世纪中国史的莫里斯·迈斯纳,以及后来成为AAS主席的罗兹·墨菲等人,都认为“列文森的史学著述内容丰富、意旨深远,但尚未获得充分赏识,也未得到充分理解”。
于是,他们决定发起“约瑟夫·列文森纪念基金”,并编撰一部文集,来为列文森的史学成就做永久的纪念。这年末,在多方努力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设立了“约瑟夫·列文森纪念基金”,纪念文集的编撰工作亦于1969年夏启动。
在同侪看来,列文森的作品是一座丰碑。他在1953至1969年间提出的诸多开创性概念,如天下与国家、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经典主义与历史主义、科学与儒学等,至今仍在被使用、被反刍。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列文森著述的时代性。列文森的一些预设,例如他为明清时期思想潮流所描绘的图示,已可以被1970年以来的史学发展证伪。
列文森对“儒家中国”的描绘,很大程度上以“清代中国”为坐标。倘若55年前的那场事故没有发生,列文森很有可能会修正他的观点,正如他的导师费正清所做的那样。不过,列文森的作品依旧值得被一再阅读,不单只作为史学作品被阅读,更作为文学作品被阅读。
对文学与音乐的热爱,渗透在列文森笔尖。他的书中没有干瘪的论述,隐喻与修辞渗透了他的文字,他像创作小说与交响乐一样构造他的历史叙述。这也是为何列文森被同侪赞誉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
选择成为犹太人
1920年6月10日,约瑟夫·列文森出生在波士顿的一个犹太裔家庭。犹太人身份认同影响了列文森的学术旨趣,使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学术方法,这种学术方法迥异于当时流行于美国的汉学或区域研究所采纳的方法。
历史学家安格斯·麦克唐纳在1970年发表于《关注亚洲学者通报》的《历史学家的求索》一文写道,汉学的诞生,一开始“只是为了满足对异国情调的好奇心,以证明西方世界有能力掌握任何话题”,区域研究则出于功利意图,“主张中国对于西方有正面的重要性,应当根据‘知己知彼’的原则来加以研究”。
在麦克唐纳看来,有时这些学派的观点会变得野蛮,因为它们都预设了西方的优越性,暗含对当今世界秩序的支持。
麦克唐纳举塞缪尔·亨廷顿为例,这位后以“文明冲突论”闻名的知名政治学者,为美军轰炸越南乡村的行径背书,认为轰炸有利于推进“城市化”,进而促进越南“现代化”。
但对于列文森,中国不只是他的研究领域,也是他认识世界的方法。在他看来,中国古人的“天下”观念,是一种普适性的观念。古代中国并未被塑造为一个国家,而是被塑造为一个世界,这一点在西方只有罗马帝国可与之比肩。
透过中国,列文森思考着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同样贯穿犹太人的流散史。而在融入民族国家与重新成为犹太人之间,列文森选择了后者。
列文森逝世3个月后,他的遗孀罗斯玛丽·列文森在清理遗物时,在一沓复写纸下找到了一个残破的文件夹。文件夹里散落着一些手稿、讲座笔记、剪报与IBM打孔卡。翻阅这些纸页,它们像蝉受伤的翅鞘一样发出来自过去的微响。在这些文件中,罗斯玛丽发现了一篇名为《犹太身份的选择》的遗稿。草草读过后,她便发现了这篇文章的价值,决定在纪念文集中将之发表。
在遗稿中,列文森写道,“犹太人总是重申,其与自身不可分割的人民,必须保持可见性,并在所有的世代中历史性地生存下来”。
列文森注意到全球化进程里文化调和的倾向。民族将在其中逐渐融解,所谓民族性,将沦为一种异域风情。成为犹太人却是要反对此种趋势。
他写道:“犹太教不是溶于混合溶液的一滴水,不是生活的调味品,不是历史的一个主题。这是一种生命的选择。”
据罗斯玛丽回忆,列文森逝世前,除在准备一部全新的三部曲外,也在为一本关于犹太教的书收集资料。私下里,列文森称这本书为他的“退休之作”。《犹太身份的选择》一文,便是其开篇。
列文森对犹太身份的强调,时常会让他的同侪感到尴尬。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对犹太人仍抱有成见。列文森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该校历史系仅有一位犹太裔教授,即德国流亡学者恩斯特·康托洛维茨。
人们习惯将作为史学家的列文森与作为犹太人的列文森分开。但他从犹太经验中提炼出来的诸多主题,如“历史与价值、特殊与普遍、分离与同化等张力关系”,也同样见诸他的中国研究。
在现代世界里成为一个中国人,在他看来,和成为犹太人一样是一项沉重的使命。这意味着,你必须拒绝以超然的态度,从外部审视犹太文明或中华文明,而是将这些文明的要素融入你的骨血,让它们塑造你,维持你的可见性。
罗斯玛丽在《犹太身份的选择》一文的前言写道,列文森“理解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和流散犹太人所面临的困境,这或许启发了他敏锐地体察到华人在中国或者在南洋所面临的类似问题”。
终其一生,列文森都没有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而他对中国的学术兴趣,恰恰发端于二战战火中的南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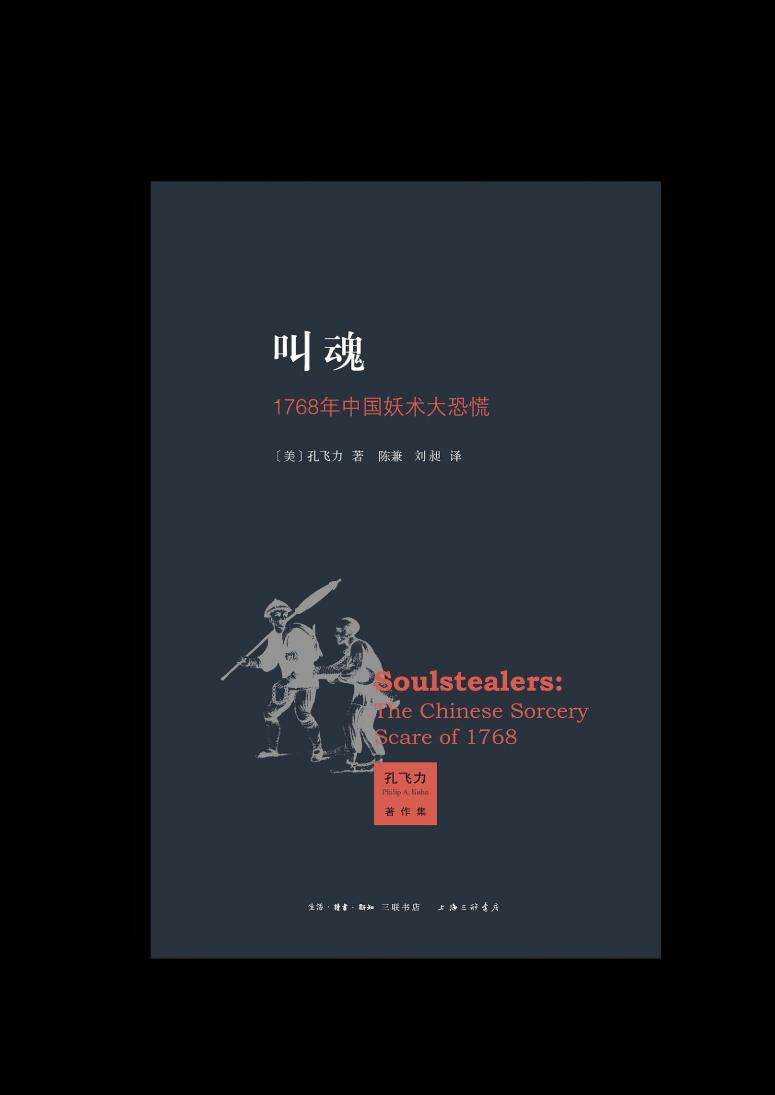


列文森的起点:相遇费正清与太平洋战争
列文森素来是一位优异的学生。1937年9月,列文森考入哈佛大学。1938至1939学年、1939至1940学年中,他与一位影响他一生的人物相遇了。
这两学年里,列文森住在柯克兰宿舍楼。哈佛的住宿系统别有特色,每栋宿舍楼都会有一名舍监,这些舍监通常由哈佛的资深教授担任。柯克兰宿舍楼的舍监,正是20世纪美国汉学先驱之一的费正清。
费正清年长列文森13岁,列文森读本科时,他也处在自己学术生涯的开端。不同于列文森,费正清曾在清华大学进修,考察中国的海关贸易,师承历史学家蒋廷黻。
当费正清于1939年与日本学专家赖肖尔在哈佛开设东亚文明课程时,美国的东亚研究仍在萌芽阶段。历史学系投入到欧洲与美国的学术资源,远胜中国。这让费正清感到困惑,一片拥有四亿人口的大陆,仿佛消失在美国学界与政界的视野中,而那片土地上发生的战争将改写20世纪的世界史。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费正清与列文森的人生拐点。战争使得美国重视起中国研究。费正清在战时加入战略情报办公室担任情报员,亲身参与中国高层政治的辉煌经历提升了他的地位。加上他勤奋写作,使其迅速崛起为北美中国研究学界执牛耳者。
1955年,费正清在哈佛建立起东亚研究中心。到20世纪中叶,费正清的学生占据美国大学中绝大多数汉语、汉学相关的职位,形成所谓“哈佛学派”。列文森正是其中之一。
与费正清的战时经历相仿,1942年2月,甫一从哈佛毕业,列文森便应征入伍,加入美国海军预备役。这年,他以二等兵身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科罗拉多大学学习日语。
列文森的语言天赋,让他在一年时间内迅速掌握了日语。随即,他作为情报员被派往太平洋战场,随同新西兰陆军与美国海军,在所罗门群岛及菲律宾等地作战。1946年3月,他以中尉军衔复员,重回哈佛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
战前,他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古典学与欧洲史。而在太平洋诸岛屿上,他度过许多沉寂的夜晚。那时他便会回想起他所受的日语训练以及柯克兰宿舍楼里费正清的耳濡目染。于是,在涛声催化下,对中国的兴趣开始在列文森血液中发酵。
要理解那些如同花瓶碎片般掺杂在假名中的汉字,必须理解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互动与纠缠。在为战争学习日语的那一年里,列文森发现了日本的汉学传统。仿佛从中国的脊背之后望向这个国家,他透过日语文献逐渐拼凑出一个古老中国的形象,尽管彼时它仍朦胧得像一声哀叹。
他想了解中国真正的样貌,勘测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之间的断裂。这项事业,值得他和他的老师费正清一样用一生去完成。

约瑟夫·列文森
列文森在香港:冷战阴霾下向东方逆行
多年以后,在为即将出版的繁体中文版《列文森文集》作序时,列文森之子托马斯·列文森会回想起他最初的中国印象。这种印象始于列文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弥漫着烟草味道。55年后,当他再度翻看列文森办公室中的藏书时,那股烟味仍隐约地滞留在书页间。
在家人与同侪记忆里,列文森是幽默的,这从他待人接物的方式可以见得。列文森的办公室里有一张虎皮地毯。托马斯·列文森回忆这张地毯:“当然还带着巨大的虎头,每当六岁的我走进那间办公室,都会胆战心惊地盯着它黄色玻璃般锃亮的眼睛和那些可怕的牙齿,好像随时会被它一口吞掉。”
来这间办公室拜访列文森的访客,甫与列文森会面时,往往由于敬畏其在学界的盛名而变得拘谨。所以,列文森把这张虎皮地毯放在开门的弧线之外的位置,以免它惊吓到访客。不过,这也让很多没有第一时间注意到这张地毯的客人被虎头绊倒。于是,列文森便会借机讲起这张地毯的来历。
原来,这是列文森身为猎人的岳父猎回的三只老虎之一。岳父将这三只猎物分别送给他的三个孩子。罗斯玛丽·列文森不喜欢将这吓人的物什摆在家中,列文森便将它带到办公室安置起来。每次有访客留意到这虎头,他都会向他们绘声绘色地描绘起岳父打猎时的场景。交谈的气氛变得融洽起来,人们会注意到,列文森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对话者。除了基于博士论文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外,他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是在对话中产生的。
对话发生的场所,可能是课堂、研讨会与讲座,也可能是伯克利的咖啡厅与露台。列文森的学生、历史学家魏斐德仍记得1965年秋天,一个据他所言“阳光闪烁的下午”,在学生餐厅外的露台上,列文森和他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讨论着一篇即将在美国历史协会午餐会上发表的讲演稿。魏斐德没有忘记那天在露台上所看到的山峦,这些山峦似乎比平时更贴近他的眼睑。随着他与列文森的对话,一个又一个崭新的主题开始显影。
正如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所做的一样,列文森的学术工作提升了中国研究在伯克利历史学系中的地位,使之与欧洲研究及美国研究并列,成为伯克利历史学系的三驾马车。然而,在列文森学术生涯的开端,差点与伯克利的历史学教职失之交臂。即使有费正清的极力推荐,伯克利也是在长久的迟疑之后才最终决定聘请列文森。
与费正清相比,身为中国研究者,列文森缺乏在中文世界生活、学习的直接经验,这无疑会使他的学术资历显得不那么可信。因此,费正清决定将列文森送到香港,期待着香港对他的冲击 ,以及他对香港的回应。
在获得研学资助后,列文森于1951年初抵港。冷战的阴霾笼罩着香港,出于对香港被战火波及之可能性的恐惧,美国大使馆建议美国公民撤离香港。列文森几乎是唯一在这个紧张时刻逆行前往香港的美国人。
1月25日,在给费正清的信中,列文森写道:“我们真的在香港安顿了下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九龙……这个城市看起来自信满满,特别是如果你刚从士气消沉的马尼拉过来。当局宣布了城市营建计划,让一台打桩机在市中心不停运作。”
在香港,他见到了一位名叫马鉴的学者。马鉴生于1882年,在香港大学中文系当系主任。1925年,马鉴曾远赴哥伦比亚大学,在杜威门下修习教育学。归国后,马鉴起初在燕京大学任教,并兼任国文系主任。他任内为燕京大学延聘了一批新知识分子,包括俞平伯、钱玄同、冰心等人。同时,他与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人过从甚密。
列文森希望,能够在马鉴引荐下找到一位导师。他很快融入香港生活,体验着此地的学术氛围。3月22日,他再度去信给费正清,信中写道:“我和罗斯玛丽搬到了太平山上的一座白色小别墅里,这座房子曾经是标准石油公司的。我就在这里和我的厨师、女佣、半个园丁(另一位先生拥有他的另一半),以及我们的两条跑来跑去的狗——一条阿尔萨斯母犬和一条西德腊肠犬待在一起。我对现在的情况完全满足了。”
列文森从当时香港学界获得的启发,譬如“中国现代艺术史上传统派、折衷派与西洋派之间不断变化的潮流”,被他写进其最重要的著作《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
一代代中国研究学者的薪火相传
沿着《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开创的道路,一代代中国研究学者不断补缀列文森未完的宏大图景。这正是“列文森图书奖”存在的因由。受列文森学术兴趣启发,该奖项侧重评选“促进中国学术与更广泛的知识话语世界之间的对话”的作品。
“列文森图书奖”自创办起,每年都会评选出两本用英语书写的中国研究著作。一本聚焦20世纪前的中国,一本聚焦20世纪后。“列文森图书奖”在当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颇具权威性,其评选出的不少著作已经成为史学名著。
在1987年颁出的首届“列文森图书奖”中,列文森学生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拔得头筹。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国防等诸多领域,宏观把握明亡清兴的历史更替。
魏斐德希望透过清初对帝国秩序的重建,描绘出近代前期中国社会中发生的重大变化。作为列文森的第一代学生,魏斐德的著述受到列文森的直接影响,史料却更加扎实、详尽。后来,他与孔飞力、史景迁一起,被誉为美国“汉学三杰”。
孔飞力同样获得过“列文森图书奖”的褒奖。1992年度的“列文森图书奖”,颁给他于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叫魂》讲述了乾隆年间的一起“叫魂案”。1768年春,一则谣言出现在浙江德清。一些流窜的施法者,能够通过剪断受害人辫子,或对受害人衣服名字施法的方式,吸取他们的精气。最初受理此案的地方官员,认定“叫魂”不过是无稽之谈。但很快,民间便开始出现自发“猎巫”的暴力行为。谣言几乎在1768年10月传遍全国,人们陷入一种集体性迷狂中。最终,乾隆下令在全国境内严查妖术,经过3个月的调查之后,军机处认定“叫魂案”只是一则谣言。
孔飞力通过一个小切口,揭示出乾隆盛世隐藏的危机。他认为,乾隆时期是中国转向近代的关键节点,晚清的溃烂并非仅仅始于鸦片战争。乾隆年间,中国人口爆炸式增长,民众的生存条件却日渐恶化。这种趋势演变成“叫魂案”中弱者对更弱者的暴力,可以说是对底层的一种权力补偿。
当然,“列文森图书奖”获奖作品中,不止有上述这些专注呈现明清中国宏观图景的著作。1970年代末以来,西方学者开始对中国的地方史尤其是城市史感兴趣。2006年的“列文森图书奖”获奖作品——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所著的《说扬州:明清商业之都的沉浮》便体现了这样的趋势,她用细腻的笔触为所热爱的城市作传。
早逝的列文森,会欣慰于他所开创的这一学科如今的进展。一代代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和他一样将中国作为一种方法,透过中国的透镜认识这世界,也让世界认识中国。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