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与新生:《魔戒》之父托尔金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场病因祸得福,为世界留下经典文学作品。若不是突患“战壕热”而被转移,托尔金很可能死于“战地绞肉机”。英国军方披露的有趣细节,储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数字化档案里。
托尔金是《魔戒》《霍比特人》和《精灵宝钻》的作者,被誉为现代奇幻文学之父。改编自其作品的电影《指环王》影响了不计其数的青年,托尔金研究在西方也早已成为显学。2024年,英国学者汉弗莱·卡彭特的《托尔金传》中译本出炉,这位曾面见、采访过托尔金的作者,揭开了世纪作家托尔金更为真实、复杂的面貌。
托尔金为何能创作出《魔戒》等奇幻经典?半个世纪以来,许多学者都对此做出诠释,这其中,战争和友谊是两个绕不开的原因。从《魔戒》到《霍比特人》,友谊是支撑着主角们战胜绝望的强大力量。《魔戒》与《霍比特人》是奇幻传奇,也是关于友谊的颂歌。而托尔金在《魔戒》第二版前言中却写道:“1918年,除了一人幸存,我所有的朋友都死了。”
那些曾渴望改变世界的青年
青年托尔金有三位好友:克里斯托弗·怀斯曼、罗伯特·吉尔森、杰弗里·史密斯。
托尔金年少时失去父亲,他和母亲住在伯明翰,家境并不算富裕。当他就读于爱德华国王学校时,怀斯曼与他因为文学趣味和阶层上的相似而熟识。
和怀斯曼一样,托尔金对语言兴趣浓厚,他的母亲梅贝尔对此功不可没。母亲在托尔金4岁时教他读写,介绍拉丁语的基础知识。在国王学校,托尔金爱去图书馆,图书馆在名义上由助理教员负责,实际交给了一些高年级学生管理。根据《托尔金传》记载,1911年的学生图书馆员包括托尔金、怀斯曼、吉尔森。他们意气风发,挑战秩序。图书馆禁止学员在此喝茶、吃点心,他们便偷偷这么干,甚至把用过的茶叶藏到清洁工的桶里。吉尔森是校长的儿子,怀斯曼认为招揽他入伙有利于提供一层身份上的庇护。
吉尔森又邀请了他的好友史密斯,后者后来是牛津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1911年,他们建立了一个非官方的半地下组织,命名为茶社和巴罗社团(Tea Club and Barrovian Society,简称T.C.B.S.)。这年假期,他们把讨论文学的阵地转移到牛街巴罗百货商店的茶室,这个名字也微妙地传递出年轻人对于“规矩”的反叛。
T.C.B.S.的成员相信,文学能够改变社会,这听上去有点像中国古人说的“文以载道”。但托尔金和同伴并不将这种“启蒙”寄望于国家或君主的推动,而是盼望从自身出发,联结同伴,建立小共同体,在促进彼此的同时,一点一点地通过实践去影响社会环境。
他们彼此交往不是基于财富和地位,而是审美、思想与相似的愿景。他们盼望缔造一个开放与联结彼此的环境,让彼此在面对世道艰险时有所依托。正是这段经历缔造了托尔金前半生最珍贵的友谊。怀斯曼多年后回忆:“后来我成为学校《编年》杂志的编辑,要列出获得各种荣誉的人物名单。如果有人是我们组织的成员,我就在他名字旁打个星号,并在页脚的星号注释里写,‘这人同时也是T.C.B.S.的成员’,这代表了我们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负责整理托尔金遗稿的小儿子克里斯托弗,他的名字正是来自于父亲对于好友怀斯曼的思念。1924年11月21日,克里斯托弗出生于英国利兹市,他是托尔金家的第三个儿子,也是《魔戒》《霍比特人》最忠实的读者。《托尔金传》记载:克里斯托弗在聆听魔王、精灵、半兽人(奥克)的故事中长大,托尔金认为这个小儿子敏感、急躁、倔强、自律、顽皮,像极了少年时期的自己。
根据托尔金父子的往来书信,1937年,13岁的克里斯托弗因为心律不齐卧床在家,托尔金要求他为刚出版的《霍比特人》挑错,挑出一个错误就奖赏两便士,克里斯托弗列出一连串的错字、印刷错误,寄给了出版社。
1943年到1945年,克里斯托弗在南非接受军事训练,托尔金频繁给他寄信,不断把《魔戒》的书稿寄给他。在表达思念之情的同时,也是在征求儿子的修改意见。克里斯托弗还是“吉光片羽”社(Inklings,“迹象社”)最小的成员,这个社团最知名的人物是托尔金和C.S.路易斯。路易斯与托尔金的友谊与破裂,也是被读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但至少在当时,路易斯是《魔戒》最忠实的拥趸。他也曾笑言:克里斯托弗朗诵《魔戒》时“要比父亲好”。
母亲是托尔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托尔金对友谊的珍视与童年有关。
他的家族世居于伯明翰,但他父亲被委派到南非担任一家英国银行的经理,托尔金在布隆方丹出生,南非巨大的狒蜘蛛令他印象深刻。造化弄人,在他年满三岁时,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回英国伯明翰省亲,父亲却身患疾病,不久后因风湿热猝然长逝。
托尔金随母亲居住在萨候尔村庄(Sarehole),那是《霍比特人》中夏尔郡霍比屯的原型。在小说世界里,霍比特人是一脚掌宽大的精灵小矮人,他们与世无争,性格朴实,热爱安稳的田园生活,却终究难逃巨变。而在19世纪末,萨候尔村人烟稀少,覆盖有绿地和沼泽,是一片自然气息浓厚的地方。
托尔金人生中第一位启蒙老师,是他的母亲。梅贝尔女士通晓拉丁语、法语、德语,她鼓励托尔金发现爱好,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天意弄人,梅贝尔1904年因罹患急性糖尿病而去世,早早失去亲人让托尔金饱受孤寂折磨,他因此珍惜友谊,渴望家庭般的氛围。16岁那年,他遇到了伊迪丝·玛丽·布拉特,他们都是早早学会独处的孤儿。
1909年夏,二人坠入爱河,但托尔金的监护人摩根神父充当了拦路虎。他认为这会极大地影响托尔金的学业,况且伊迪丝信奉新教,而摩根神父立志将托尔金培养为天主教信徒。
摩根神父禁止二人见面和通信。有一回,托尔金违反禁令,摩根神父威胁中断他的大学生涯,托尔金和伊迪丝因此不得不中断联系。但在此期间,他们都还牵挂着对方。在托尔金21岁生日那天,他再一次给伊迪丝写信,这一次,他决定向她求婚。可伊迪丝说,她已经跟另一个男人订婚了,因为她以为托尔金不会再来找她。
托尔金没有放弃,他与伊迪丝约定在一座铁路桥下见面。在他热烈的攻势下,伊迪丝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她不愿让自己带着悔恨步入一段婚姻。尽管男方家人勃然大怒,伊迪丝仍决定退还订婚戒指,郑重声明与托尔金结婚,甚至为此宣布自己昄依罗马天主教。
托尔金承认,伊迪丝就是《精灵宝钻》的灵感源泉,他曾在书信中写道:“我从未称呼伊迪丝为露西恩——但她就是后来成为《精灵宝钻》核心的那个故事的源头。故事最初诞生于约克郡小村鲁斯的一处开满野芹花的林间空地……”
友谊与爱情丰收之际,战争浩劫悄然袭来。1914年,一位青年枪杀斐迪南大公夫妇,引发连锁反应。这年夏天,牛津校园空空荡荡。8月4日,英德宣战。3天后,英国战争部长基奇纳勋爵签署全国总动员令。托尔金在T.C.B.S.最好的三位朋友,均于当月参军。

英国陆军军官托尔金。1916年7月到10月,托尔金在法国前线,直到患战壕热。
大战改变了一切
1914年12月的圣诞假期,T.C.B.S.核心成员团聚于怀斯曼家中。托尔金将这次聚会称为“伦敦会议”,那将是他们倒数第二次团聚。
他在两年后写给史密斯的信中感慨:“T.C.B.S.被赋予了火种——作为一个并不孤独的团体——这些火种注定会点燃一盏新的明灯,或者,它会去做相同的事情,重新点燃世界上那一盏旧的明灯。T.C.B.S.为了上帝和真理而存在,我们会用更为直接的方法点燃火种,而不是在战争中丢掉性命(这场战争中,我们这边的所有人,无论善恶站在一起,共同抵抗邪恶)。……那次(伦敦)会议之后,我找到了一种方式来表达长期郁积的那些东西,并开启了巨大的可能性——我一直都将这归功于我们四个人短短几小时内产生的灵感。”
彼时的托尔金尚未写作中洲神话,他在好友的鼓励下研究语言、积极写诗。他编撰的《昆雅语词典》日后演变为《魔戒》中高等精灵的昆雅语,他创作的诗歌《仙境海岸》已经出现了维林诺的意象。在T.C.B.S.同仁中,托尔金是最后一个入伍的,因为他的家境在四人中最普通,他担心中断学业可能造成巨大损失。
托尔金参军的时间是1915年6月,他在惠廷顿·希斯(Whittington Heath)的兵营训练,被任命为兰开郡燧发枪团第十三营的少尉军官。吉尔森和史密斯已经成为陆军下级军官,怀斯曼则加入了海军。
9月,吉尔森从一场流感中康复,获准短期休假。他决定奔赴前线前去探望托尔金,并发电报叫上了怀斯曼和史密斯,聚会地点在托尔金驻扎地附近的利奇菲尔德。这就是他们最后一次团聚。
学者加思在《托尔金与世界大战》中记录道:“聚会当天,吉尔森和史密斯参观了塞缪尔·约翰逊故居博物馆和大教堂,之后与托尔金、怀斯曼一同入住乔治旅馆(George Hotel)……与此同时,在法国北部,一场战役预示了T.C.B.S.中三人的未来,英军……发起了一次灾难性的进攻,以至于当进攻者转身撤退时,已经屠杀了近八千人的德国机枪手最终因为怜悯而放下了枪。”
1916年7月,索姆河战役爆发,托尔金还只是一名信号官。史书将这场持续四个月的壕沟战称为“绞肉机”,在这场恐怖战役的第一天,大约19000名英国士兵死在德军机枪下,6万多人受伤。整场战役过后,双方伤亡共130万人,其中英法联军伤亡近80万人,却未能实现预期中的大推进。
索姆河战役打响之前的6月25日,吉尔森曾给父亲写信,描述一座被战争摧残的花园重新出现自然的生机:“飞燕草、吊钟花、矢车菊,还有各种颜色的虞美人,疯长一片……这是战争的破坏所创造的仅有的美好事物之一……”
7月1日,吉尔森在进攻当天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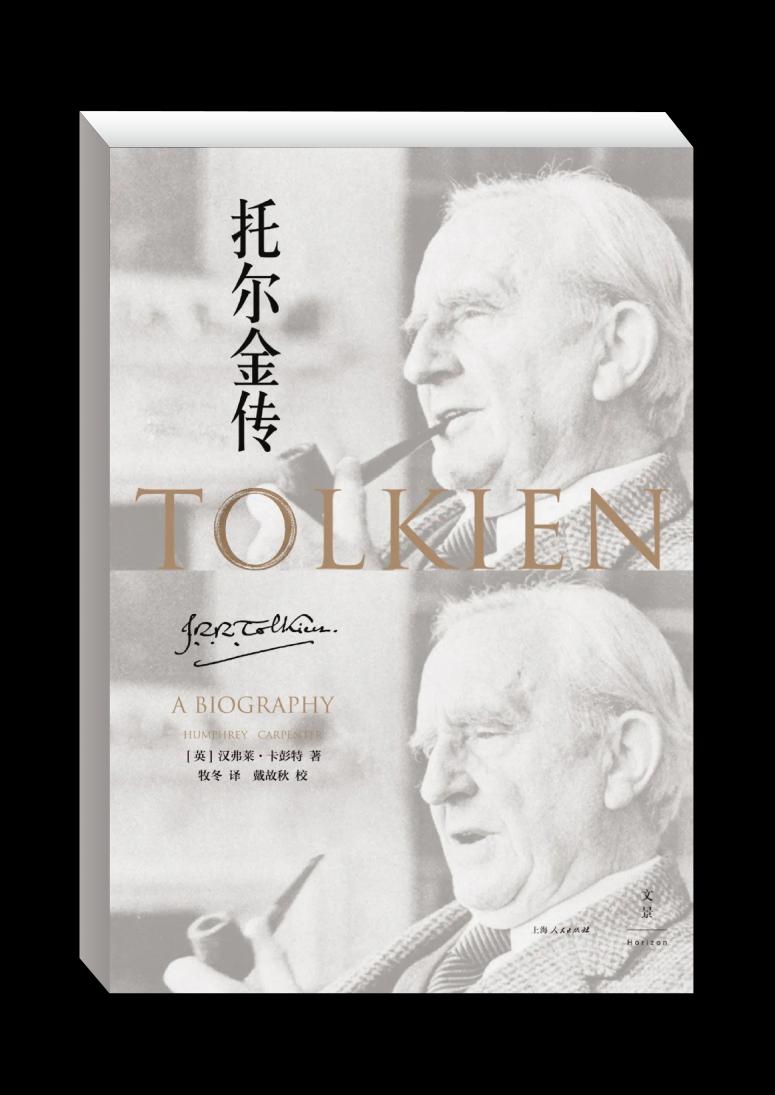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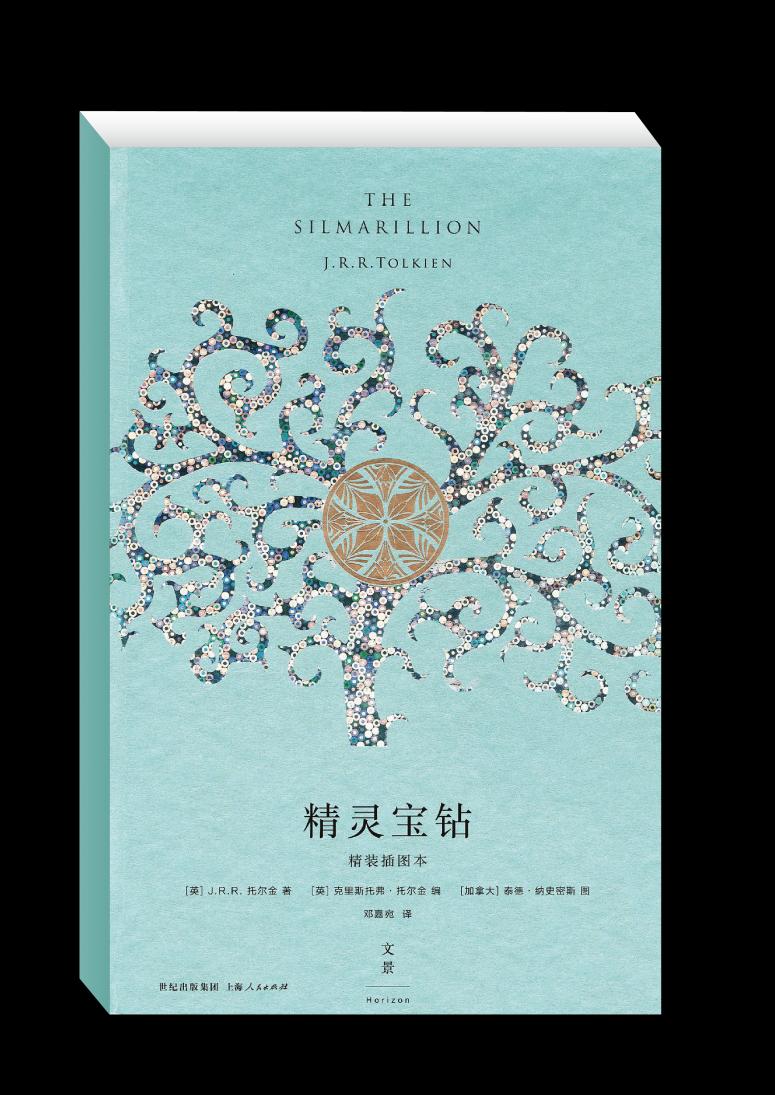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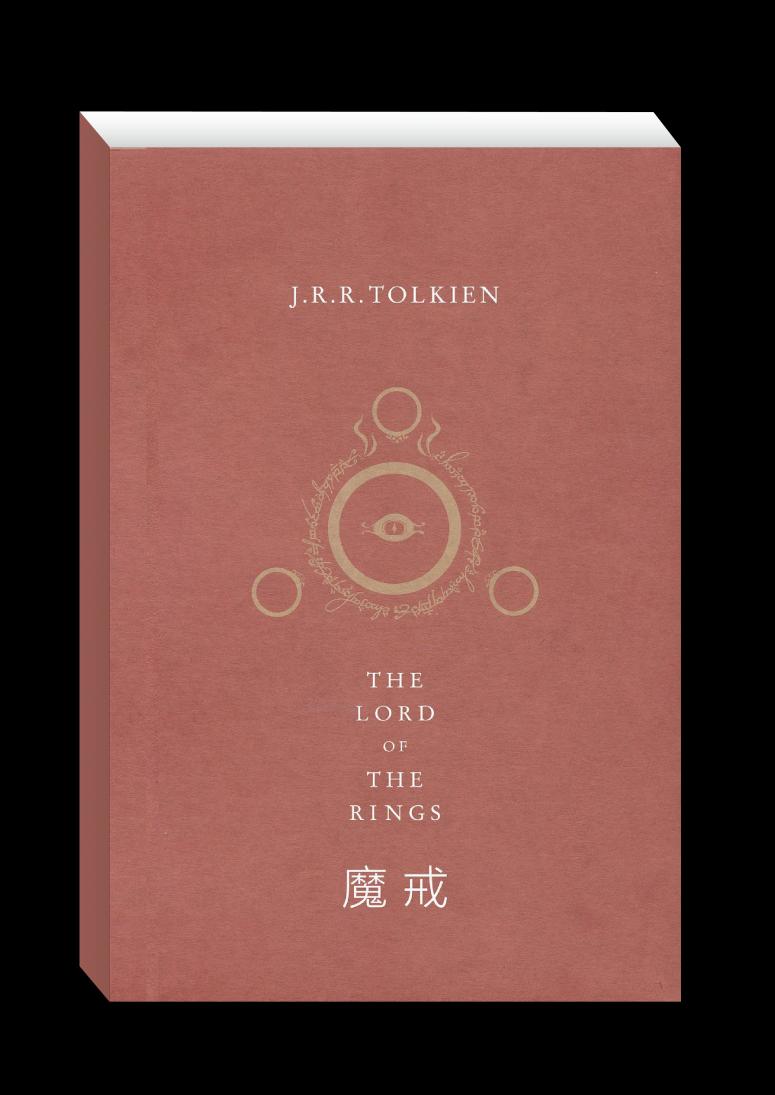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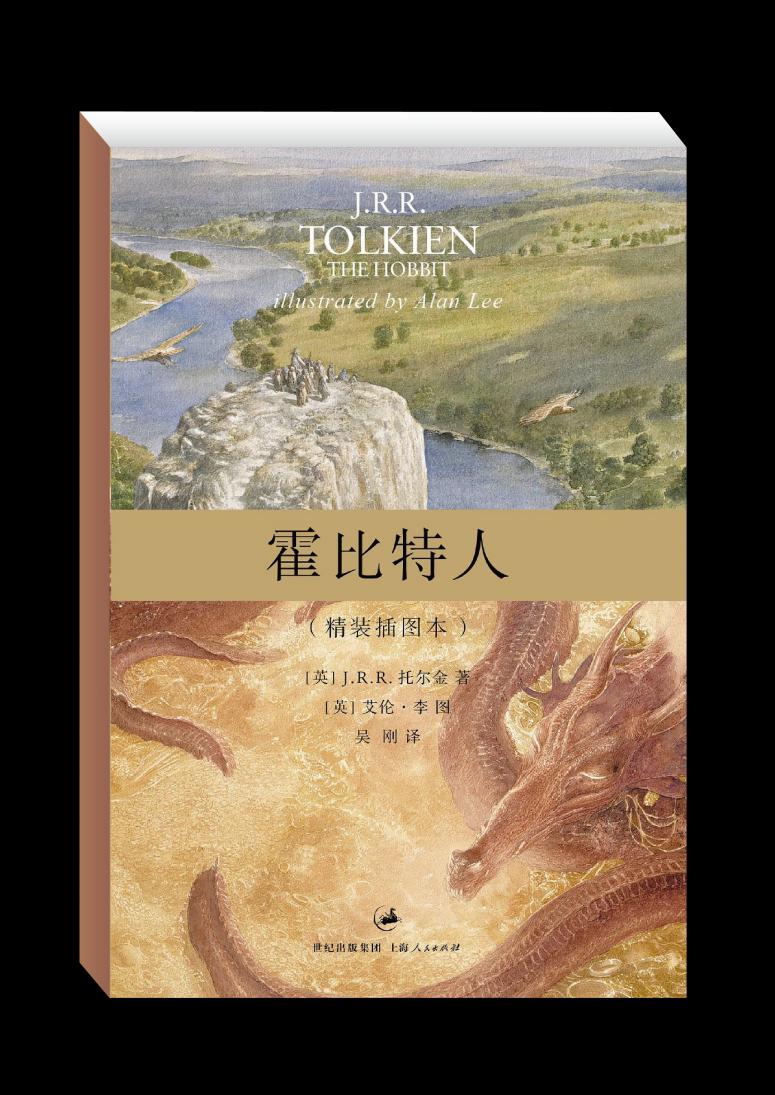
愿我们都能活着迎接更好的岁月
托尔金没有第一时间知道好友的死讯。战争中断了通讯,他们在暗夜中茫然。
7月15日,他从战场上回到营房,史密斯来信告诉他吉尔森的死讯。他回信给史密斯:“我感觉(T.C.B.S.)不再属于一个完整的团体。说实话,我觉得T.C.B.S.已经结束了。”史密斯回复:“T.C.B.S.没有结束,也永不结束。”
此时,托尔金也给伊迪丝写信。他在和妻子订婚后就被安排去法国前线。为了告知自己的位置,他在信中使用了一种墨点密码,伊迪丝能通过密码知道他的位置。
这年10月,托尔金因为战壕热而暂时撤出法国。这是一种由虱子传播并导致发烧的疾病,患者因此头痛、出现皮疹、眼睛发炎、腿痛。1916年10月28日,25岁的少尉托尔金被送至救护站。两天后,他被转移到编号22的救护队,11月8日被送回英国。
托尔金担心另外两位好友的安危,他不知道战争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英国并非幸存之地,德国轰炸机跨过海峡,先后在伦敦和赫尔市投下炸弹。
托尔金的心境日后投射于《魔戒》卷六第五章的开头:“刚铎之城全城都笼罩在怀疑和极大的恐惧中。在一些人看来,白昼并不意味着多大希望,每个早晨他们都在等候噩耗,对他们而言,美好的天气和明亮的太阳似乎只不过是种嘲弄。”
1916年12月,当托尔金康复出院时,怀斯曼致信:“史密斯已于12月3日阵亡。”
此前,史密斯曾写信给托尔金,鼓励他在创作神话传奇的路上继续走下去。史密斯仿佛预见了自己的死亡,他说:“亲爱的约翰·罗纳德,愿我们都能活着迎接更好的岁月……我本来还想写更多,但时日无多,你恐怕也必须将此作为绝笔。”
1918年,除怀斯曼外,托尔金的好友已全部阵亡。
1916年底,托尔金正式开始写下整个中洲神话体系中的第一个成型故事。这个故事最初名为“失落的传说”(Book of Lost Tales),中译名又叫《刚多林的陷落》。那之后,他在神话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除了大众耳熟能详的《魔戒》《霍比特人》,还有托尔金本人最看重,由他的儿子克里斯托弗编辑、整理,于1977年出版的《精灵宝钻》。
在1939年应邀于圣·安德鲁斯大学发表演讲《论仙境奇谭》(On Fairy-stories)时,托尔金旗帜鲜明地指出:“童话故事首先不是有关精灵、仙子这些神奇生物,而是关乎‘奇境(Faerie)’,即精灵、仙子所栖居的领域。这个领域所含更广:天地日月,草木鸟兽,无所不包;甚至人类自己。”
真正的童话是关于“奇境”的故事,而创作的关键在于如何创造、呈现那个“奇境”。这篇文章俨然是托尔金对其写作方法论的概括。“中洲”世界就是他所创造的“奇境”,从语言到地图,再到人物的名字,托尔金推敲每一个细节。像杰出的诗人推敲用典和韵脚,他让读者置身于信以为真的虚构,相信这些故事在奇境之中可以发生。
“要开启奇境之旅就须心怀谦逊和纯真”,托尔金认为童话具有幻想、复苏、逃避、慰藉四种价值,童话能够重新激活读者的经验,让孩子们看见更多可能,让大人们短暂找回尘封已久的“童心”。
1955年,托尔金在一封信中自陈,他的神话创作是为了给他出于爱好所发明的语言打造一个故事背景:“语言的发明是(小说的)根底;那些故事都是为了给这个语言提供一个世界,而不是相反。”
他也坦白了《魔戒》创作背后的民族主义冲动:“我只会把这些传奇故事献给英格兰,我的祖国。它们应该具有我想要的那种语调和品质,有些清凉和澄澈,使人想起我们这边的‘氛围’(是英格兰、欧洲西北部的气候和土壤:不是意大利或爱琴海,也不会是东方)。”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托尔金起初是将《魔戒》作为一个新语言的容器,也是他献给祖国的情书。恰如丹麦有《贝奥武夫》,托尔金也希望英国拥有属于自己的英雄传奇。但是逐渐地,这种爱国情怀被更加博大、玄思的情感所包裹。他探寻神话故事与宗教、信仰、真理之间的关系,他相信写作具有跨越国界的力量。一部悠长深邃的神话故事,能够凝练人类世界的局部真理。
命运经常以离奇的方式冲击世人,又以玩笑的方式赐予恩典。事后回看,托尔金的一战岁月就是这样的历程。他最好的朋友相继在战场上死去,祖国和欧洲大陆在毁灭的阴影之中,他本人却屡次大难不死。1918年,他本该重新回到法国前线,如果按照这个命运轨迹,他可能会死于一战结束前夕,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就不会是《魔戒》《霍比特人》作者,而是一个死于一战尾声的倒霉士兵。
结果临上战场前,胃炎袭来,托尔金转道在布鲁克兰兹军官医院疗养,时长三个月,其间体重锐减12公斤。之后他又转移到布莱克浦的疗养院,就是在那里,他听到了大战结束的新闻,可他最好的朋友再也回不来了。
在《论仙境奇谭》中,托尔金写道:“在其神话——或者说奇境——的情境中,这是一种突如其来、奇迹般的恩典:人们从不指望它会再次发生。它并不否认灾难、悲伤和失败的存在:这些可能性对于解脱的喜悦来说必不可少;但它拒绝(你可以说罔顾现实证据)普遍的终极溃败,因此它是一种福音,让人一窥那种喜悦,那种超越世界之墙局限的喜悦,与悲恸一样能让人不禁潸然泪下。”
某种意义上,一战摧毁了托尔金的过去,也锻造了他的新生——巴罗茶社的岁月因好友死去而黯淡,但巴罗茶社的精神被延续了下来。从《霍比特人》到《魔戒》,托尔金都不厌其烦地用故事来传递正直、勇气、信仰和爱。他肯定自由的可贵,提倡“善之共同体”的必要。当邪恶降临中洲大陆,顽强的个体结合在一起,绝不在黑暗笼罩时缴械。
或许,正是因为见证了太多悲剧,托尔金才不愿在虚构中以悲剧收尾。他希望珍视友谊的人得到报偿,善良的霍比特人得到恩典。在战后百废待兴的氛围里,托尔金的叙事也暗含着重建之意。在与怀斯曼的通信中,他写道:“对我来说,宗教、人类的爱、爱国的责任,以及对民族主义的强烈信仰,都是极其重要的。”
因此,如果直面真实的托尔金,他一方面有保守、民族主义的一面,另一方面,他是一个笃行“建构”而非“解构”的作者,他始终渴望唤回人之上的价值尺度。在高调宣扬上帝已死、神话已死、个人主义成为潮流的二十世纪,托尔金其实是一个文学的异类。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