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谈美国出版业的前生今世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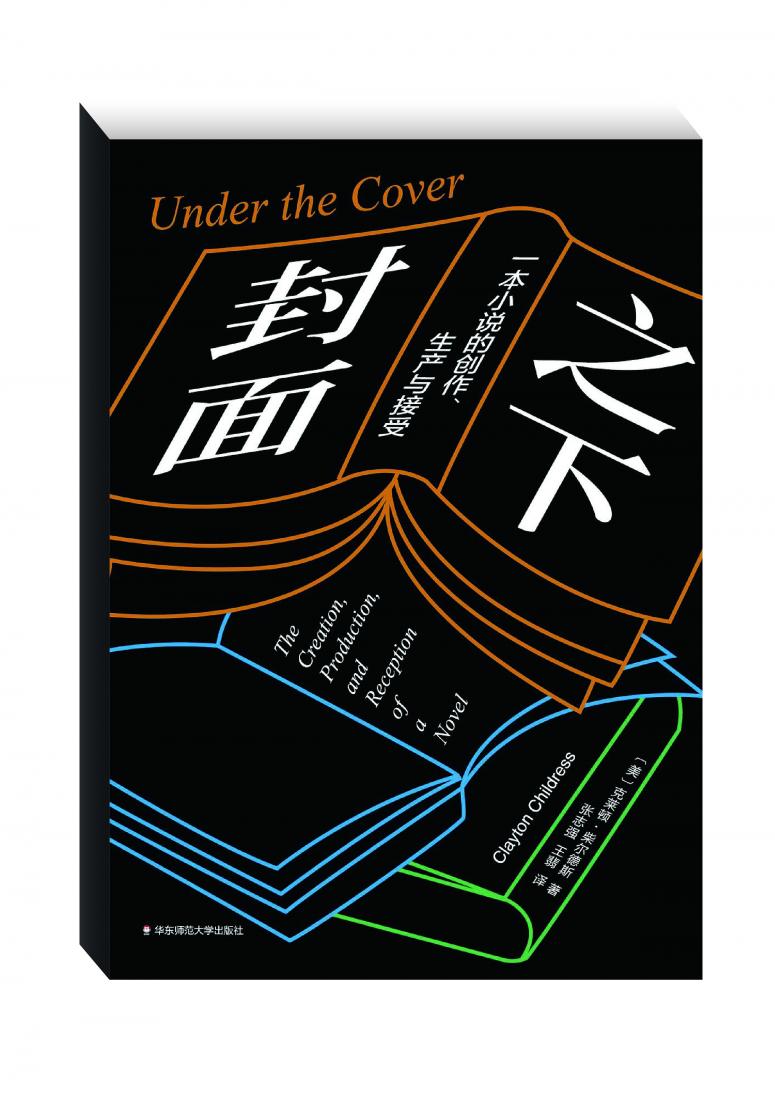
从手稿一路来到读者们身边,一本小说的出版,需要经历创作、生产、接受三大场域。理想情况下,如果这部小说想要成为成功的出版品,就需要在这三个截然不同的场域间保持平衡。
透过聚集美国作家科尼莉亚·尼克森的长篇小说《贾勒茨维尔》在这三个场域中的表现,美国社会学家克莱顿·柴尔德斯的《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以下简称《封面之下》)为我们呈现了当下美国出版业的一个精细的剖面。
在克莱顿看来,《贾勒茨维尔》这部书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出版故事。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单可以看到美国文化产业的诸多秘辛,亦能窥见文学如何在不同场域之间的张力中被形塑。
而《贾勒茨维尔》的故事背后,有着一个自浪漫主义时代就一直被追问的巨大疑难问题。那就是文学是否必须服膺于文化体制的要求,不论此体制的形成,是因为逐利社会的逻辑,还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高压?它能否拥有独自遁入不朽的能力,哪怕此刻它已虚弱如回声,但镂在空谷里的回声,千百年后却仍依稀可辨。
除了这些古老的疑问外,亚马逊之类的互联网巨头进军出版业,也造成了新的冲击。正因此,《贾勒茨维尔》的出版故事,仍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故事,其中有危机,也似有隐秘的航道,通向另一片杳无人迹的大陆。
“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学赞助体系”
若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文学,它似乎不过是一个晚近形成的概念。在英国,英语语言文学为一门学科,直到1828年才开始设立,不过彼时的英语语言文学,更接近现代的语言学研究。真正的英语语言文学课程,始于1831年的伦敦国王学院,这所学院即是后来伦敦大学的前身。
在英国学者彼得·巴里看来,1820年代之前,英国高等教育仍由英国教会把持,与中世纪相差无几。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文学得以作为一门世俗的学问诞生?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将18世纪小说中的时间观,视为塑造民族想象的重要技术手段。安德森认为,文学中存在的“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的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恰恰是民族这一理念的准确类比,因为民族也是被设想成一个在历史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
1840年,当F·D·莫里斯获任国王学院教授时,在其就职演说中,他认为,透过学习英语文学,“我们可以令自己获得解放……超越那些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看法和习俗”。同时,在进化论的时代,英语文学可以作为宗教的代偿,在人们心中塑造出民族的想象共同体。
不过,以上历史事实,已经成为本世代英语文学现场的一个远景。尽管文学与民族主义的暧昧关系并没有失去自身的学术价值,但塑造当今英语文学的,并非日渐学院化的文学批评,而是MFA创意写作课程。
1936年,美国作家威尔伯·施拉姆在爱荷华大学开设了第一个作家工作坊。克莱顿写道,爱荷华的“这种模式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被复制,到2000年才开始推广。事实上,2000年以来的创意写作MFA课程比整个20世纪加起来都要多”。
当然,这一现象背后依托的不是文化产业自身的活力,而是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EA)慷慨且有针对性的资助。在MFA项目的一些受益者看来,MFA项目为许多位于文学食物链中层的诗人、小说家,提供了一份稳定收入,使其写作不必被其个人经济上的波动困扰。
名作家在成名之前,于底层生活的蚌壳中结出文学的珍珠,历经几番退稿,终获出版,进而畅销全世界。这样近乎神话的故事,曾经发生在加西亚·马尔克斯、《教父》的作者马里奥·普佐身上。
然而,更多作家,即使是留名文学史的爱伦·坡、戈尔丁、哈特·克莱、华莱士·史蒂文斯,也不能单靠文学收入支撑自己的生活。他们要么终生过着在文学与生计间奔波的双重人生,要么在贫穷的压力下结束自己的文学生命。
科尼莉亚·尼克森的学院生涯,则可作为当代美国中层作家的一个典型。《贾勒茨维尔》出版之际,透过在米尔斯学院MFA项目中担任讲座教授,她每年在纸面上即可从米尔斯学院获得12.5万美元的薪水。这使得她不必为出版流程中的高昂花费而苦恼。
当然,也有作家质疑,MFA项目史无前例地将大量作家吸纳到学院体系之中,久而久之,下一代完全由MFA项目培养出来的美国作家,其作品是否会缺乏切入当代生活现场的能力,只剩下一种过分甜腻的熟巧?在MFA项目将作家体制化的同时,作家是否会丧失反思文学本身的能力?
一代代学生被吸引到MFA项目之中,如同卡夫卡小说里的主人公来到法的门前,他们为门后的光亮而来,却恐惧那个无所不能的看门人。克莱顿在《封面之下》里不无苦涩地表示,虽然MFA项目“已经增加并稳定了目前的小说家的收入,但与此同时,这也使许多下一代的小说家背负了更多的学生贷款”。
图书编辑的诞生
1855年,沃尔特·惠特曼出版首版《草叶集》时,美国图书界还残存着早期出版行业中手工业的痕迹。19世纪中叶,这些产业是围绕着印刷室里的铅字盒展开的。在这个世界里,并没有专职图书编辑的位置。
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兼营杂志与图书业务的出版商们遇到了一些难题。当时,这些出版商的常规做法,是先在他们旗下的杂志上连载小说,而后推出单行本。
20世纪初,美国主流社会仍受清教影响,十分保守。他们推出的杂志,却是供家庭阅读的合家欢读物。因此,如何保证连载小说的道德标准,成为出版商们必须关注的问题。
正是在此背景下,现代意义上的图书编辑被细分了出来。斯克里布纳之子出版公司,在20世纪伊始,即开始招募“既可以检查作品的正派程度,又可以和作者一起工作以使他们的书稿离开道德灰色区域的全职员工”,这便是编辑这一职业最初的职责。
但到了1930年代,编辑一职就越出了这一枯躁的轨道,开辟出属于他们的神话。麦克斯维尔·珀金斯,就是编辑神话的原型人物。1910年,珀金斯入职斯克里布纳的广告部门,正式开启其编辑生涯。9年后,一本名为《浪漫的利己主义者》的小说,在珀金斯的积极游说下出版了。出版时,珀金斯与小说作者一起,为这部小说拟了一个新名字《人间天堂》。
小说作者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1920年《人间天堂》出版时还籍籍无名。但《人间天堂》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首版3000本于3日内售罄,尔后又加印11次。5年后,在珀金斯的帮助下,他还出版了《了不起的盖茨比》。
在其编辑生涯中,珀金斯发掘出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在内的诸多一流作家,为他们编辑出《太阳照常升起》《天使望故乡》《时间与河流》等一系列有分量的小说。
编辑不再只是类似道德守门人般的存在,他们是作家的知音与朋友,从作家们词语的钻石矿脉中抛光出一部部杰作。在与沃尔夫合作时,珀金斯时常被认为是他所经手的那些小说的真正作者。正是在珀金斯的影响下,沃尔夫才将装在三个手提箱中的千余页手稿,切削成了长篇小说《时间与河流》。
有鉴于此,麦克斯维尔·珀金斯成为了编辑理想的化身。他的书信集,被一代代编辑视作圣经。珀金斯生前在康乃迪克州新卡纳的住处,也已被收录进美国国家历史名胜。
文学代理人制度
编辑的故事只是《封面之下》所呈现的出版业生态的一小部分,当然,也是中国读者相对熟悉的部分。除编辑外,克莱顿·柴尔德斯还介绍了一个对中国读者而言颇为陌生的职业:文学代理人。我们可以透过类比,曲折地接近文学代理人这一职业。
那些紧盯低端市场的代理人,透过从怀揣着作家梦却不熟悉行业规则的新手那里榨取高昂服务费谋生。克莱顿毫不留情地称他们为“掠食者”。这一部分人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我国的发表中介。
正规的文学代理人,则类似于作家的经纪人。起初,文学代理人的职责,只是帮助处于文学生态顶端的作者处理他们无暇顾及的合同事宜。二战前,美国仅有约10%到12%的作家拥有代理人。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随着连锁书店在美国兴起,美国的图书市场总量开始增长。而很多成名的作者,需要应对多媒体、多市场的“全球版权”,但缺乏处理这些复杂合同所需的相关知识。在此期间,原先分散的出版社开始整合为若干出版巨头。这就使得传统图书编辑在工作量激增的同时,就业门槛也较过去更高。
许多编辑开始转职为文学代理人。他们甚至认为,代理人的工作,比之在出版巨头内谋生,更接近珀金斯式的编辑理想。代理人取代了传统编辑的一部分职能,专职为出版社发掘作者。而编辑,则只需要如同高台跳水般扎入他信任的代理人为他提供的文稿中。
如今,文学代理人已经是美国文学产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克莱顿写道:“到2008年,在主要出版商那里,近99.5%的作家都有代理人。”代理人制度似乎表征了美国文学生产的一些隐秘的特征。美国的文学生产,仍是基于同行评议的内部生产。文学刊物的存在对于代理人制度而言至关重要,因为代理人正是透过阅读刊物为出版社寻找新人的。
而文学刊物,则愈发信任MFA项目的筛选机制,希冀MFA项目的教授们在学院内一批批地制造出合资格的作者。与此同时,不同于旧有的英语文学课程,MFA项目即便不能像生产水果罐头一样生产出作者,也能哺育出不间断关注当代作品的优质读者。
在这个文学场域中,仍有人怀念故去的黄金时代,似乎那时,商业的强硬逻辑并没有渗入文学之中。然而,讽刺的是,最有可能摧毁传统出版业秩序的,却是亚马逊的自出版。它减省一切中间程序,给予底层作者充分的发表权,但也不会为这发表权提供任何附加服务,而是从中抽取高额佣金,做着近乎无本万利的生意。
似乎,这便是未来的文学空间,一个空白的、专业化的空间,仿佛一只失踪已久又被寻回的丰饶角,其中布满回声般的词语。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