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斯奈德:居住荒野,居于世界
波兰著名诗人米沃什有一句话:“最好的成绩,都是由那些直接与生命建立联系,而不是以书写文字建立联系的人取得的。”这句话十分耐人寻味,出自一个诗人之口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因为诗人本就是依靠书写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族类,诗人依靠诗歌为世界塑形。
但是,细心观察与区分不同的诗人,就会发现,不同的诗人虽然都是用诗歌作为手段,但实际上在完成着彼此完全不同的目的和使命。有些诗人一直在向着人的存在的本质发问,他们所有的诗歌都在探索自身与死亡、生命和信仰的联系,即人之为人的意义。
另外一些诗人,他们与世界的联系,是依赖于与世界之间的亲密互动与接触来完成的,在他们看来,文学或者说诗歌是需要在另外的一种生活中完成的,而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书斋,是需要“躬身穿行”。
书斋诗人依靠书籍,以及对世界形而上的观察和思考而形成诗歌;后者则类似于荷马那种吟游诗人,他们的诗歌在他们与世界强烈接触的摩擦中“迸发”。加里·斯奈德就是米沃什所说的“直接与生命建立联系而非以文字与世界建立联系”的诗人。
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是世界上目前还健在的高龄诗人,他1930年生于美国,曾经获得过普利策诗歌奖、美国国家图书奖,被称为“深层生态桂冠诗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斯奈德通常意义上被归入“垮掉派”诗人之列,虽然,他曾经极力否认过这一归类。但是无论他承不承认自己是“垮掉派”的一员,都无法否认他与包括艾伦·金斯堡、杰克·凯鲁亚克、威廉·巴勒斯和格雷格理·柯尔索等在内的,被称为旧金山文艺复兴的团体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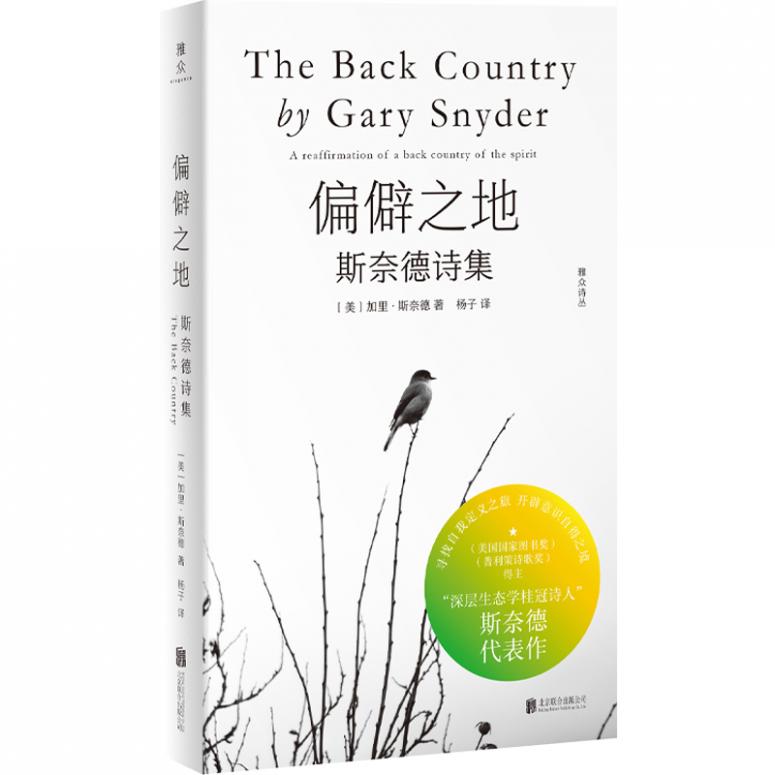
《偏僻之地——斯奈德诗集》【美】 加里·斯奈德 著
杨子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3年10月
的密切关系。
“垮掉派”是二战后美国重要的诗歌流派。该流派对许多文化分支都有重要影响,除了诗歌以外,摇滚乐嬉皮士运动等亚文化显现都与这一流派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反对主流文化,主张走上街头,他们喜欢爵士乐,但追求精神上的纯净与修行的同时,也存在着吸毒、性开放等问题,对美国亚文化产生了十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一种自由选择的生存方式
“垮掉派”的成员大多重视亲身体验,注重自然,同时喜欢东方文化,他们对美国主流文化不满,转而向古老的东方寻求精神启迪。
斯奈德向往的是一种自然的荒野生活。他当过护林员,也当过伐木工人,有着丰富的野外生活经验,他很长时间在荒野中跋涉、生活,参加很多体力劳动:从事过农业、畜牧业,参与过伐木、修桥、铺路。
与现在的一些野外探险者不同的是,斯奈德的荒野生存有着深厚的文化支撑,他深深喜爱禅宗和佛教,对于自然有着独特的感受方式。他的自然选择不是一时兴起,更多的是一种与信仰和精神相关的生存方式的重构,是一种朝向存在的自然守望。
二战结束后,对于文明和人生境况的反思促使很多诗人深刻反思主流文化。“垮掉派”与城市文明、精英文化所标榜的主流文明相对抗,主张选择一种更加自由的生活方式,他们反对消费文化,反战,对于现代文明充满了反诘。
与书斋中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金斯堡和斯奈德都提倡一种诗歌的非知识分子化,意思就是诗歌不是诞生于书斋之中依靠文字去制造的东西,而是需要肉体和灵魂真正地到真实的生活和活生生的人当中去所产生的精神产品。
斯奈德被归入到“垮掉派”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他与“垮掉派”的诗人来往密切,尤其是与金斯堡。1955年,在金斯堡那首著名的《嚎叫》呐喊出来的标志性的旧金山“六画廊”朗诵会上,斯奈德朗诵了他那首描写郊狼的《浆果宴》。
但斯奈德从不认为自己是“垮掉派”,他的诗歌风格虽然跟“垮掉派”的风格不同,但仍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反学院的诗风,在诗歌中吸纳东方哲学,强调一种“在路上”的体验诗学。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斯奈德更像是一个独立的哲人与隐士,他从美国西部一路跋涉到日本、印度,在荒野中,斯奈德完成着他与世界之间的亲密互动,书写了众多风格独特的精彩诗篇。
需要指出的是,斯奈德虽然生活方式非常乡野,实际上他所受的教育并不是粗鄙的。他曾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文系读研究生,还曾经师从我国著名昆虫学家陈世骧先生,他对中国古代诗歌感兴趣,翻译过白居易和寒山的作品。
“斯奈德的视野之开阔,他那双行脚僧般的双脚所抵达的地点众多……是在书斋里遨游世界的诗人望尘莫及的。”(译者扬子语)在《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特别强调了加里·斯奈德与艾伦·金斯堡的不同,相对于金斯堡这个“怒气冲冲的城市弥赛亚”,斯奈德更像是一个“孤独的乡村冥想者”;他“节制、退守,容忍沉思……兼具埃兹拉·庞德与亨利·梭罗的风格。”
斯奈德诗中镀金的生灵
斯奈德诗歌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生灵与人的位置,有时候,生灵、动物的位置似乎是高于人类的,它们有着一种人难以理解的神秘感。比如在他著名的诗作《浆果宴》中,他以一种美国西部部落作为图腾崇拜的神秘的动物“郊狼”为主要对象,书写了一首风格诡异的小长诗。
在部落文化中,“郊狼”作为造物主和神秘命运的决定者而存在,而位于这首诗中的人类却以一种倦怠的姿态出现。诗人写道:“一些人聚在某处”“整天胡扯”,而这些疯狂的郊狼在人类“乘公交进城上班”时开始行动。在谈论郊狼的时候,他又加入了“吃浆果的熊”“拂晓的猫”“鳟鱼”“漂亮的公牛”等诗歌自然意象,在这样一幅灵异的自然图景中,郊狼宛若一种神秘的生灵,秘密潜行。
可以说,整首诗歌充满了神秘气息,仿佛是一个虚构的幻想奇景,在一座“死城”中,人似乎只是作为倦怠的消沉布景,而郊狼则“生机勃勃”,它们似乎才是世界的主角。在斯奈德笔下,生灵,特别是动物似乎有着一种伊甸园般的神秘,每一个东西都被“镀金”,拥有着“世界初民”的神性光芒。
斯奈德重视体力劳动,他曾经辩护说自己不是一位“自然诗人”,而是一位“劳动者诗人”。在一些诗里,斯奈德用口语化的笔调,如实地写出了蓝领工人般的单纯生活。
《春天》一诗中,提供了一个修路的场景。“将沥青填入公路的洞坑/我们往火车上装满/修路的材料……”在这样的劳动中,诗人用心呈现了一些这之外的事物:“开花的田野”“峭壁”“黑色小树林”……全诗没有一句抒情的句子,却写出了一种禅意,一种单纯的美好的生活图景。
斯奈德很多诗歌用词简单,多是短句,进行铺排错落之后竟然生出某种令人激动的感情,看似轻松随意,给人无雕饰的通脱透美感。这样的古拙与简洁,背后是一种独特的看世界的眼光在起着作用,并不全然是对于诗创造的简单的词句排列等修辞上的技巧。
比如像《八月雾气弥漫》这样的诗歌,虽然给人一挥而就的痛快感觉,但是其中蕴藏的意蕴却很绵长。这是一首给爱人莎丽的诗歌,“八月雾气弥漫,/九月干旱。……我们把全部的钟拨慢/天突然就下雨。……你/像某种细长/新鲜的年轻植物/在夜里变得光滑沁凉/伏在我身上……”其中,对于爱人的一个明喻十分传神,充满爱意。
斯奈德写了很多首给妻子、儿女的诗歌,他的著名诗集《山河无尽》记录的就是他的日裔美国妻子在患癌之后,生命最后的时光,诗歌当中充满了骨骼般的硬朗。
令人惊奇的是,斯奈德利用了中国古典诗歌将之美国化,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风格。这种风格很难模仿,也很难有人超越他。究其原因,是他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非绝对东方,也非绝对西方的生活审美,这种思维促成了他那些不事雕饰、风格独特的诗歌。
像斯奈德这样的诗人,一旦打通了思维界限,仿佛写什么都可以成诗,而那些模仿斯奈德的诗歌,学到了意境的营造,学不到一套完整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只能是偶发性的“创作抖动”,并不具备“真”与“持久”。这是一个有关于境界的问题。
所以,读斯奈德,将之作为一种精神淘洗来阅读即可,如果真想学到其中的诗歌内蕴,恐怕要有一整套的思维系统作为支撑才行。
在自然中觉醒
斯奈德一生的诗歌写作与生活实践,可以看做是一种探索多样文明的选择。他从小受到修习禅宗的父亲的影响,接触到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文明”,那种熏陶让斯奈德能够脱离当时西方社会的主流选择,走上一条完全与众不同的道路。诗歌作为他生活选择的一种“形式”呈现,为我们留下了灵魂证据。
现代文明以降,城市文明的扩张让我们常常把自然与城市文明对立起来,近些年以来“生活在别处”的热潮,让许多人远离城市去乡村生活,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人不能离开自然而生存,自然对于人来说就像是一个精神家园,一旦我们长久脱离了这个家园,我们人类就很可能出问题甚至生病。
可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斯奈德是最早的一批有着这种觉知的人之一,因此美国的很多人都将他看做“先知”性质。对此,斯奈德在一篇译者访谈里谈到:“我们应该了解自然,应该认识花鸟鱼虫、星星月亮。不认识自然的人就像孤魂野鬼,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当一个农夫。”
荒野与世界本就不应该成为对立的存在。当城市生活变成一个牢笼的时候,另外一个襁褓在那里等待迎接我们的归来,那就是以“荒野”为表征的自然。虽然斯奈德深谙禅宗,但是他始终坚持自己是一位诗人,“我用诗替代解释。艺术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我是诗人……”斯奈德说。
“我不在乎 就这么活着/青山 漫长的蓝色海滩/可有时 睡在野外/我又想起 我拥有你的时光。”也许斯奈德诗歌艺术的魅力就在于他处于荒野与人之间的这一罅隙,他没有完全弃绝人类社会,像鲁滨逊一样走向自然,也没有被人类世界的纷扰和复杂圈囿,变为一种人际关系的探索者。他居于荒野,也是居于世界,至于在自然中的觉醒是否能够实现,这似乎是另外一个问题。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