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与忏悔录:当西方转向中世纪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彼得·布朗,于1970年代写成的《古代晚期的世界》,提纲挈领地勾勒出公元150年至750年间地中海世界的文化转向。正是这部著作,最早在英语学界标示出“古代晚期”这一时间段,起始于几乎颠覆罗马帝国的“3世纪危机”,而在7世纪的阿拉伯“大征服”中画上句号。
这之前,所有叙述古代晚期的著作中,当数爱德华·吉本的巨著六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最知名。在此书中,吉本认为,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最终导致了它的灭亡。
尽管布朗同样十分关注古代晚期向基督教中世纪的转变,但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再把古代晚期视作一个注定要滑向崩解的世界。与此相对,启蒙主义的通俗史学,将古代晚期贬低为蒙昧、荒芜、堕落的黑暗时代,而造成此种黑暗的,则是基督教对古典文化的遮蔽。
由此,作为对这种先入之见的反驳,《古代晚期的世界》在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的张力间展开。布朗意欲证明,这两种文化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唯有在古典哲学的圣杯中,基督教的智性才真正被酿造出来。
我们可以在奥古斯丁一脉的教父哲学中,听到古典文明的回响。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回忆,是西塞罗的《荷尔顿西乌斯》,促使他“突然看到过去虚空的希望真是卑不足道,便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向往着不朽的智慧”。
我们在《古代晚期的世界》中窥见的,便是这样一幅图景:当皇帝、蛮族、士兵、地主与包税人在空舞台上跳起回旋舞,幕布后,修士、主教、圣人正守着如豆的火光。而这火光照在他们的肉身上,以致那些跳舞的人,无论贵贱,都被他们佝偻的投影笼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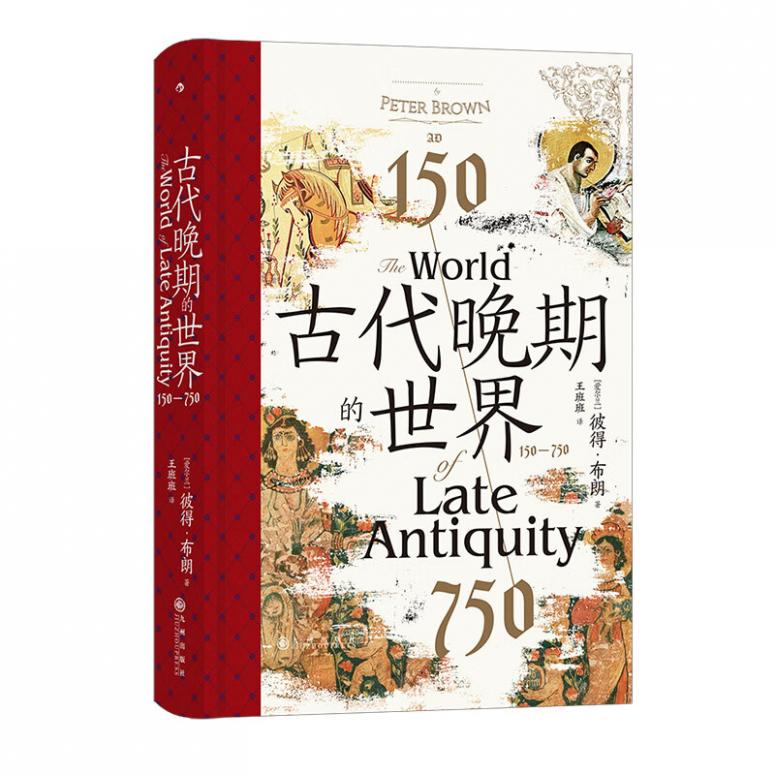
《古代晚期的世界》
【爱尔兰】彼得·布朗
(Peter Brown) 著
王班班 译
九州出版社
2023年10月
从城邦到世界
如何界定古典世界,这个世界又在何时抵达其边界?布朗认为,随着罗马帝国扩张至它行政控制力的极限,古典思想的基点,开始从城邦转向一种对“世界”的沉思。
当诸城邦被一种对普世帝国的想象黏合在一起,和平之神垂怜帝国,于此升平年代,文明在暴雨过后的水泊中照见自身的形象。
哈德良的前任图拉真,执迷于扩张领土。在他御驾亲征下,罗马征服达西亚,并进军两岸流域。图拉真在鞍马劳顿间死去,吉本评价道:“等到图拉真逝世,明亮的远景立即黯然失色。最值得担忧的情况,莫过于遥远地区的国度,一旦失去强有力的控制,就会挣脱强加在其身上的枷锁。”
与尚武的图拉真相比,哈德良更像一名沉稳的古典学者。即位初期,他便放弃了无法有效统治的领土,尽管如此行事必然招致非议,但哈德良仍希冀以平和稳健的方式统治帝国。
哈德良的继任者、“哲人王”马可·奥勒留,在与蛮族作战间歇,于黑森林边的营火旁,写下诸多碎语。这些碎语后被猬集于斯多葛派哲学经典《沉思录》,他在其中写道:“所有从神而来的东西都充满神意。那来自命运的东西并不脱离本性,并非与神命令的事物没有关系和关联。所有的事物都从此流出;此外有一种必然,那是为着整个宇宙的利益的,而你是它的一部分。”
奥勒留哲学中道德化的神,已经偏离多神教的仪轨,变得抽象、内在。但它仍是一个面向共同体的神,不像诺斯替主义(古希腊语:γνωστικός,又称灵知派)一样服膺于个人灵知。而诺斯替式的表述往往玄奥晦涩,混合着新柏拉图主义与拜火教的影响。
当我们重新发掘灵知派破碎的经卷,透过这些纸草上的残篇,便能辨认出作为其支柱的古典哲学。而多神教的遗存与基督教元素的并置,赋予他们一种独特的异端气质。
诺斯替主义者认为,存在两个造物主。至高的造物主不为人知,只有透过不断的训练灵知才能把握。《圣经》中显见的造物主,则被称为德谬哥(希腊语:δημιουργός),而祂只是一个工匠。
诸神从至高造物主中流溢,其神性随着祂们日益疏离至高造物主而变得微弱。人的堕落,也并非起始于人类始祖们的逾矩。堕落在个体中单独发生,若苏菲亚(Sophia,意为“智慧”)从人的脉管中流失,人也就失去了与神的联结。
也因此,诺斯替主义有趣的地方在于,当信徒们孜孜不倦于偶像崇拜时,他们便已开始转向一种超越性。而人与超越性的关系,映照出人自身的神性。
当我们由诺斯替主义这一支流,进入教父哲学及其后的经院哲学,便可发现,这些学说绝非如启蒙史学所指摘的蒙昧反智。理性在古代晚期并未被遗弃,相反,它几乎是被过度地使用。
圣徒与哲学家
当我们转向地中海东部,在那里,古典文明虽几经辗转,却从未断绝。拜占庭帝国仍沿袭希腊的世俗教育体系,它覆亡后,阿拉伯人早已替他们曾经的敌人保留下古典文明的火种。
对罗马帝国东部领土的关注,延续到彼得·布朗1988年的著作《古代晚期的权力与劝诫》。在这部书中,我们能瞥见和《古代晚期的世界》相似的介怀,尤其在宗教方面。宗教构成了古代晚期文化转型的重要背景。
《古代晚期的权力与劝诫》探究的,是权力如何与逐渐兴起的基督教话语互动,后者如何像微波渗入食物中一样渗透前者,动摇其形态。《古代晚期的世界》虽然不只关注宗教,但也为我们勾勒出几个关键的节点。
其中之一,是圣安东尼的出现。关于这位圣人的描述,成为中世纪圣徒金传的先声。在据称为亚历山大里亚牧首阿塔纳修斯所做的《安东尼传》中,安东尼被写成一个农民之子,“不谙希腊语,完全由上帝教导”。
为拜访安东尼,一位哲学家前往他苦修的沙漠。细沙如乱码织在哲学家的长髯中,哲学家发现安东尼手边没有书籍,好奇他平时是怎么阅读的,安东尼回答:“哲学家啊,我的书是上帝创造的自然;每当我想要阅读上帝的文字,它就在那里。”
386年,这些逸闻传到在米兰担任修辞学教师的奥古斯丁那里时,奥古斯丁下结论道:“没有学问的人突然飞上了天;而我们这些人尽管有学识,却仍然在血和肉里挣扎。”
早期护教神学的反智与民粹倾向,往往出现在一批具有高度古典教养的上层知识精英的笔端。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认为,对于天使与魔鬼,对于不可见世界的本质,任何一个受洗基督徒都比本时代最博学的哲学家了解得更多。
在教父们的设想中,基督教可以带来一种新的普世性,任何人,都能借由基督,获得与教养无关的神性智慧。但不无讽刺的是,这些护教者的社会地位,却是透过他们的古典修养获得的。
晚年成为希波主教的奥古斯丁,仍能收到地方士绅向他请教修辞学的信件。狂热的僧侣传作者、居洛斯主教忒奥雷多特,也与当时著名的智术师伊索卡希俄斯保持着公开的友谊。
尽管基督教强调圣徒的平凡出身,竭力想成为下层阶级的宗教,但与知识精英结盟仍是其扩张影响力的主要手段。在君士坦丁一世于312年正式皈依前,基督教并没有成为罗马任一行省的主流宗教。
驶向拜占庭
最后一位统治罗马全境的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于395年去世,帝国依照其遗嘱正式被分割成东西两部分。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中陨落,东罗马帝国则延续至1453年。为了把古代晚期及中世纪的东罗马帝国与其古典时代的原初形态区分开来,史学家又称这一时段的东罗马帝国为拜占庭帝国。
用短短一章概括拜占庭的千年历史,无疑困难重重。在《古代晚期的世界》中,布朗的叙述主要围绕查士丁尼(约482年—565年)与希拉克略(约575年— 641年)这两位重要的君主展开。
这两位皇帝都在其政治生涯的前半程取得了辉煌的军事成就。透过一次次远征,查士丁尼翦灭汪达尔人与东哥特人的王国,为帝国收回北非、意大利等地。希拉克略则将宿敌萨珊波斯一举击溃,巩固了帝国东部边疆。
但这些胜利都如海边的沙画般脆弱。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战争与瘟疫耗尽了帝国国力,皇帝沉迷于敲凿大理石的叮当回声,希冀在教堂与堡垒中镂刻他的皇权。赋税一再加重,最终引发了532年的尼卡暴动。
在皇宫被围,火焰焚毁一半的君士坦丁堡时,查士丁尼一度想放弃皇位。而他的皇后提奥多拉告诉他:“紫袍是最光荣的殓衣。”3日后,贝利萨留的军队从波斯前线赶到,君士坦丁堡因镇压而血流成河。
自此,查士丁尼的统治风格改变了。他开始强调君权神授,抹去皇帝作为世俗的“第一公民”的存在。执政官职位于541年遭废除,宫廷生活却像蓝藻一样扩张。提奥多拉出行时有4000名随从,是19世纪奥斯曼苏丹的两倍。
后世想象中,查士丁尼是一位不眠的皇帝,常常工作至天亮才稍作休息。他的形象,不复是那意图重建罗马的幻想家,而是一个睡眼惺忪的老人,总被无休止的麻烦纠缠。
他的统治依赖“受人憎恨且毫不团结的近臣小朝廷”及亲属,这是查士丁尼时代在帝国脉管里播散下的慢性毒药。古代晚期的政治权力变得愈发横暴,以致必须用一个新名词将其与过去区分开。希拉克略将拜占庭皇帝的头衔,从拉丁语的Augoustos(奥古斯都)改为希腊语βασιλεύς(巴西琉斯),他同时也使用“独裁者”(αὑτοκράτωρ)和“主人”(κύριος)作为其头衔。
跟随希拉克略,我们抵达古代晚期的尽头。阿拉伯人的突然崛起,打破了萨珊波斯与拜占庭间的均势。帝国无力战胜阿拉伯人,它精神的疆域也只能一再收缩,转向内在,转向信仰。
这历经6个世纪的文化转向在此刻成型,尽管帝国臣民们彼时仍浑然无知。从查士丁尼到希拉克略的几代人间,基督教会深深扎根入世俗生活里,主教彻底取代古代时代的行政官僚。拉丁语不单是文学与教养的语言,如今也是神的语言。
拜占庭民众不再能够想象一种普世的认同,他们愈发强调以信仰划定的身份,也愈发不安,愈发在这身份里流离失所。他们不再参与政治,而在阁楼里自我鞭挞。他们的帝国,将是一派黑暗中唯一满载信仰之光的救生艇,他们却只得在尘世,透过苦难中的坚忍,攀缘通向天国的阶梯。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