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在最后的天空之后思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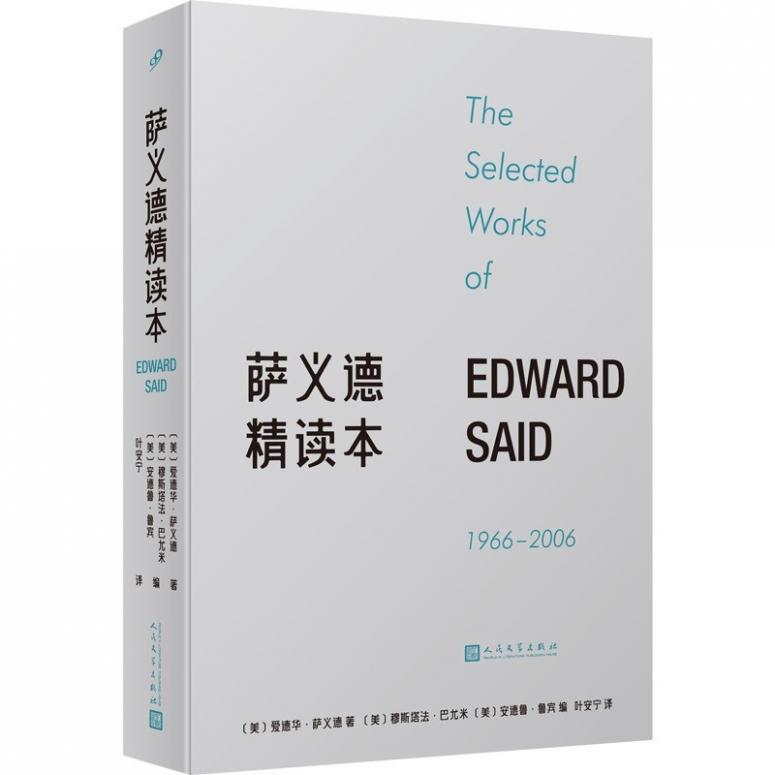
巴以冲突以血腥、惨烈的方式,在2023年10月再次进入公众视野。而谈及巴勒斯坦问题,美籍巴勒斯坦裔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是一个绕不开的角色。
作为巴勒斯坦人在西方最有影响力的代言者之一,萨义德用他一生的运思,独自创造出一片后殖民主义的话语森林。他故去多年之后,仍有人会从其中拾出只言片语。而他学院精英般的形象,已然成为一种政治符号。
萨义德直接述及巴勒斯坦的作品,如《巴勒斯坦问题》《报道伊斯兰》《最后的天空之后》等,不单在阿拉伯世界留下回声,在西方世界,他的写作亦打破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神话。萨义德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从不明确证实自己在进行一场犹太人的解放运动”,而是“一场犹太人在东方的殖民定居运动”。
在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之外,爱德华·萨义德在学术上的贡献,在于他以一种他称为“世俗批评”的方式,进入西方文学的场域,用1960年代的诸多法国理论,更新了传统的人文主义。
他被西方学界广泛视为20世纪最后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家。英国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著作《理论之后》中认为,2003年萨义德的逝世,如同但丁《神曲》中划分人间与地狱的界碑,他的死亡,标志着西方文学理论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衰退期。
由纽约市立大学英语系教授穆斯塔法·巴尤米与乔治敦大学英语系副教授安德鲁·鲁宾主编的《萨义德精读本(1966—2006)》,猬集了这位思想家一生运思的成果。个中文章,不仅体现出萨义德作为文论家的深厚学养,亦让我们看到那位如斗牛士般无畏的知识分子,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以他的人文主义,向那些“使人类历史变得丑陋的残暴行径和不义之举”,做着他所说的“唯一的,最后的抵抗”。
当萨义德反驳福柯
1966年10月,“批评的语言与人的科学”会议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行。彼时,萨义德刚刚完成他关于约瑟夫·康拉德的博士论文。J·希利斯·米勒等一众学人,看重他的学术潜力,便邀请他参加此次会议。
同样列席的,还有一众从法国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乔治·普莱。他们极具巅覆性的思想实践,被概括性地称为结构主义。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这次会议,正是结构主义进入美国学界的原点。
萨义德早期的思想,从结构主义受益颇多。美国作家蒂莫西·布伦南在《萨义德传》中写道,法国理论带来的崭新的感受力令人兴奋,“不仅因为欧洲哲学显得比美国淳朴的虔诚信念复杂、精深得多,更因为‘理论’不能被简化成学究的闲时消遣。相反,它对权力、传播和历史阐释等议题自信又反叛地发言”。
他的《东方学》,某种程度上是在米歇尔·福柯的阴影下写成的。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关系,在他们著述中都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不过,在福柯的作品中,有一个仿若真空的话语空间,福柯的写作极少涉及具体的政治诉求。但对萨义德而言,作为巴勒斯坦人,他始终要面对殖民主义这一庞大的政治现实。
殖民统治不单是历史的沉疴,它早已融化在前殖民地的日常之中。它塑造出作为“我们”的西方与作为“他们”的东方。而在东方学话语的包裹之下,殖民拥有了开拓的意味。文明的是“我们”,野蛮则归于“他们”。
由此,在早期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看来,对社会而言,去殖民无疑是一种阵痛。譬如弗兰兹·法农就在其著作《大地上受苦的人》中宣称:“不管是使用什么名称或引进什么新方案,去殖民(décolonisation)始终都是一种暴力的现象。”
在法农眼里,去殖民意味着一种人取代另一种人,而且是“没有过渡期的,完整且绝对的取代”。萨义德当然不会全然服膺于这种激进的二元叙事。《大地上受苦的人》是由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催生的,因此,法农也用战争的词汇及语法装潢它。
但“权力”这一福柯哲学的关键概念,对萨义德而言,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味。作为尼采的后继者,福柯始终将人文主义视为一种陈辞滥调。
在写于1982年的《旅行的理论》一文中,萨义德论及那些福柯的读者们,总希冀着超脱于左派与右派之上,其实不过是“用老于世故的唯智主义来合理解释政治上的不作为,同时又希望表现得有现实主义味道,与权力和现实世界不脱节”。
而萨义德始终无法接受结构主义的预设,即一种系统化的暴政左右了人们的一切行为,抵抗不过是此一系统的泄压阀。他近乎单纯地相信批评的力量,透过它,一个潜在的空间被打开了。从中,我们可以辨认出那些“为人类自由而产生的不受胁迫的知识”。
知识分子的责任
萨义德成熟时期的思想,更多地受惠于安东尼奥·葛兰西与西奥多·阿多诺。透过他们的著述,萨义德窥见了身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所在。1993年,他在BBC瑞思系列演讲中主讲《知识分子论》时,即以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作题解。
葛兰西在其《狱中札记》里写道:“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前者从事教师、行政官吏、教士等传统职业,后者则是由资本主义孵化出来的专业人士,如工作技术人员、行政顾问等。他们往往服务于各类企业与政府机构。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国作家朱利安·班达在其名作《知识分子的背叛》中的观点。不同于葛兰西将知识分子视为社会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班达所承认的知识分子,仅仅是那些沉睡在先贤祠与万神殿里的巨人,譬如伏尔泰、苏格拉底、斯宾诺莎与耶稣。
萨义德认为,班达所指称的精英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斥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
但无疑,葛兰西的论述更接近当代知识分子的现状。在专业细分愈发精密的当下,如萨特那般公开向社会发声的知识分子,正蜕变为学院内不问世事的专业人士。知识不再意味着敞开,而是变成一种隔绝。
作为对这种隔绝的反击,萨义德更多地以随笔而非专业论文的形式呈现他的思想。他的英语散文有着清澈明晰的风格,完全没有故作深奥的地方。他的确如苏格拉底口中的那只牛虻般从事着知识分子的事业,当城邦昏睡之际,他的词语便会刺向它笨重的躯体。
萨义德曾批评《奥斯陆协议》为“弱者的和平”。尽管整个世界都称道《奥斯陆协议》是巴以迈向和解的关键一步,但该协议并未提及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部分领土的占领,对于流亡在外的350万巴勒斯坦难民,《奥斯陆协议》亦保持缄默。
1995年10月,即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在白宫草坪上签订《奥斯陆协议》两年后,萨义德评论该协议的《中东“和平进程”》一文在《国家》杂志刊发。文章中颇为讽刺地写道,甚至“阿拉法特本人没有通行证就不能进入加沙”。
对于哈马斯,身为世俗知识分子的萨义德也早有预见,他说:“以色列在1980年代怂恿哈马斯的发展,将其作为破坏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大起义的工具,现在回过神把它提升到罪大恶极的等级。”
显然,巴勒斯坦当局也被萨义德刺痛了。文章发表次年的8月22日,在加沙及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市,巴勒斯坦的官员们冲进几家书店,清缴了店中所有萨义德的著作。
萨义德的晚期风格
《萨义德精读本》首次出版于2000年。那时,萨义德已步入人生的晚年。在他故去3年后,2006年,他未完成的遗著《论晚期风格:格格不入的音乐与文学》出版了。
正因此,新版精读本才得以收录《适时与晚期》等一系列围绕着“晚期风格”这一主题写作的文章。萨义德从阿多诺写于1937年的《晚年贝多芬》一文中,发现了这个主题。
在人们惯常的想象中,艺术家晚年的创作应该是平和、庄严,如同纪念碑一般的存在。在其中,你几乎感受不到生命的气息,只能任由那些刻意为之的质朴包围你。晚期风格要么是一种已完成的风格,要么就是从这种已完成中悲剧性地衰退。但阿多诺所体认的作为文化象征的贝多芬,是一位苍老、失聪、孤独的作曲家。
贝多芬晚期的音乐不再明亮与流畅,而是变得怪异、晦涩、疏离,可说是完全放弃了与听众间的交流。似乎,在晚年的贝多芬身上,阿多诺发现了自己作为流亡者的形象。对故土的记忆压迫着他的视神经,使他产生了一种双重视觉。本土居民眼里单纯的事物,亦要与记忆中的同类事物相对比,才能确定其成色。
流亡者的世界常常是缄默且拒绝沟通的,因为故土在他们心中常常被升华为乌托邦。它不再是那一片具体的地域,而是纯粹栖居于记忆中的一种构想。人生暮年的萨义德,之所以再次为阿多诺哲学所吸引,不仅因为他与阿多诺同样都以古典乐作为哲学思考的材料,亦因为他们也都穿越了20世纪的战火,流亡至美国。
这位以谈论开端闻名的思想家,如今步入了他人生的黄昏。《奥斯陆协议》之后,他便开始深入研究阿多诺哲学。同时,自1987年起,他亦为《国家》杂志不定期撰写音乐专栏。
但这并不意味着萨义德逃遁进了音乐的世界,不再积极介入政治。一如阿多诺,音乐始终是他思想的核心。萨义德死后,他组建的“西东合集乐团”存留至今。他希冀音乐能够作为一种塑造团结的力量,弥合巴以之间的矛盾。
这也是为何萨义德要在写于2000年的《定义的冲突》一文中,毫不留情地反驳塞缪尔·亨廷顿那著名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过度简化的框架,对萨义德而言,不啻于东方主义的回光返照。
自《东方学》以来,萨义德就一直反对将文化看作一个均质的整体,反对基于偏见并且不断生产偏见的本质主义。因此,他为巴勒斯坦问题开出的药方,颇为理想主义。在萨义德看来,只有拆除边墙,超越民族国家的话语构建,让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在这片土地上如兄弟一般生活在一起,巴以间的悲剧才能画上休止符。
或许到那时,《欢乐颂》就将在约旦河两岸间响起,夜空也会流淌在人们彼此注视的眼眸里。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