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爱具备宽恕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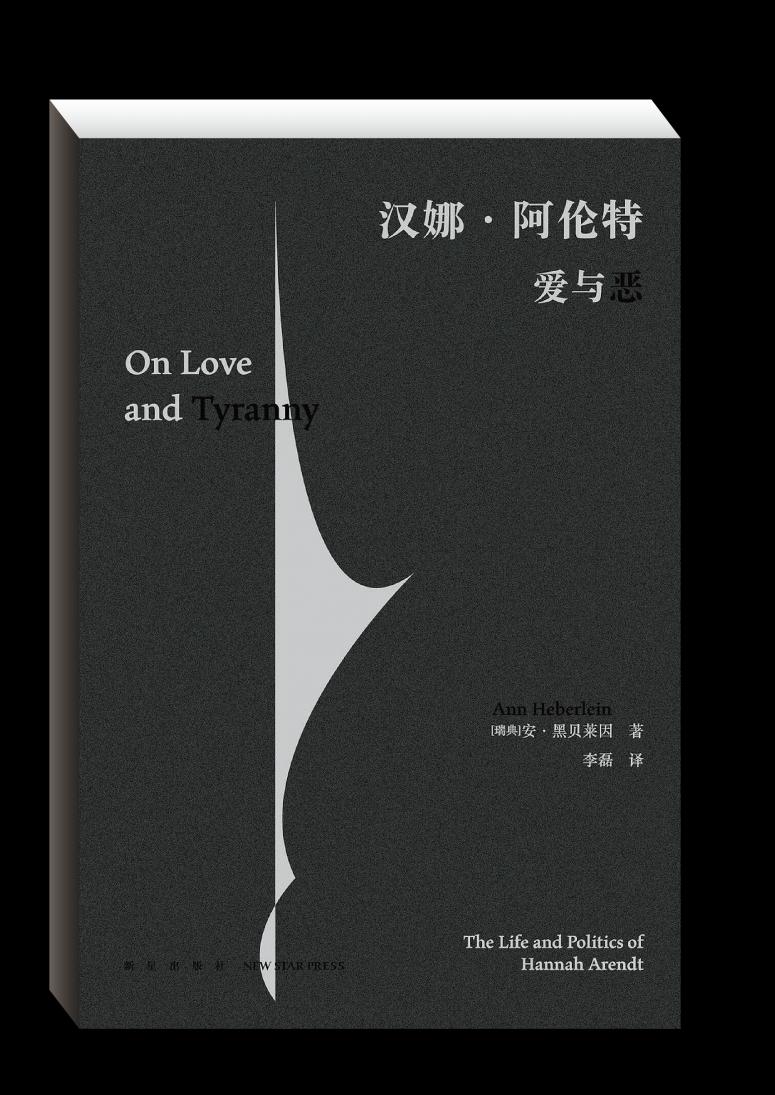
汉娜·阿伦特无疑是20世纪的一个传奇。关于她的生平,已有各种八卦在世间流传。但是我们如果用这样的猎奇心理来阅读安·黑贝莱因所写的《汉娜·阿伦特:爱与恶》,把阿伦特的传奇经历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不仅是低俗的,甚至是不道德的。面对阿伦特的传奇,看客的眼光甚至比平庸之恶更邪恶。
原因很简单:所谓的阿伦特的传奇经历,没有一次不是她的切身之痛成就的。这本书尽管提供了丰富的生平细节,但是它所要表达的绝不是阿伦特的人生经历多么丰富多彩。它是要追问一个沉重得多的问题:这个命运多舛的女性是如何放下这一切,坦然面对自己的苦难,用爱与世界和解的?
反抗恶的权利与勇气
面对这个世界上的恶势力对于自己的加害,阿伦特本来拥有讨回公道的道义权利。一个无辜的人,仅仅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从八岁(1914年)就开始逃亡,一次次流离失所,一次次面对死亡。她所承受的苦难,是这个恶势力强加给她的。因此,哪怕她心生怨恨,奋起反抗,甚至以暴制暴,对加害者进行复仇,也都有了正当的理由。
年轻时的阿伦特也的确是不屈服的。她奋力与恶势力抗争,为维护自己的生命与尊严,逃离了威胁生命的拘留营,逃离了随时可能拘捕她的德国,再从沦陷后的法国逃往西班牙、葡萄牙,最终逃往美国。这种逃亡本身就是不屈服于恶势力安排的抗争。相比于那些与她一起关押在拘留营而没有逃走,最后默默无闻死去的人,敢于以实际行动抗争的阿伦特已经表现出了她的勇气与责任。
阿伦特面对自己的苦难,是经过理性的思考而选择抵抗的。那个关于平庸之恶的著名论述,就是如此。阿伦特没有把艾希曼描绘成大众所期待的杀人魔王的形象,而是把艾希曼循规蹈矩的官僚形象如实地呈现给社会大众。由此引发的争议,几乎摧垮了阿伦特。社会大众难以接受艾希曼这么“普通”的形象,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在为艾希曼开脱罪责。
然而,阿伦特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她发现了这种平庸的恶,杀人如麻的恶人不一定是青面獠牙的或心理变态的。相反,像艾希曼这么“普通”的人,也可以因其平庸而成为杀人的狂魔。因为他对于杀人已麻木,他对于杀人是冷漠的,没有同情心、怜悯心。更重要的是,他缺少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或者也没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自觉意识与兴趣。
阿伦特对加害者的追责,除了批判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外,还这样明目张胆地追究到了平庸的普通人身上。麻木冷漠、缺少独立思考能力这样的特点,不正是现代社会中大众的特点吗?
那些愤怒指责纳粹没有人性、残忍暴虐的社会大众,恐怕做梦也想不到,纳粹的极权统治也有自己的份。没有这些平庸的普通人的合作,纳粹的极权统治也是难以顺利实施的。当阿伦特说出这个残酷的真相后,那些被她激怒的大众对她进行声讨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不仅如此,阿伦特还把追责扩大到了对犹太人自己的责任的清算上。她亲身经历了、亲自调查了一个又一个犹太人被迫害的事件。她发现,迫害犹太人的不仅有纳粹,还有犹太人自己的同胞。
这些参与迫害自己同胞的犹太人,常常是一些犹太社区里的管理者。他们掌握了其他犹太人的信息,包括身份、住址、财产状况等等。正是犹太人中的这些掌握了同胞信息的人,把这些信息提交给了反犹主义者,为那些加害者提供了便利。这些参与迫害自己同胞的犹太人又该承担何种责任?总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就被当成受害者而得到人们的同情吧?
阿伦特的这种义无反顾的追问,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包括她的许多朋友都因为她的犀利言论而躲着她了。她很难过,但不后悔。这就是道义的勇气。
区分罪责的智慧
阿伦特对于大屠杀责任的反思,从纳粹的极权主义思想根源,追究到平庸之恶,再追究到犹太人自己的配合。这在部分犹太人看来,有敌我不分、为纳粹开脱之嫌。但是阿伦特没有在自己人的质疑声中停下思想的脚步,她所思考的问题似乎也随着问题的复杂性被不断揭示而逐步深化。既然这么多人都在这个巨大的罪行中扮演了角色,那么如何区分不同的罪责?
那些精心策划大屠杀的统治集团的主谋,与那些麻木参与的执行者,以及那些被迫出卖自己同胞以换取自身安全的犹太人,他们的罪责当然是不同的。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问题。区分这些不同的罪责,实际上是宽恕的前提。而对不同的罪责,阿伦特也选择了不同类型的宽恕。
她区分出了可以宽恕与不可宽恕的恶。那些可以宽恕的,是一些具体的个体事件中的过错,而那些不可宽恕的则是抹杀人性的罪恶。从这个意义上说,出卖自己同胞的犹太人是可以宽恕的,而纳粹统治集团的罪恶则是不可宽恕的,包括制定大屠杀计划的决策者,也包括尽忠职守的艾希曼之流。这与法律上如何量刑无关,而是关乎道德上给予这些人什么样的谴责,是否在道义上饶恕这些人所犯下的罪恶。
宽恕作为一种伦理行为,也是复杂的。面对那些加害者,一味劝说受害者宽恕,确实是有偏袒加害者,容忍其继续作恶的嫌疑。没有了受害者的怨恨甚至报复来制衡,那些恶人岂不更加无法无天?他们在作恶之后反正可以得到受害者的宽恕,那么这些恶人岂不更加有恃无恐?
面对宽恕中所隐含的这种伦理困境,阿伦特是通过理性的思考来解决的。她对那些不可宽恕之恶是绝不宽恕的。哪些恶是不可宽恕的?就是那些没有人性的恶。在这样的恶中,作恶的人首先把自己的人性抹掉了,他们不把自己当人了,所做出来的恶事也是灭绝人性的,这样的恶已无须宽恕。因为,无论如何宽恕,那些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的人也不可能再成为人了。纳粹组织的大屠杀就是这样的恶。他们在把犹太人抽象化为可以消灭的“物”之时,自己早已失去了人性,变成了杀人机器。
但是对于谎言、不足、违约这样的恶,阿伦特选择了宽恕。这些恶只能说是人性的弱点,虽然也会带来伤害,却还是可以被宽恕的。宽恕的前提,应该是作恶者真心悔过、痛改前非。受害者在此前提下选择给加害者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才是有意义的。倘若没有这个前提作为限制,我还是怀疑宽恕又变成了滥做好人,那又与纵恶无异了。
爱这个世界的意义
对于阿伦特而言,宽恕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盘算。她对于加害者的宽恕,还是因为“爱”。她是爱这个世界的,尽管她曾发出“爱这个世界为何这么难”的感慨,但是这并不妨碍她爱这个世界。对于一个爱这个世界的人而言,让伤痛阻止她对世界的爱,无异于让伤痛直接终结了她的生命。
她要继续活着,就必须走出伤痛,放弃仇恨,重新爱这个世界,这样,她的生命才能得以延续。让她不爱这个世界,就等于终结了她的生命,她只有重新爱这个世界,才能继续活着。因此,宽恕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宽恕之后,她就可以继续爱这个世界了。所以,在宽恕的背后,是爱赋予了宽恕力量。
那么,什么是爱这个世界?“爱世界是一种态度,一种专注于宽恕、接受与和解的行进方向。为了生活在一个有可能发生大屠杀的世界里,我们必须理解和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就像必须理解今日正在发生的事一样。”书中这样的爱似乎又有点不分敌我、没有原则了。
但是这种爱的态度也许正是一种正能量,它是化解世间爱恨情仇的唯一的良方。冤冤相报,不如相逢一笑,这或许正是世界变得美好的唯一途径。当然,这种爱的态度不是要我们生活在甜美的幻想中。
爱这个世界,不仅仅是爱它美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包容它的缺点,给世界变好的机会。“我们绝不能遗忘,也绝不能沉迷于怀旧情绪。我们必须够爱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爱它所有的瑕疵,我们必须和自己的记忆共处,牢记我们必须感激的人和事。”坦然面对这个并不美好的世界,但仍然无悔地爱它,或许这就是阿伦特的切身之痛与世界之爱给我们的最大启迪。
1952年5月24日,阿伦特在弗莱堡给丈夫布吕歇尔的信中谈论了与海德格尔的交往。丈夫早已知道妻子年轻时的那段浪漫师生恋,但他此时毫不介意两人恢复交往,而海德格尔的妻子则表现得十分抵触。这位本来就积极反犹的纳粹女性,对于阿伦特这位犹太情敌在多年之后幽灵般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自然十分恼怒。
阿伦特也豁出去了,公开对自己的丈夫说:“我已不必在他面前装模作样,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她已经坦然面对过往的尴尬之事,而今重新来过,与海德格尔之间只有同事之间的友谊,没有任何私情,所以也不怕海夫人的冷眼了。更妙的是,阿伦特的丈夫十分慷慨,鼓励妻子与其老情人交往。
一位大度的丈夫,一位坦诚的妻子;一位年老的情人,一位嫉妒的老妇。这四个人构成的正是一幅奇妙的宽恕、和解、充满爱又不无瑕疵的世界图景。阿伦特宽恕了海德格尔在政治上的欺骗与感情上的背叛,布吕歇尔宽恕了妻子与情人的“藕断丝连”。海德格尔在情人阿伦特面前表现出了愧疚,海夫人虽然对阿伦特这个犹太情敌一时还难以释怀,但在海德格尔垂暮之年,这对情敌还是和解了。
这一幕像极了电影中各色人物历经磨难,终于大团圆的温馨结局,也为什么是爱这个世界做出了完美的诠释。
阿伦特所承受的苦难,赋予她爱这个世界的勇气,也给了她爱的能力。她阻止不了嫉妒、谎言与抑郁,但是正因为她爱这个世界,那些犯过错的人才得以改过自新,这个世界因此而多了一份美好,多了一份希望。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