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秩序”:彷徨中的奥斯曼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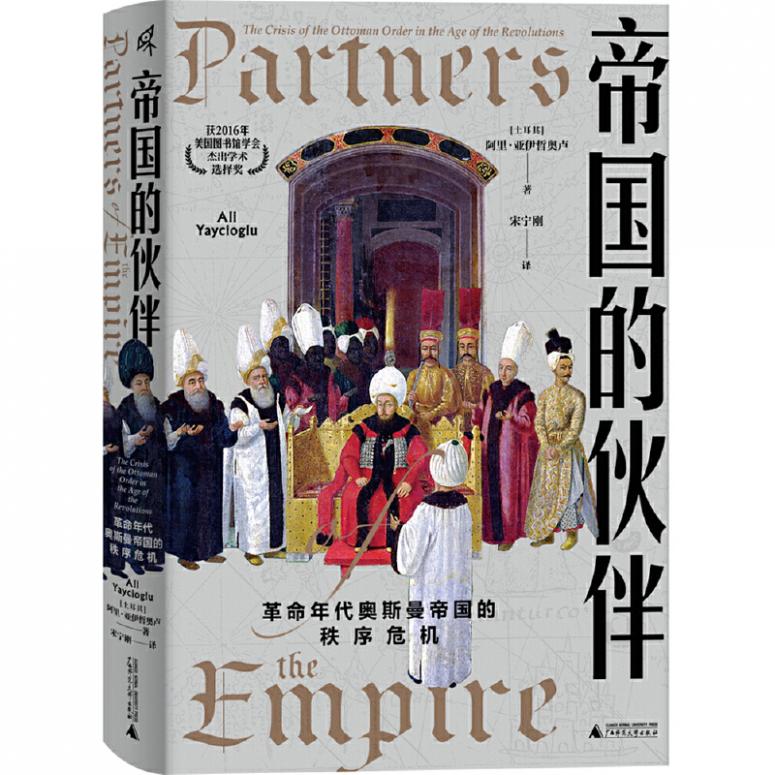
埃及已是夜半,这土地上,紧贴着尼罗河铺展开的绿洲如蚯蚓般纤长,这便是人类最古早文明的所在。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自此,埃及人再也没有建立他们自己的王朝。
两千多年后,1798年,埃及乃至整个近东的文明仍在沉睡。奥斯曼帝国鲸吞下这一整片区域。诚如德拉克洛瓦画笔下挤满妃嫔、阉人的土耳其后宫,在东方学家的想象中,正是奥斯曼的专制、迟钝、暴虐,让近东陷入停滞。
尼罗河如一柄大马士革弯刀刺向海湾,水藻让这奔涌了千年的河面锈迹斑驳。另一队征服者趁着夜色登陆,这便是拿破仑的舰队驶入了亚历山大港。这一时刻,常被视为中东近代史的开端。
但正如耶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提摩希·施奈德所说:“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点就像一层浮冰,覆盖黑暗的未知大海。”在施奈德看来,存在两种历史叙事:一种像雨水落在浮冰上,加增其厚度;另一种,则像破冰船,“靠着自己的动力航行,找出漏洞所在”。
我们总是把近东抑或远东的历史切削,装入欧洲中心主义的“冲击与回应”模型中,并将其因式分解,变成一组组二元对立。土耳其历史学家阿里·亚伊哲奥卢的《帝国的伙伴》,凭借对土耳其语原始史料的梳理,拆解了我们对奥斯曼近代史的诸多二元论想象。
古老帝国的艰难转身
《帝国的伙伴》着重讨论1806至1808年的事件。这三年间,奥斯曼帝国发生了两次革命、一次政变。其间,两位苏丹被废黜,首都伊斯坦布尔遭炮击,上万人葬身火海,支持“新秩序”的改革派几乎被屠戮殆尽。
为何在短时间内,帝国会遭逢如此激烈的变故?要明晰个中原委,亚伊哲奥卢就必须为这些事件找到一个坐标系,既把它们放在19世纪初国际大环境里考察,也应在一个长时段中把握其在自身历史发展里的位置。
历史径直是那荒野本身。故历史学有时应该采用地理学的方法,勘测这由诸多事件构成的地层。考究某一事件在历史地层中的位置,就是要厘清构成它的元素,辨认出使它沉积于此的地质运动。
《帝国的伙伴》的考察,从1700年开始。亚伊哲奥卢在此分析的,是奥斯曼帝国在整个17、18世纪的秩序构建。
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帝国秩序的构建往往依赖一种对“世界帝国”的想象。前者就像一片湖泊,有明确疆界,民族国家将星散的个人融化在自己身体里。帝国则像大河,起始于一滴融雪,却注定要不断地冲蚀出属于它的河道。
“奥斯曼国家被设想成这样一项事业。”亚伊哲奥卢论述道,“它征服土地,带来正义,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和平秩序。”
此种观点,几乎可以在任何处于扩张期的帝国找到回声。不过,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帝国统治带来的正义,首先是基于伊斯兰教的正义。
故而奥斯曼苏丹的身体不仅仅是国家及其世俗法律的肉身化显现,它同时也是“神在人间投下的影子”。又因为帝国疆土横跨不同文化区域,苏丹的至高权力也就拥有了繁杂的来源。在波斯人那里,他是帕迪沙;在草原民族中,他是可汗;而在穆斯林面前,他是哈里发。
在19世纪前,并没有一种正式的世俗法律可以约束苏丹。帝国官员不会因血统而得到荫庇,他们仅仅作为苏丹的仆人而获得权柄。这意味着,即使一个奴隶,也可以在帝国的官僚体系中攀上高位。但理论上,苏丹能够绕开法律程序,直接没收任何一位仆人的家产,乃至将其处决。
权力结构的高度不稳定,是奥斯曼政治的特点之一。但进入18世纪,随着帝国在欧洲战事中频频失利,各行省的地方显要开始坐大。他们透过不断的政治谈判,事实上成为了盘踞在各地的世袭贵族。
西方军事技术的进步,使得奥斯曼骑兵难以在战场上占据主动。1763年,苏丹穆斯塔法三世(1757至1774年在位)的特使艾哈迈德·雷斯米,出使了腓特烈大王治下的柏林。在传回伊斯坦布尔的报告中,他这样描述普鲁士军队的操典:“士兵每300人为一批,进行持枪、填弹、卸弹的训练,练习并排整齐行进,无论畏惧与否,绝不破坏队列。无论日夜,长官对士兵丝毫不放松。士兵枪不离手,弹带在腰,一切都保持最佳状态。他们所受待遇之悲惨甚于奴隶,仅得面包一块,使其不死而已。”
帝国的精英阶层,深感奥斯曼军队的朽败、低效。从军事改革开始,1806年,在苏丹塞利姆三世治下,一场名为“新秩序”(Nizam-ı Cedid)的改革,重构了奥斯曼的统治秩序。
近卫军对抗“新秩序”
即位前夕,苏丹塞利姆三世写下了一首四行诗,其尾句在后世看来不免悲怆。这位精通音乐、诗歌与教理的苏丹写道:“崩溃然后重建,世人称之为命运(devrān)。”
在土耳其语中,“devrān”一词指涉星辰的周期运动、时间的交替循环,有时也被引申为“革命”。显然,塞利姆三世敏锐地预感到,一场重塑世界政治地貌的地震即将袭来,他于1789年4月7日即位。这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
亚伊哲奥卢提醒我们,应该把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还原成世界史的一部分,而非孤立的区域史。事实上,奥斯曼与欧洲的联系远比我们想象中紧密。
一个近乎黑色幽默的细节可以证明此种联系:践祚前三年,幽居托普卡帕宫的塞利姆王子,曾写信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向他请教如何重组帝国的财政与军事。
塞利姆三世首先着手处理的,是军事问题。帝国的军队被称为近卫军,又译为耶尼切里(yeniçeri)。这支军队起初采用血贡制度组建,是直接听命于皇室的奴隶军队。帝国定期从巴尔干地区信奉基督教的农民中征调一些少年,让他们改宗伊斯兰教,作为士兵受训。
但随着欧洲战事的绵延,帝国急需扩大兵源,火器的发展使得奥斯曼军队愈发依赖诸如耶尼切里的精锐步兵。血贡制度因此解体,来自社会底层的穆斯林青年、从农村迁居城市的移民纷纷涌入近卫军的营房。这些营房被称为“ocağın”,直译为“壁炉”,象征他们与苏丹一道分享的正餐。
近卫军就像渗入两块木板间的胶水,将帝国上下的不同阶级黏合在一起。他们深深卷入城乡的经济活动之中,在高层中亦拥有绵密的关系网络,以致反对他们的人往往也出身于“炉边”。18世纪末,上述这一切使得近卫兵的兵变不再只是单纯谋取权力的政治行为,而是能够将整座城市动员起来的“革命”。
1808年,在观察过由“新秩序”引发的三年动荡后,奥地利外交官弗朗茨·冯·奥滕费尔斯男爵在一张便笺中写道:“近卫军深嵌于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宗教宪制,消灭近卫军便是在摧毁奥斯曼苏丹国。”
如何理解帝国的“新秩序”?显然,它并非只是用一支欧式新军取代古老近卫军的单纯军事改革。与新军同时引入的,还有现代化的规训技术。
围绕着新军的一簇簇话语,是“秩序”、“训练”与“服从”,而非“英勇”与“荣耀”。围绕这支新军的诸多改革,带来了知识与工具理性,新军高度的服从性让它不再像耶尼切里一样融化入帝国的整个社会结构。
而要供养这样一支军队,帝国必须同时调整其陈旧的税收制度。这意味着帝国需要以各种方式加强对领土与人口的控制,包括和外省显要合作,承认其地位,抑或相反,透过没收与政治处决喂饱“新国库”。
但最终,近卫军与“新秩序”的紧张关系中断了塞利姆三世的改革。1808年,当支持“新秩序”的地方显要向伊斯坦布尔进军时,这位于1807年近卫军兵变中逊位的苏丹被宫廷侍卫们勒死,弃尸于皇宫内院入口。
三种彼此交织的秩序
18世纪末,和很多现代早期国家一样,奥斯曼帝国陷入了财政危机。人口增长与通货膨胀,使得原先的土地法典失效,税收开始以汇总的形式征收。这进一步导致在地方层面,苏丹只能掌握极有限的税收。
俄土战争中的军事失利放大了帝国的危机,尤其是当1770年,俄国海军绕过整个欧洲大陆侵入爱琴海时,帝国辽阔的疆域反而不利于防守。
因此,在18世纪末,奥斯曼领土中同时存在三种彼此勾连、互相渗透的秩序。
其一是集权化的“新秩序”。其二是外省显要基于伙伴关系的秩序,他们希望透过《同盟誓言》将外省王朝与苏丹合作共治这个帝国的局面合法化。其三则是地方社群自下而上的自治。
在亚伊哲奥卢看来,奥斯曼的外省显要,是在极不稳定的权力地基上,向苏丹提供军事、财政服务的企业家。这些显要中最知名的,莫过于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透过一场成功的现代化改革,穆罕默德·阿里甚至一度拥有了足够与伊斯坦布尔直接对抗的实力。
地方社群的自治也并非有意的制度设计,而是在县级行政单元的治理实践中自然形成,然后再被国家权力承认。县的长官,称为阿扬,需要经由社群一致同意,才能就任。
自治局面的产生,有赖于17世纪末旧税制的崩溃。这使得奥斯曼帝国放弃向个人收税,转而将县视为税收的最小单位。
新的汇总征税法,让帝国官员们不得不依赖熟悉地方民情的社群领袖。在卡迪或者说法官的监督下,他们与社群就税收展开讨论,并最终达成一致,完成详细的分摊账目。
从这里,从卡迪法院内高声念诵的税收条目里,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被打开了。习惯、法律、传统交织在这窄小的厅堂,那些寒微的人与显贵一起作为政治与经济主体发出了声音。
《帝国的伙伴》是一本关于秩序的书,它呈现出这三重秩序如细密画般彼此交织的结构。我们或许可以用一个未必完全恰当的比喻理解它。“新秩序”是在帝国的头脑中产生,它意在管辖、指挥,尽管帝国巨大身躯中漫长的神经线路让它难以快速铺展开来。
显要的秩序:这巨人的四肢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神经中枢,它们开始独掌展开军事、经济、外交之权,同时希望终结苏丹不受限制的没收与处决。
最后,社群的秩序呈现出帝国最小的权力细胞。正是它们支撑了外省王朝的野心,也是它们最终存留了下来,告诉如今的我们,即使在被视为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奥斯曼,人依然能在时代的夹缝中保存自己。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