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创作生涯九十周年:重返黄金时代
1933年,一篇署名“悄吟”的长篇散文《弃儿》在长春《大同报》的文艺副刊上开始连载,散文讲述了怀有身孕的女子芹经历的一段悲惨时光。她被未婚夫遗弃、身无分文受困在洪水中的旅馆。被名叫蓓力的男子搭救后,芹在病痛与饥饿中生下婴儿,将婴儿送养后,又独自在医院度过三周。
所谓“弃儿”,具有明显的双关意味,既是被送走的婴儿,也指代女子芹在被遗弃中度过的孤苦日子。
这篇散文并未在当时的文坛引发过多关注,人们还不知道,一位天才作家即将诞生。
1933年10月,一部名为《跋涉》的小说合集出版,引起满洲里文坛的关注。因带有“反满抗日”的倾向,两个月后,这部合集被当时的日伪政府查封,该书作者流亡青岛,最后落脚上海。
1935年12月,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弃儿》和《跋涉》的作者在上海出版了新作《生死场》,署名萧红,这个日后被称为“文学洛神”,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由此蜚声文坛,终于被世人熟知。
如今,距离萧红开启文学生涯过去了九十年,她在文学上的影响力未曾退减,她的文章多次被选入课本,而她已成为与鲁迅、老舍等人一起被几代中小学生熟知的作家。她笔下的呼兰河凝聚了北方故土的童真与失落,是无数人回望中追寻的精神家园。
鲁迅曾评价她为“中国当代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她也确实如一颗流星划过那个战火飘零的年代的长夜。在短短八年的创作生涯里,她写下的东西不算多:《生死场》《商市街》《呼兰河传》《马伯乐》,但每一部都从厚厚的历史尘埃中脱颖而出,照亮了后来的无数追随者。
同时,这些自传性的文字,临摹出作家萧红塑身的一部分:在漂泊与疾苦中度过的短暂人生,曲折的情感生活,以及对命运的不甘。
在临终的前几天,萧红写下最后的遗言,“我将与长天碧水共处,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遗憾自己的创作生涯即将结束。几日后,也就是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香港病逝,年仅31岁。

1934年,萧红、萧军在离开哈尔滨前夕合影。
被遗弃与遗弃
萧红原名张廼莹,1911年6月1日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在当时,以萧红的家境,生活本应无忧无虑,但童年的萧红似乎并不快乐。她八岁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迎娶继母。在萧红笔下,父亲的形象总是负面的。收录在《商市街》里的一篇文章曾这样描述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在这样残缺的家庭里,唯一能给予萧红关怀的人就是祖父,在萧红眼中,祖父是一个让她“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温暖和爱”的人。也正是在祖父的支持下,萧红得以顺利地完成学业。从1920年到1930年,萧红在哈尔滨先后读完了小学和初中。
1929年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萧红的人生。首先是当年一月份,父亲将她许配给哈尔滨汪家的次子汪恩甲。其次是六月份祖父去世。庇护萧红度过少年时代的亲人离去,而她又被一段包办婚姻束缚。萧红无法接受,她对所谓的家庭再也没有留恋,不顾家人反对,决意逃婚,在1930年初中毕业后的夏天,出走至北平,入学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由此开始了她12年的漂泊人生。
在后来的一篇散文《初冬》里,萧红讲述了自己漂泊多年后,偶然在街上遇到了弟弟张秀珂。那是1935年上海的初冬,偶遇后的姐弟二人在店里喝咖啡,其间弟弟劝萧红回家,不要继续漂泊。萧红回答,“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
从1930年到1935年,萧红先是因逃婚被父亲切断经济来源,从族谱中抹去。她辗转北平和哈尔滨,最后被迫投靠未婚夫汪恩甲,两人住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1932年6月,汪恩甲不辞而别,留下怀有身孕的萧红和尚未结清的大笔吃住费用,被旅馆扣押的萧红面临被卖到妓院的风险,只好致信《国际协报》求助。
7月12日,当时以笔名“三郎”在《国际协报》文艺副刊发表文章的萧军受主编委托,前往旅馆探访萧红,两人结识后迅速相恋。一个月后,一场由松花江决堤引发的洪水席卷哈尔滨,萧红搭乘搜救船逃离旅馆。
这段往事正是开头提到的散文《弃儿》的真实背景。文章里,“一个肚子圆得馒头般的女人,独自地在窗口望着。她的眼睛就如块黑炭,不能发光,又暗淡,又无光,嘴张着,胳膊横在窗沿上,没有目的地望着”是萧红为过去的自己画下的画像。她与笔下的女子芹一道,再次体验被黑暗和绝望围困的那段时光,转而因一次意外寻得光的出口。
将与汪恩甲的孩子生下并送人后,萧红与萧军同居,加入了当时东北的左翼青年作家群体,走上创作之路。

《萧红》剧照——萧红与鲁迅走出内山书店场景。
半生漂泊
在三十年代,熟悉萧红和萧军的文艺群体习惯把他们称为“二萧”。虽是恋人关系,在生活和创作上彼此扶持,但萧红和萧军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萧军性情直率、热烈,有浓厚的革命热情,从事文学创作前曾参过军。萧红敏锐细腻,虽学生时代也参与过抗日运动,但对政治没有萧军那么热情高涨。
创作上,从两人落脚上海后各自出版的作品就可以看出分别。萧军于193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与日本侵略者浴血抗争的场景。在抗日战争已打响四年的当时,《八月的乡村》有鲜明的时代感。
同年,萧红出版的《生死场》更像是从时代巨幕的一角割开了一道裂口,她以哈尔滨近郊的农村为背景,讲述了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图景。它的时代背景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前后,但在小说里,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似乎并未对角色们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正如小说里所写,“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仅仅是活着这件事,就已经耗尽了角色们的力气。
而《生死场》的面世引发轰动的同时,也为萧红带来一些争议,争议无非是抗日大局当前,谁会去关心发生在农村地区的一些家常琐事?但萧红似乎并不以为然,她笔下这些带有个人成长印记,刻画底层人们尤其是底层女性命运的文字成为当时主流叙事之外一道极为独特的声音,同时养成了萧红日后的创作脉络和风格。
发表完这两部作品的次年,萧红和萧军参与了杂志《海燕》的创刊。或许因为这期间萧军与他人有情感纠葛,萧红在这一年决定前往日本。在散文《孤独的生活》里,萧红记录了她在日本独自吃饭、上街以及读书的琐碎日常,从一些语句里可以看出她寂寥的情绪,“假若,再有别的朋友或熟人,就是冒着雨,我也要去找他们,但实际是没有的。只好照着原路又走回来了”。
1937年,萧红接到萧军的来信,中断在日本的生活,乘船回国。至此,已经分别半年的两人并未因久别重逢而在情感上回温,反而多次恶化。与此同时,八月份淞沪会战打响,萧红被迫继续漂泊。她先与萧军从上海前往武汉,又应时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副校长李公朴的邀请,于1938年1月底,随萧军等一众文艺创作者前去任教。
前往山西是萧红人生中的又一转折点。在那里待了不到一个月,日军又逼近临汾,萧红和萧军此前在生活和创作中的分歧未能再次经受住考验,萧军决定留下来打游击,萧红先辗转山西运城,在3月份到达西安。
在收录于《商市街》的许多散文里,萧红记录了东北时期她与萧军经历的那段困顿生活。正如《生死场》里忙着生、忙着死的农人们,那时的萧红和萧军总是为生计发愁,如何解决饥饿常常是与创作同等重要的事。《黑列巴和白盐》一文中,萧红写没有收入的两人每日依靠借钱度日,买一些黑列巴和盐,“黑列巴和白盐在许多日子成了我们唯一的生命线”。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后“二萧”以分别告终。对萧红来说,与萧军相伴的困顿生活里,相濡以沫是真实的,因困顿带来的痛苦和漂泊也是真实的。她从19岁起就在不断经历这些,她最后的愿望只是可以有一个安稳的环境进行创作,但这并不在萧军的人生规划里。
离开山西后,萧红与萧军正式分手,结束了六年的恋情。随后,她明确了与作家端木蕻良的关系,在1938年4月随端木蕻良回到武汉,举办了婚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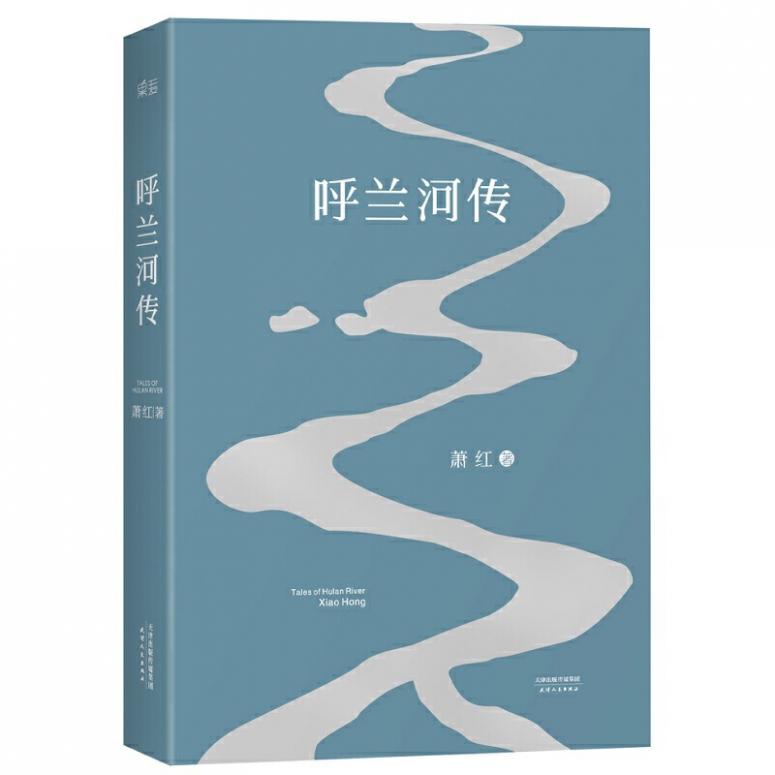
短暂的黄金时代
近十年,出现过一些以萧红为原型的影视作品,有2012年,霍建起导演的《萧红》;2014年,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以及香港纪录片导演魏时煜的纪录短片《跋涉者萧红》和围绕《黄金时代》拍摄的幕后纪录片《她认出了风暴:萧红和她的黄金时代》。
以霍建起的《萧红》为例,电影里,宋佳饰演的萧红总是拘泥于她与不同男性的情感纠葛里。创作者想要塑造的大概是一个渴望爱情但又为情所困的萧红,完全忽略了身为作家的萧红在创作上的经历,这种对萧红片面式的解读在许鞍华的《黄金时代》里也有所体现。
对萧红来说,与萧军的情感经历固然重要,但在离开萧军后,萧红还是写出了堪称她至高文学成就的《呼兰河传》,她在临终前感到遗憾的也不是个人生活,而是不能再继续创作。
创作才是萧红生命的主心骨,她也用事实证明,她的创作远比她的个人生活更深邃。只是在一些后来者眼中,讨论一位女作家的情感韵事远比直面她的作品来得简单有趣。清醒如萧红早就意识到这点,在生前写给友人的信中她提到,“当我死后,或许我的作品无人去看,但肯定的是,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
写完《呼兰河传》时,萧红已身在香港。与端木蕻良结婚后,二人先从武汉前往重庆,再于1940年来到香港。《呼兰河传》于当年9月在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连载,小说以萧红童年生活过的小城呼兰为背景,描写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地区的人情风貌,它可以看作是萧红将小说《生死场》和收录于《商市街》里的散文杂糅过后,创作出的一种模糊了小说与散文界限的新文体。语言朴素简洁,同时兼备诗意,更重要的是,萧红从未以这份携带在语言之上的诗意来将笔下的人物过度曲解,她维持了身为作家在创作与道德之间的平衡。
小说《呼兰河传》完结的第二年,萧红出版了长篇小说《马伯乐》的第一部,并很快开始了第二部的连载。与此同时,整个1941年,萧红因肺病频频住院,在1942年被医生误诊,做完喉部手术后病情急转直下,最后病逝。她所留下的“半部红楼”就是尚未写完的《马伯乐》。
小说《马伯乐》是萧红向恩师鲁迅的致敬之作,它的主角是一个身处动荡时代,却总是想要逃避的知识分子。《马伯乐》可以看作是萧红版《阿Q正传》,其中引用了萧红从东北逃亡至武汉的这段经历。2018年,尚未写完的这“半部红楼”由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续写完成,他用英文续写了第十章到第十三章,再由其夫人、翻译家林丽君译成中文。
无论是许鞍华的电影,还是后续一些萧红作品的出版物,都沿用了“黄金时代”这个词。它并不指代萧红所处的那个年代,而是来自萧红旅居日本时写给萧军的一封信,“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象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
对于当时的萧红来说,“黄金时代”是带有反讽的,它依旧指向过往四处漂泊的境遇。如今身在日本,无需为生计和住所发愁,可以安稳地创作,已然是自己的黄金时代了。
可惜,这样的“黄金时代”太过短暂,在萧红的一生只占据了短短几个月。如果它再多一些,我们也许会看到作家萧红更丰富的创作生涯。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