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马克·麦卡锡去世, 他记叙黑暗残酷的美国西部

美国作家、电影《老无所依》的编剧科马克·麦卡锡,6月13日在他位于新墨西哥州首府圣达菲的家中安详离世,享年89岁。美联社援引常年生活在得克萨斯州的作家詹姆斯·韦德的观点评价麦卡锡,“几乎单枪匹马将美国西部带入文学领域”,对西部小说来说,他“超越并重塑了这一类型”,使之不再仅仅是供人消遣的类型小说,而是可以容纳严肃题材的文学器皿。
不同于很多作家、艺术家愿意向人们展示出一副精心雕饰的公共形象,我对麦卡锡生活细节的了解少之又少。他刻意疏离文学界,成为荒岛中的鲁宾逊,在他自足的文学宇宙担当造物主的角色。似乎只有透过他结晶出的文字,我们才能猜测他内心深处的隐秘。
但如此猜测,往往过于武断,缺乏深度:在文字中,我们看到的常常是我们自己的倒影。读者第一次窥见私人生活中的他,也是几经周折。1992年春,理查德·B·伍德沃德找到了这位隐士作者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寓所。
伍德沃德是一位纽约的艺术评论家,此行从东海岸的都市森林来到荒凉、空旷的美墨边境,是为了给《纽约时报》撰写一篇关于麦卡锡的报道。当时,麦卡锡正要在克里夫出版社推出他的新作《天下骏马》。
独居于此,麦卡锡不习惯媒体人,抑或文艺界人士打扰他。除了每天像工作般刻苦地铺开4个写作项目,为每个项目全神贯注地投入两小时,其余时间里,你很难把他的形象同一位可与唐·德里罗、托马斯·品钦、菲利普·罗斯并列的伟大小说家联系在一起。
他将自己的私生活埋在写作之下,就像一条暗河将它的汹涌埋藏在地表之下,纵使在写作中,一段壮美的西部传奇被创造出来,这传奇却不能照透那条隐秘的生活之河。他的个人生活至多是像水汽般渗入他的写作,除了那部他写了20年,取材自早年经历的《苏特里》外,他很少写大卫·科波菲尔式的自叙或自白。
麦卡锡和他笔下充满野性的牛仔后裔全然相反,他健谈、博学、乐观,毫不疲倦地投入人生。他曾告诉理查德:“一切都很有趣,我已经 50 年没有感到无聊,甚至忘记无聊是什么样了。”
但麦卡锡尚未将他的面孔置于聚光灯下。他的写作,在1992年前没有被美国的读者大众瞩目。但诸如《血色子午线》一类作品,已经以其坚实、残酷、启示录般的风格,在专业读者那里成为一种秘传,伍德沃德写道:“很难想象有哪位美国大作家如此远离文学生活:他从来没有成为新闻界的宠儿,作品从来没有畅销过,从来没有大肆宣传他的书,甚至从来没有接受过采访。他的精装版小说销量都没有超过5000册。”
《天下骏马》的出版,扭转了这一切。作为其“边境三部曲”的首篇,它引起美国出版界震动,首版精装本即卖出19万册,其后两月连印七次,都供不应求。整整21周,它都占据《纽约时报》“最畅销书”榜首,麦卡锡一跃进入公众视野。
他力道强劲的写作一直持续至今。在他身后,亦有足以扩展其文学版图的遗作《乘客》《斯特拉·马里斯》存留,并将引入中文世界。
麦卡锡的响尾蛇
美国的每个行政区都有专属的昵称与座右铭:前者凝聚着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朴素感受;后者更正式,是被镂刻进徽章与旗帜的格言,故需要从这一行政区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展望中提炼出来。
新墨西哥州的昵称,是“着魔之地”、“阳光之地”。其座右铭,则是一个拉丁语词语“Crescit eundo”,意为“增加”。
这片沿着经纬线被整齐切割出来的土地,原本并非美国所有。1846年美墨战争期间,美国在这片原属墨西哥的广阔边地上设立了临时州政府,美墨双方于1848年签订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后,该地正式成为美国领土。原本流动、模糊的边界,亦透过一次次购地协议固定下来。新墨西哥州成为美国南部边疆的中心点,同时也在西进运动中扮演枢纽的角色。
这片“着魔之地”,有着与东海岸十三州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地缘条件。1981年,当贫穷的青年作家麦卡锡获得236000美元的麦克阿瑟奖金后,他就选择以新墨西哥州为代表的西南各州,作为他的下一部小说《血色子午线》的取材地。
麦克阿瑟奖金又被称为“天才奖”,由约翰·D·麦克阿瑟基金会颁发。根据基金会的官方解释,该奖金“不是对过去成就的奖励,而是对一个人的独创性、洞察力和潜力的投资”。197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极力向麦克阿瑟基金会推荐当时仍寂寂无名的麦卡锡。历史学家和小说家谢尔比·富特也表示,他曾告诉麦克阿瑟的工作人员:“他(麦卡锡)会像他们给予他荣誉一样荣耀他们。”
尽管麦卡锡并非像《时尚先生》杂志谣传的那样住在石油井架下,但他在西部小城埃尔帕索的寓所也十分简陋。1982年,他在一家购物中心后面买下了一间漆成白色的石屋。石屋的装修工程,很快因资金缺乏而中止。
麦卡锡认定它“几乎不适合居住”,只把它当作晚上休息的地方,因此也拒绝领伍德沃德进到这间脏乱小屋的内部参观。他在石屋的储物柜里存放着约7000本书,很多都没有拆封。他已离过两次婚,贫穷、孤独,就像他石屋院子中停放着的各式年久失修的皮卡车。
多年来,他一直奔波在一家又一家汽车旅馆之间。那时他总会随身携带一只100瓦的高亮灯泡,以便可以在居无定所的深夜里读书、写作。当他得知自己获得“天才奖”时,他正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的一家汽车旅馆过夜。
诺克斯维尔县城,被环抱在美国东南部的山岭、丘陵、溶洞与高原中。而它所属的田纳西州像一只半打开的匣子,其辖区的形状是一个狭窄的平行四边形。麦卡锡在诺克斯维尔长大,1951年时,他进入田纳西大学,后又退学加入美国空军,去往阿拉斯加。
在阿拉斯加的空军基地服役时,麦卡锡经历了一次觉醒,他从此下定决心写作。在边地荒凉的冰雪中,他第一次感受到一种言说的欲望。就像一个初习某种外语的人,首次体会到一种陌生的声带颤动。他发现自己毕生的使命就在于他必须艰难地对着蓝天发出这第一个音节,为了这最初的声音,他开始大量阅读,以让词语洪流在他舌尖冲刷出一种专属于他的语感。
他于1957年返回大学,从原本修读的物理与工程学系转到英文系。获麦克阿瑟奖金之前,他就已经写过4部长篇小说。甚至为了写作,他将自己原本的名字“查尔斯”改成了“科马克”。他的新名字提示出他家族的爱尔兰背景。科马克原本是15世纪时一个爱尔兰领主的名字,这位领主修建的布拉尼城堡,至今仍存留在爱尔兰南部的科克市。
财富终于眷顾了他,似乎预示着冥冥中他要从田纳西重新出发,选择一个新的文学处女地。命运把他带到西部,而最终,他的书写与这片土地紧紧缠绕在了一起。
埃尔帕索拥有80%以上的讲西班牙语的人口。这座小城市位于得克萨斯最西侧,它沿着格兰德河铺展开来,如同一只回旋镖在两个世界之间往返:隔着河,就是墨西哥的华雷斯,向西则可进入新墨西哥州。
麦卡锡常常在美墨边境旅行,寻找灵感。那天,在新墨西哥州与得克萨斯州交界的梅西拉小镇用餐时,他开始向伍德沃德讲起他最近的经历。“在野外看到一种可以杀死你的动物非常有趣,”他说着,便和伍德沃德谈论起他在大弯国家公园遇到的莫哈维响尾蛇。
它们栖息在美国西南部与墨西哥中部的沙漠里。只要一提到它们,你就会联想起一幅荒凉、干燥的图景,一条柏油路像拉链一样笔直通过,让道路两旁的空旷咬合在一起,而这浅绿色的毒蛇在细沙上爬动时发出嘶嘶的声响。
麦卡锡停下车,小心翼翼地把蛇赶进枯黄的灌木丛。晚些时候,公园管理人员的话,让这位作家确信,他在和响尾蛇遭遇时已触到了死亡的边缘。“我们这里没有人被它咬过。”他告诉麦卡锡,“因为被咬过的人都活不下来。”
在写关于麦卡锡其人其书的报道时,伍德沃德一直在思考麦卡锡口中响尾蛇的意义。为什么这位作家一定要反复地提起这与他的文学无关的离题话?难道他要将他的自我隐藏在这冗长的生物学讲演中吗?
的确,席间,麦卡锡甚至饶有兴致地讲起响尾蛇的发育阶段,讲起自己在阿拉斯加野外径直遭遇一头灰熊时的感受。“这感觉很奇怪,”他用他柔和的田纳西嗓音咕哝道,“那里没有栅栏,而且你知道,在它厌倦了追逐土拨鼠后,它也许会朝你的方向移动。”
在空旷风景中与致命危险遭遇,这也正是《血色子午线》里常常会出现的场景。文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称,这血腥、华丽的小说为“一部真正的末世预言小说”。
而在伍德沃德看来,麦卡锡对响尾蛇的关注揭示出了他写作的一个核心特点:刻毒(Venomous)。“麦卡锡是一位详尽描绘人类残忍行为的作家,他很少用心理学的麻醉剂安慰读者。”伍德沃德评价道。
西南边境的血色与辽阔
与作者科马克·麦卡锡本人一样,《血色子午线》中的主人公“少年”,也是从田纳西来到西部的。
在小说有如圣经般庄严的开头,他如此描绘1847年的田纳西:“黑人在田间劳作,瘦削而佝偻,棉花蒴果中的手指如同蛛爪。黑暗版的园中痛苦。一些身影迎着下沉的夕阳,走在沉缓的黄昏中,穿过纸一样的地平线。一名黑人农夫独自赶着骡拖着耙,沿着雨打过的洼地步入夜色。”
当他在1990年代时独居于埃尔帕索的石屋时,田纳西作家麦卡锡的形象便逐渐隐去,代之以一个穿着牛仔靴、精力充沛的老者。他的头发已然花白,走起路来却像是跳舞,有着爱尔兰凯尔特人特色的蓝绿色眼睛深嵌于他的面孔,如同隐现于天际的晨星。
和小说人物共享由南方迁徙到狂野西部的经验,《血色子午线》成为麦卡锡的转型之作。他终于摆脱了福克纳式的美国南方文学在他前期写作中投下的巨大阴影。此后一生,他都像淘金者一样淘洗这个尚未被充分文学化的边疆。
尽管围绕西部,已经产生了太多流行文化符号如牛仔、左轮手枪、赏金猎人、印第安人,但对这片地域的深描却并不充分。而麦卡锡很早就表现出对西南边境的兴趣,在他看来,美国西部早已成为这个国家最著名的象征之一。
这片荒野向拓荒者们敞开,仿佛征服它就是美国的“天命”——这便是关于西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神话。但这个神话,其实就像肥皂泡一样短暂、脆弱。狂野西部权力半真空的社会形态,常被认为存在于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至1890年全美人口普查之间。
如同一场暴雨即将降临在干燥的广场上,拓荒者的那些定居点起初就像雨点,一滴滴稀稀落落砸在尘埃中。它扬起尘埃,提示着广场的空旷与荒芜,但这空旷荒芜很快就被迅速涌来的雨点覆盖。
政府建立起来,法律的齿轮开始运转,秩序的地基已然稳固,作为神话的西部便会消失。但也正因为这消失,西部永存于美国人的意识:独自居住在旷野,人必须足够强大,才能拥有对命运的把控感。
无独有偶,活跃在20世纪初的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也认为,西部构成了美国人族群认同的核心:透过向西的扩张,美国生活的流动性提供了“支配美国性格的力量”。
西进运动给予美国人的力量感、自我把控感,使他们不同于欧洲人,他们开始强调平等、民主与个人主义。但同时,在“昭昭天命”之下,合众国的灵魂也被种族主义的自负以及无序的暴力污染了。
印第安原住民被污名化为热衷于给拓荒者“剥头皮”的野蛮人,虽然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这些“野蛮人”很快就学会了西方人的技术,他们开始骑马游牧,使用枪支。1812年,为了对抗新生的美国在北美的扩张,英国甚至提议在五大湖区建立一个印第安保护国。
《血色子午线》,揭示了这种基于扩张主义与种族傲慢的美国精神的阴暗面。小说背景设定在美墨战争前后,主人公“少年”迷信暴力,14岁时便离家出走,前往墨西哥。后来,他在阴差阳错中加入了一支由罪犯、老兵和印第安人组成的赏金猎人队伍,在墨西哥的旷野中猎杀印第安人。28年后,这支队伍也被这无边的暴力吞没。
这本书中,时常有关于“剥头皮”的血腥描写。即使对它推崇备至的哈罗德·布鲁姆,亦承认这些可怕的细节时常让他不得不停止阅读。伍德沃德也说,《血色子午线》“可能是自《伊利亚特》以来最血腥的书”。
麦卡锡曾在1960年代居住于西班牙伊维萨岛,后来又长期生活在西语人口占多数的埃尔帕索与新墨西哥州,这使得他十分熟悉西班牙语。写作《血色子午线》时,他就参考了很多西班牙语文献。而西班牙语的句法也渗入他的英语写作之中,结出一种坚硬、简洁的风格。他喜欢简单的陈述句,并且从不使用在他看来极度愚蠢的分号,伍德沃德认为这种行文方式“让人想起早期的海明威”。
他拥有极其广博的兴趣。《血色子午线》不同于一般西部小说的地方,就是麦卡锡让智性之光散在这小说三棱镜般坚实的情节结构上,折射出丰富、细腻的层次,他将对历史、神学、哲学、科学的沉思融入其中。
他告诉伍德沃德,在中学时,他“是唯一爱好任何事物的人”。甚至,他“可以分给每个同学一个爱好,并且仍能剩下40或50个带回家”。中学时的麦卡锡从未设想过自己作为作家的前景,如若不是在阿拉斯加的那段阅读的时光,他或许会想做一个物理学家。他宁可与物理学家来往而不与文学家来往,他曾说:“物理学家在 20 世纪的成就,在人类事业中当属最杰出的那一部分。”
当问及他为何成为一名作家时,他最喜欢做的就是援引弗兰纳里·奥康纳对相似问题的回答:“因为我擅长写作。”只要被写作的激情俘获,他就全然投身其中,成为一名全职写作者。麦卡锡从未有过一份稳定、正常、世俗的工作。这让他的妻子感到苦恼。
1961 年,他与李·霍勒曼结婚,并在次年育下一子卡伦。夫妇俩住在一间棚屋里,棚屋远在诺克斯维尔郊外大雾山山脚下,交通不便,没有暖气也没有自来水。
为解决供暖问题,儿子诞生后,麦卡锡在他位于塞维尔县的小屋内建造了一个壁炉。当时作家詹姆斯·阿吉在诺克斯维尔的旧居正要被拆除,麦卡锡造壁炉的砖块,就是从拆除现场一块块捡回来的。
而当妻子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及育儿工作后,麦卡锡仍希望让她找一份工作,供养他的小说写作。霍勒曼因此负气出走,搬到怀俄明州并与麦卡锡离婚。
不过麦卡锡却对贫穷不以为意,即使他因没交电费被断了好几个月电,也是如此。成功后的麦卡锡回忆起这段摸黑生存的日子时,是这样说的:“总会有好事发生,那天我的牙膏用完了但却没钱买,我边苦恼着,边出门查看邮箱:里面正好有一支免费的样品。”
《天下骏马》之后
再见到科马克·麦卡锡,已经是13年之后。2005年时,他已经是一个早已实现了美国梦的,在商业和艺术上都非常成功的作家了。
在麦卡锡成为文学明星的前夜,伍德沃德拜访了他。那时在新墨西哥州谈论响尾蛇的两人,绝不会想到,这本即将出版的《天下骏马》,会在麦卡锡行将步入60岁时彻底改写他的命运。
成功并没有让这位老作家停滞,反而激励他写出更纯熟的作品。小说《穿越》作为“边境三部曲”的第二部,在1994年出版时刷新了《天下骏马》的首印纪录,仅在美国,其印数就超过20万册。
美国桂冠诗人、2008年度普利策奖得主罗伯特·哈斯在《纽约时报》评论道:“《穿越》是散文的奇迹,是原汁原味的美国杰作。”他认为,这部书的鬼斧神工,可与福克纳、莎士比亚、梅尔维尔等巨匠相比。
麦卡锡在1998年完成了“边境三部曲”末卷《平原上的城市》。与出版界对此事的狂热相比,麦卡锡的态度显得冷淡而谦逊。“很多作家都会写三部曲。”他如此告诉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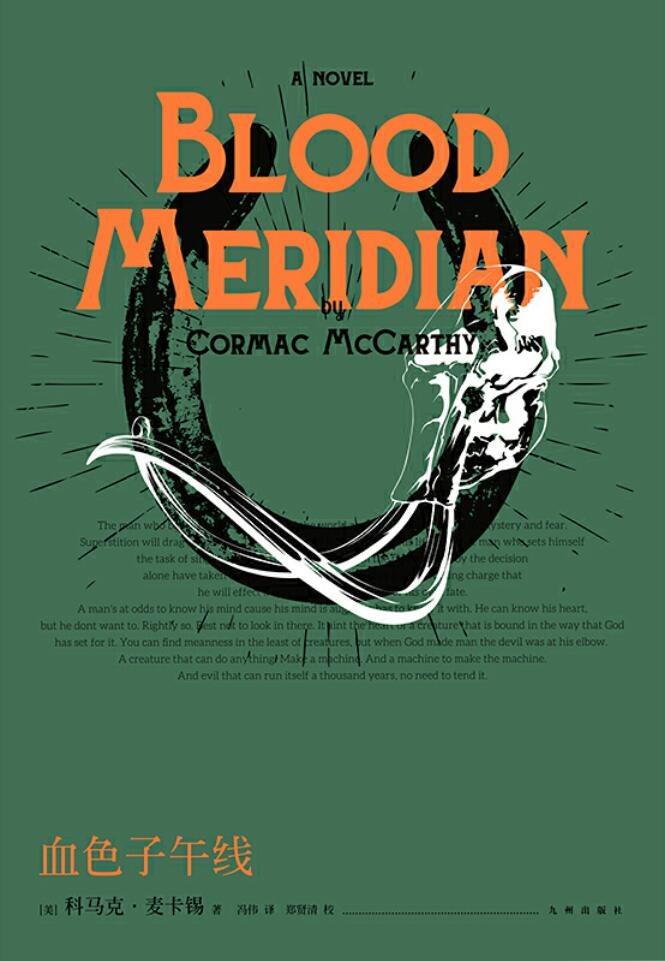
他几乎厌恶与人谈论写作或艺术,他更倾向于和一群科学家一起工作。所以,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他接受了多学科研究中心圣达菲研究所(简称SFI)邀请,来到圣达菲。在SFI,麦卡锡充分发展着他广博的兴趣。
他以德国化学家奥古斯特·凯库勒的一个梦为材料,撰写了一篇关于潜意识的本质及语言起源问题的论文。2017年4月20日,这篇论文发表在纽约的科学杂志《鹦鹉螺季刊》(Nautilus Quarterly)上。
有时,他也会受邀参加圣达菲本土一些有文艺界人士出席的晚宴。他不再和13年前一样拒绝出席,而是会去到会场,和那些作家孜孜不倦地谈论一匹马的优劣。
在SFI的停车场里,伍德沃德一眼便认出了这位老作家的坐驾。它与13年前他在埃尔帕索的那间石屋院子里看到的车别无二致,都是红色的福特柴油皮卡,甚至都还带着得克萨斯州的车牌。
在一众宝马、奔驰及丰田的包围下,麦卡锡的红色皮卡几乎要与停车场产生排异反应。他的主人、在SFI充当轮值研究人员的科马克·麦卡锡,是这里唯一的大学肄业者,也是唯一的作家。
穿过SFI明亮的大厅,如果足够幸运,你就能听到这位作家在他办公室里打字。他依然在用一台1963年上市的Olivetti Lettera 32 便携式打字机。这台机器的蓝漆已多有磨损,拉杆滑动时发出喑哑的声音。
不过,正如麦卡锡的朋友、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默里·盖尔曼所说:“没有任何地方像圣达菲研究所一样,也没有像科马克这样的作家,所以两者非常契合。”
每天,他都会穿上牛仔靴、牛仔裤和熨烫挺括的衬衫,像个牛仔一样走进SFI。在SFI,他没有任何公务,他的责任据他所说仅仅是“去吃午饭,参加下午茶”。
当然,他也会定期旁听SFI的研讨会,学习关于弦理论、朊病毒蛋白进化等细分领域的最新知识。有时,他也会参与讨论。盖尔曼说:“在一些研讨会上,当讨论涉及太多术语时,他(麦卡锡)会感到茫然。但即便如此,如果他不那么害羞,他也可能会问一些尖锐的问题。”
在SFI,他找到了自己的最佳状态,可以关注文学却不必被与文学有关的琐碎事务打扰。在这里,他进入自己的第三段婚姻,有了一个孩子约翰,也终于可以把他封在柜子里的书拆封。
“当除了写作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时,你能完成的事情真是令人惊奇。”他告诉伍德沃德。他已完成了他最新的小说,这部小说后来被科恩兄弟拍成电影,名叫《老无所依》。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