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许倬云: 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

“从大陆逃到台湾,在台湾重新生根发芽,长出新的中国的旁枝,这个是我们到台湾时最大的感觉。我亲眼看见美国在五六十年里的变化,却没有变得更好,我感受到它的衰退。”视频那端,远在美国匹兹堡的许倬云先生,双臂交叠,对着镜头缓缓地说。
许倬云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集中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中国上古史。近日,这位93岁的老人获得“2022-2023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过去一年,许倬云八易其稿,完成新书《经纬华夏》。新著以考古学为基石展开论述,考察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本学术著作,他感叹道:“我已老迈,大概再无余力撰写如此较具规模的专著”。
全书结尾,是这位常年心怀忧虑的鲐背老人对这个世界的殷殷嘱望:希望《礼记·大同篇》里的“大同世界”理想,早日在中国乃至世界落实。“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采人之长,舍人之短,在我们源远流长的基础上,熔铸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文化的初阶,在更远的未来继长增高。拳拳此心,以告国人。”
许倬云的学术成就,与其大时代下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在80岁时,他总结一生:“在时代巨变之中,残疾之身躯,随同父母,不断迁徙。二十岁前,未尝宁居,中年时,离台来美,不觉又已四十年,一生之半,在海外度过。一转眼,已是八十岁,眼看要终老异国。”
时光荏苒,又十三载,这段总结依然可以用。
“抗战是我非常重要的记忆”
许家所经历的动荡,是从太平天国时期开始的。
许氏家族是士大夫世家,清朝乾隆年间从福建搬到无锡,成为当地士族。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后,许家所在的无锡——这一全国最富庶的平原地区,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重创。军锋所至,文人士绅悉数逃散,许倬云的爷爷跑到外地做师爷谋生。待战乱落幕,无锡许家的26个男丁只剩下5个。许倬云的父亲许凤藻,出生于1891年,考上了位于南京、隶属于南洋水师的江南水师学堂,从此走上海军军官之路。
1930年,已经育有两儿两女的许凤藻、章舜英夫妇在厦门又收获了一对双胞胎,哥哥叫许倬云,弟弟叫许翼云。弟弟一切正常,哥哥却先天性肌肉萎缩导致手脚弯曲,一辈子离不开拐杖。
1935年,许凤藻携全家调任荆沙关监督,兼任外交交涉员。两年后,抗战全面爆发。7岁的许倬云对战时生活记忆深刻,“抗战是我非常重要的记忆,看见人家流离失所,看见死亡,看见战火,知道什么叫饥饿,什么叫恐惧,这是无法代替的经验。”
“我真正有记忆,忽然从小娃娃变成有悲苦之想,就在抗战时期一批川军赶赴前线时。”因身体原因不能上学,许倬云坐在家门口的抱鼓石上,望着延绵不绝的川军队伍从家门口走过。妈妈带着一群妇女忙着烧开水,给大军提供饮水。大人都在驻足议论:“这些人一个都回不来的。”
他见证了离乱,见证了伤兵们无可奈何的哀痛。伤员聚在村子的广场上,第二天死掉一半人,第三天又死掉一半中的一半人。医生们忙不过来,药物和耗材简陋,伤兵们喝了高粱酒,把酒倒在腿上后就开始被截肢,一时间鬼哭神嚎。每次看美国经典电影《乱世佳人》,看到伤兵一幕,许倬云就会想到家门口的惨状。这段经历,让幼小的他瞬间长大。
谈及抗战岁月,许倬云常感慨:“为什么我到五十岁才能原谅日本人?我不原谅日本军阀,我原谅日本人。”
许凤藻被派主持第五战区经济委员会后,工作重心是保障军粮民食供应以及安定社会秩序。随着战线的推移,父亲到处驻点办公,全家人只好跟着走。许倬云常常被安放在土墩上、石磨上,坐在小板凳上静静看众人干农活。这让他得以深入内地农村,了解长江沿岸的山川胜景及传统中国农村的生活习俗——这段艰难困苦的底层经历,成为他一生的精神底色。后来,他写作《汉代农业:中国早期农业经济的形成》一书,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托少年时期的切身经验,重构了传统中国农业基本盘的整体面貌。
关于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许倬云回忆:“在抗战逃难中,我是被背着走的,在湖北是背在背上,在四川是背在背篼里,我父亲单位里总是有身强力壮的人背我。”
“因为我一辈子不能动,不能跟人家一起玩,所以永远做一个旁观者,这跟我一辈子做历史研究有相当大的关系,历史学家也做旁观者。”这段经历,使得他终身的历史研究,都注重“常民”视角,而非传统的政治史或帝王将相。
抗战胜利后的漂泊,从无锡到台湾
抗战胜利后,许凤藻出任全国引水委员会主任,奉命恢复被战争切断的航道。短暂干了一阵子,就退休了。父亲刚一次性领到的退休金,遵照政府要求兑换成金圆券,就在急速通货膨胀中化为废纸。1946年,许倬云插班进入无锡辅仁中学就读高中。因为身体残疾,此前他都是在家自修,接受父亲、兄姐的指导。父亲读什么书,他便跟着读,而父亲最喜欢读宋代名臣的奏议。许倬云最初沉迷于看武侠小说,10岁时遵父命读《史记》。抗战时,他读了许多报刊,有《大公报》《观察》《时与潮》《东方杂志》。父亲无法对其进行系统教育,但会随机指点,比如在短波收音机上听BBC时,把欧洲战事进展结合地图,讲给在家自学的儿子。
辅仁中学创建于1918年,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预备学校。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大学,还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教会学校。抗战时期,辅仁中学搬入上海租界,抗战胜利后迁回无锡。学校教科书由上海印刷局提供,英语教科书从印度运来。
它是一所规模小,但教学严格的高中,教师多为无锡士绅家庭的知识分子。许倬云的两个哥哥都曾就读于辅仁中学,但他的身体情况特殊。父母去跟学校商议,学校只列出一项条件:第一学期必须及格。
难以想象,一个孩子跨过小学、初中,直接进入高中,怎能轻松应对课程?然而,学校确实为了帮助许倬云,把冒尖的十多个学生组成一个小班,开展“尖子生教育”。回顾中学教育,许倬云深感同学的提携,他也直言:“语文、数学很容易学,数学简直是天底下最容易学的,因为有迹可循。同样有迹可循的物理与化学也很容易掌握。”他认为:同学之间对他的帮助,不仅是补足了自己缺少正常教育的遗憾,而且,又因此得到许多同学互相帮助的经验。读完高中,父母准备送许倬云进入荣德生在1947年创办的私立江南大学。这所新大学以食品工程专业见长,但许倬云更属意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是《国史大纲》作者钱穆。
随之而来的世变,打乱了他的安排。1948年底,他随二姐许婉清夫妇南下去了台湾。
作为流亡学生,许倬云插班进入台南二中读高三。他觉得,这所学校比辅仁中学差太远了。读了三个月就高中毕业。考虑到手脚不便的他将来可以在家做翻译,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方东美的太太帮他填报了台大外语系。
草创初期的台大,学生少,老师多,学生有很多时间可以与老师交流。多年后,许倬云一直念念不忘如此密切的师生关系。在外文系一年后,许倬云转入历史系。因为校长傅斯年看到他的入学成绩,认为他应该去读历史系。
大二开始,许倬云以历史系为主,考古人类学系为辅。当时“中央研究院”迁台的人马多在台大兼课,许倬云有幸受到诸多学术大家指点,还常常是一两个人一班“吃小灶”。1953年,许倬云本科毕业并进入台大研究所,主攻中国上古史。研究所刚成立,没几个学生,老师还是原班人马。
他在台大的恩师有:考古学家李济之,曾主持河南安阳的殷墟发掘,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历史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沈刚伯,是西洋史研究的开路者;考古学家董作宾,是民国时期甲骨文研究最重要的甲骨学“四堂”之一;文化人类学家李宗侗,经常派三轮车接学生去家里上课;民族学家凌纯声,完成中国第一部民族学调查……
“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终身仰慕的楷模。我也没有专挑哪一位老师的路线,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他回忆台大时期的授业恩师时说道。


左图 抗战时期的许家兄弟。右图 上世纪60年代,许倬云在台大任教。
在美国近一甲子
1956年,许倬云从研究所毕业进入“中研院”史语所。在胡适的帮助下,他获得纽约华侨徐铭信的1500美元奖学金,得以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1957年夏,他坐船远航美国东海岸。不同于其他留学生坐飞机或快速客轮,他是廉价货船的“附带乘客”。这艘船装载着菲律宾出产的铁砂,慢吞吞地驶向目的地。
“船离开基隆码头,大约在黄昏时航向菲律宾。沿着台湾东海岸,眼看着台湾岛从绿色的山陵,逐渐退向西边水平线,渐行渐远,衬托西天云彩,宛如浮置于太平洋淡灰色海波上的一盘墨绿色盆景。”许倬云这样回忆第一次出国。
离开台湾,货船去菲律宾装货,再下一站则是夏威夷的檀香山。许倬云上岸参加观光团,印象最深的是无边无际的凤梨田、甘蔗田,以及建在甘蔗田边上的朗姆甜酒厂。实地察看,他才理解了农工业、资本主义经营、大规模生产的规模和性质。
停靠巴拿马运河时,闸门蓄水,几万吨的轮船被抬升,开闸,降水,船离去。许倬云第一次亲身体会到,现代技术的使用能够产生多大能量。
待船驶入美国最大的河口湾——切萨皮克湾,看着内湾又深又宽,两岸却很平坦,他感叹:“上帝对美国不薄!天造地设开了这一条航道,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如此的条件。”看见纽约的水运之便利,他愈发感慨:“美国的富足,除了人力以外,也有无可比拟的天然条件。”
1957年8月中旬,27岁的许倬云踏入芝加哥校园之际,美国的民权运动勃起,终于引发了阿肯色州“小石城事件”。州长抵制最高法院的判决,动用国民警卫队以阻止黑人学生进入高中校园,州的自治权与联邦权力发生冲突。总统艾森豪威尔将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派陆军101空降师去小石城,护送黑人进校园。许倬云刚巧见证了这幕风起云涌的巨变。
芝加哥大学,是当时美国中东考古乃至埃及考古研究最强的学校。许倬云进入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但因腿脚不便而住在神学院宿舍里。歪打正着,此地神学院的学生有反叛的传统,他们更加乐于投身民权运动,这也造就了许倬云的独特经历。这个撑着两根拐杖、腿上装着石膏套的中国人,跟在一群白人黑人后面,参与各种街头政治,比如去火车站接黑人,去监督社区投票……中国年轻人追求种族平等的精神,感动了美国人。
许倬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5年,每年有2到4个月在医院接受免费手术,矫治他的先天残疾。这家医院的定位是帮助穷人矫治小儿麻痹症,医生对许倬云的病例非常感兴趣。手术之后康复期间,是漫长难耐的岁月。幸而可以和许多残疾儿童的家长聊天,彼此都是同病的病人或者其眷属。在这一特殊场合,虽然生活背景各不相同,同病相怜,反而能敞开心扉,这也让他得以有机会了解美国普通民众的心理及生活。
许倬云日后回顾,自己在芝加哥“读了”五年的美国社会,并非全通过书本,“我的日子过得非常丰富:开刀、念书、搞民权、神学院宿舍里聊天。”经由如此的传奇经历,他见识了美国最底层的生活,包括美式政治中不完美甚至丑陋的现象。这种遭遇,其实是绝大多数留学生无从遭遇、也无法想象的情况。许倬云常常感慨:他何其幸运,能够因此病苦的遭际,反而有此机缘进入当地民众的生活深处,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与环境的关系。
1962年,许倬云拒绝了五份美国工作的邀请(其中包括芝加哥大学),选择回到台湾。当时,赴美留学的台湾学生普遍选择留美,许倬云是第一个学成返台的博士。之所以作此选择,是出于三个承诺:对母亲、史语所、台大钱思亮校长。回来后,他同时在史语所和台大工作,后来在台大做到历史系主任。
许倬云在学界可谓年少得志,做事直率的风格招人嫉恨,复杂的人际关系令他疲于应付。加之无法接受国民党对校园的干涉,1970年他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客座访问,迫于台湾的时局,选择定居匹兹堡至今。在台8年的一大收获是,他与小12岁的孙曼丽相爱而结合,他称其为“守护天使”。
许倬云说,自己在几十年里经历了美国最为繁盛的辉煌,也看见美国正在日渐衰败,这不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他告诉《凤凰周刊》:“因为这个国土曾经承诺给我们许多可以发展的空间、发展的线索。这会儿,没走完——甚至还没开始走,就败落了。这非常可惜,也非常令人难过。”
《万古江河》成畅销书
从1960年代开始,许倬云在台湾、美国不断教研与著述。据新近出版的《倬彼云汉:许倬云先生学思历程》记载,截至2022年,他共有中文专著58种、英文专著6种、中文合著及编著26种、英文合著2种,共计92种、212个版本行世。
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C.》,1965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哈佛大学汉学巨擘费正清评价为“小经典”。2006年,这本书在大陆翻译出版,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去年,根据芝加哥大学论文原版翻译的新版也已完成,预计今年内出版。新译本的名字更为明晰:《古代中国的转型期:春秋战国间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变动》。
1991年,大陆引进出版他的第一本书《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这本史学通识读物,由其上课讲稿和对话录组成,强调以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国历史——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
1994年,大陆出版他的第二本书《从历史看领导》。同年,他在大陆还出版了学术专著《西周史》。这本书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整合考古、文献、金文三方面的资料,从文化、观念、制度、生活等角度,论述了大一统的“华夏中国”是如何形成的。自1984年联经初版至今,这本书已经印行了十个版本,成为该领域必读的学术经典。
1998年,《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终于在大陆被翻译出版。同年,他还在大陆出版了《历史的分光镜》,这是由其学生陈宁、邵东方将其学术著作中的主要观点提要整理而成。
直到2006年,《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同步在海峡两岸出版,不仅获得国家图书馆文津奖,在海峡两岸销量也超过百万册。2019年7月,清华大学向新生发送录取通知书的同时,一并送上《万古江河》,校长寄语新生“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许倬云一生主张“为常民写史”,终于,他的著作由此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此后至今18年间,他在大陆出版新作近二十种,自选集、演讲集、旧书新版络绎不绝,成为这个时代最具公众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近年来,他的线上课程、演讲、谈话频频“破圈”,受到年轻群体的喜爱。2020年疫情初起,《十三邀》对他的采访播出,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现象,一句“往里走,安顿自己”令无数人闻之落泪。
即将出版的《经纬华夏》,与《万古江河》一样,有着一以贯之的“大关怀”。许倬云在新书末尾《余白》中描述这般继承性:“我平生著作,其计划与开展的过程,以《万古江河》最有特色。……这本书稿即将完成,本打算作为《万古江河》的续编,以补充过去陈述的分析以外,又在别的层面进行一些讨论,以说明中国这一华夏共同体,如何可以经历数千年而不败。这本书写作过程中,我的想法逐渐改变,终于走了完全不同的路线,可以说与《万古江河》居然脱钩,全然不同了。”他阐述两书的相同与不相同,“如此改变,是顺着自己的思考路线发展,顺其自然;而且因应着考古材料的众多,有一半以上的论述是有关考古成果的启示,而并不限于传统的文献资料所记载的范畴。”他觉得高兴的是,居然在整理地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时,他找到了一个缺口:将“祝融八姓”的扩散,与龙山文化后续者大汶口文化的衰退,结合为一个相关的现象,而归结于距今4000年世界气候普遍干旱、寒冷的现象。而且,在如此转移之后,中国的古代居然就从新石器时代转变为青铜时代。
在《经纬华夏》中,许倬云赞叹中国文化经历多次调整磨合后,呈现出来的包容性:“如此特色,在世界其他文化形成过程中,甚为罕见——很少有地理上如此完整的一片空间,作为族群融合的场所。于是,从本书陈述的时间看,中国文化跨度近万年,少说也有六千年。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这一个例极为独特。”他希望经由这本书,让国人知道——“天地之间应有如此的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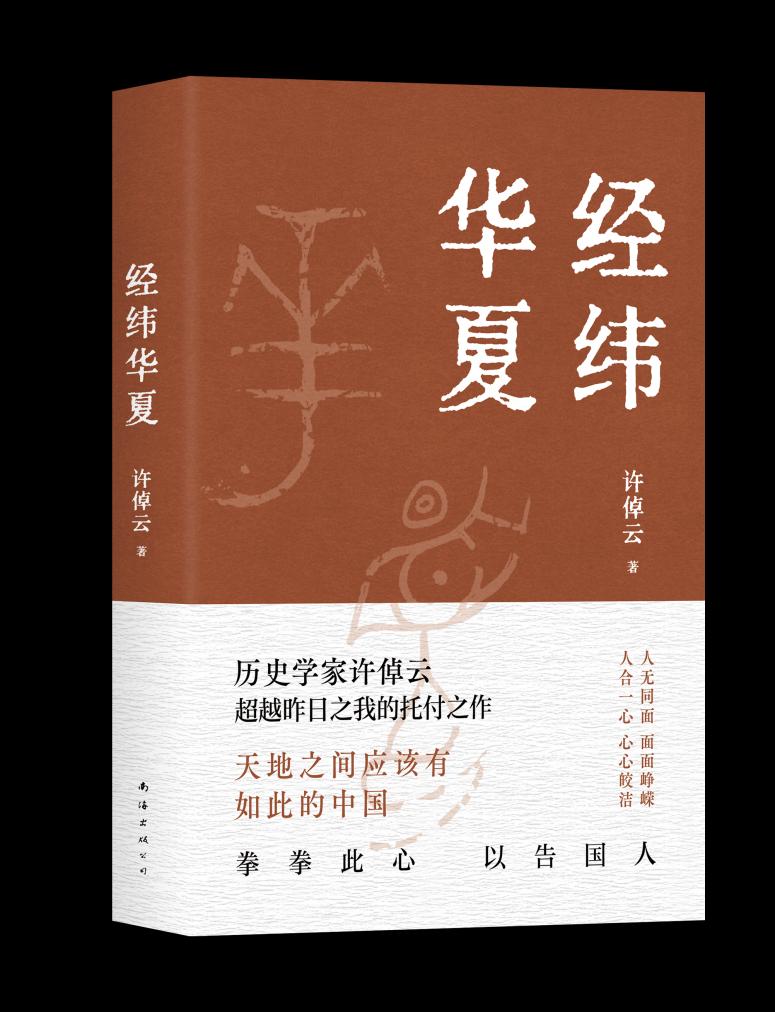
许倬云一直主张:读书固然重要,更要读“社会”这本大书——制度、规章、书本,往往与当下发生的社会现实存在相当程度的距离。九十多岁了,他还保持着少年时的习惯,每天看《纽约时报》《大西洋杂志》等英文报刊,以及两岸的中文资讯,为这个变化剧烈的世界心怀忧虑。限于身体他已经三年足不出户,但不妨碍他对新技术的关心、思考。对于个人主义之下日渐疏离的人伦关系,他显得忧心忡忡。《凤凰周刊》问道:“人工智能会对包括历史在内的人文学科造成什么改变?”他回复道:“我不担心AI超越我们,我担心我们忘了别人——人跟人之间不再有面对面的接触,人把自己封锁在小盒子里边,忘了外面有血有肉的别人。”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