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海而生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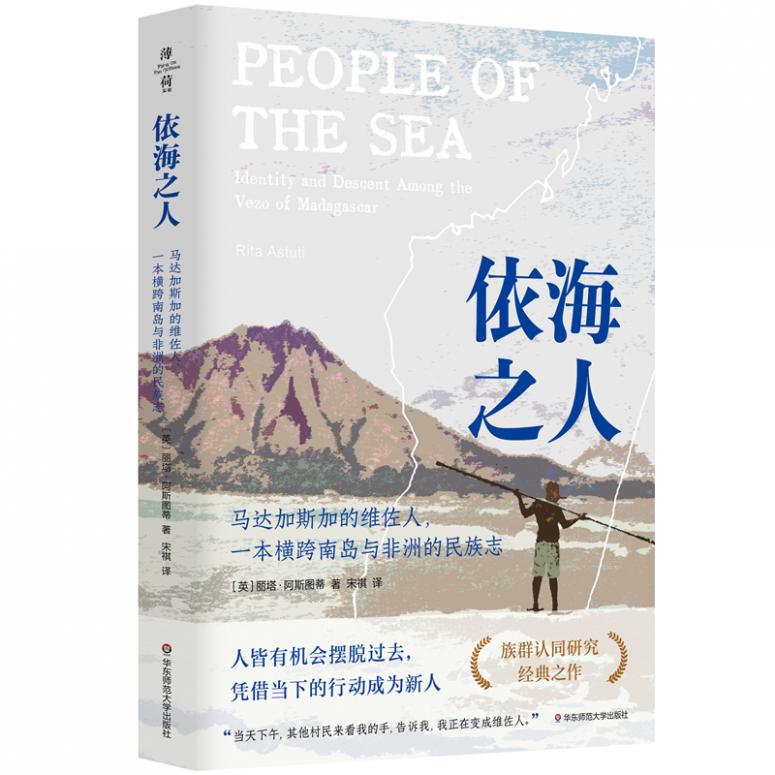
就在非洲大陆的东南角,如同一只遗失的手掌,马达加斯加岛静静地在海浪中合十。这座世界第4大岛,是最晚有人类涉足的主要陆地之一。直到约公元420年,才有南岛人自万里之遥的婆罗洲驾独木舟来此定居。
300年后,约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也来到马达加斯加,开始在此地建立贸易站,传播他们的宗教与文化。又过了300年,说班图语的黑人们也从非洲东南部移民至马达加斯加。这座岛屿遂逐渐形成今日多元文化共存的面貌。
《依海之人:马达加斯加的维佐人,一本横跨南岛与非洲的民族志》(以下简称《依海之人》),是英国人类学家丽塔·阿斯图蒂于1995年出版的作品。这部书描述了马达加斯加岛上依海而生的维佐人的习俗、文化与日常生活。
丽塔尤其注意对维佐人身份认同的研究。在她看来,维佐人这一身份认同既处在不断的波动之中,像海浪一样,只有在高高跃起时才能被称作“浪”,否则就永远是一潭死水。
但构成这身份认同的要素,也像构成了浪的海水,一直在低处潜伏着。每个人都可以是维佐人,包括从英国来的作者、一个白人人类学家。在与维佐人相处了18个月后,她因为她的一些行为,也会被她的维佐朋友辨认成一个维佐人。
那么,维佐人究竟是什么?在这座孤独的大岛上,他们这些海民,究竟怎样自处?他们是南岛人,还是非洲人?《依海之人》尝试寻找个中关键:确信维佐人的身份认同,怎样被架建,又怎样流动与变异。
谁是维佐人?
在马达加斯加语中,“维佐”(vezo)是“划桨的人”的意思。因此,关于维佐人,我们似乎拥有了一个极清晰的定义:他们是一群沿海的渔民。
他们的身份认同由其统一的职业而生,没有人会是天生的维佐人,因为没有人会作为一个渔民出生。在马达加斯加,职业不会像种姓一样烙在婴儿尚未成熟的脚踵上,人们凭自己的能力选择成为维佐人,或与之相对的马斯克罗人。
人们不能生而为维佐人,却可以生而为马斯克罗人。马斯克罗人是居住在内陆的农民,他们因自己与土地的关系而被抛入马斯克罗人的世界:一个充满秩序的,谨守节律的世界。
人与土地之间,有一根无形的脐带,不可见的血污从中沥下。人操劳土地就好像它是从人的身上剥下的一层皮,人要不停地用自己的血肉让它丰满,希冀某一日,可以得到它微薄的反哺——这就是维佐人眼中农民的世界。
在《依海之人》中,马斯克罗人时常作为维佐人的对立面而被提及:维佐人贫穷,马斯克罗人富有;维佐人不做计划,马斯克罗人精于计划;维佐人柔和,马斯克罗人苛刻……但实际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的通道从来都未曾关闭,马斯克罗人可以学习成为维佐人,反之亦然。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遭遇了海难,栖身的船在礁石上粉碎,你不得不抓住一块船板,不顾那如海蜇般生生刺进你手掌的木刺,不顾如口误般横生的船钉,你抓住它在巨浪中漂泊,最终停留在马达加斯加的海岸。
于是,在你被冲上沙滩的瞬间,你因你的幸存成为一秒钟的维佐人。只有维佐人才能够在如此的风暴中存活,不熟悉大海的马斯克罗农民,则必然葬身鱼腹。不过,你也仅仅是在这一秒内是维佐人。即使已成为维佐人,也会在不经意间丢失维佐人的身份:当海对他变得生疏,当他捕鱼时不再娴熟,他就不再是一个维佐人。
那么,外来者如何辨认出一个维佐人?凭借肤色、长相、身材,你都无法辨别出他们。维佐人的身份认同无关这些外在条件。
虽然渔民生活也会在他们的躯体上留下痕迹。丽塔注意到,尼龙鱼线会在他们手上划出一道道白色的伤口。这是他们与大鱼缠斗时留下的,鱼线反复割伤皮肉,久而久之便会形成一条细长的茧。
维佐男人的腰上也会有伤痕。在划着独木舟寻找新的鱼场时,他们会把鱼线紧紧缠在腰际。不久后,他们的腰上便勒出一道红色的血痕,这血痕渐渐化作他们皮肉的一部分,成为他们身份的印记。
他们常常会向丽塔展示手掌与腰间的痕迹,他们称这是“维佐人”的标志。
你也可以透过观察一个人走路的方式判断他是否是维佐人。维佐人常在沙地上行走,为了不陷进沙子里,他们走路时会将脚踵微微向外转动,并用脚尖抓地。当维佐人来到内陆,却依然坚持他们用脚尖抓地的习惯,他们的脚就会因此起满水疱。这些水疱,如同灰姑娘仙蒂的水晶鞋,我们在由它们带来的疼痛中确证着自己的身份。
与权力遭遇
最初来到马达加斯加的南岛人,可以说是天生的航海家。在欧洲人凭借近代航海技术开启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几千年,南岛人就从台湾出发,乘着他们的双体独木舟,在太平洋与印度洋四处迁徙。每一座可利用的小岛都有了人迹,马达加斯加的文明也由他们开启。
而进入16世纪,马达加斯加岛上兴起了两个主要政权:伊梅里纳王国与萨卡拉瓦王国。前者最终于19世纪建立了统一的马达加斯加王国,后者则被吞并,其法统被整合进伊梅里纳王国的法统之中。
王国之间纷乱的历史,似乎并没有影响到维佐人。也许正是因为被权力束缚,维佐人才把自己放逐到历史之外,成为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人。
她的维佐朋友执拗地坚持“维佐人没有国王”,“自从白人来到马达加斯加后就没有国王了”。的确,马达加斯加王国的建立,与法国对马达加斯加的入侵几乎同时发生。法国于1883年及1895年两次攻打伊梅里纳王国,最终于1897年将其吞并为殖民地。
但毕竟王权在岛上存在了三个多世纪,必定会在岛民的记忆中敲凿出一些痕迹。即使王权只是轻轻地凿下去,也会有回声,有一瞬间涌现的白色刻痕。这些不易察觉的痕迹往往残存在维佐人的集体记忆里,即他们口耳相传的故事当中。
国王常常要求维佐人纳贡,这或许是他对这群贫穷的海民维持最低限度统治的方式。维佐人之间至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国王来维佐人的村庄收取贡品。村民们纷纷呈上自己最好的鱼干。国王端坐着,让他的武士们把鱼干煮开,煮成鱼汤。他命令一个村民替他去喝这锅汤,因为他担心他的维佐臣民在鱼干中下毒。一层化开的鱼肉,像松脂一样在汤面漂浮,村民喝下鱼汤,过了好几个小时都无大碍。警觉的国王才终于命人把鱼干带走。但这些鱼干中的大部分,却都已经被煮烂了。
关于维佐人与王权遭遇的叙事,几乎总是他们在逃避王权的管辖。只要国王一来海边,他们就会出海。不过,苛捐杂税与国王的暴虐多疑,其实都并非维佐人厌恶国王的主因。维佐人真正厌恶的是,国王会肆意向他们询问其祖先的情况。
在马达加斯加语中,“历史”被称为“坦塔拉”(tantara)。历史学家费里-哈尼克提到,在马达加斯加,“坦塔拉”是不能分散的,因为拥有它代表着拥有一种宗教上的权力与威信。
萨卡拉瓦王国在统治其子民时,也将他们纳入王国的历史叙事之中。透过分享相同的历史,王国乃成为一个共同体,子民们得以洗去过往的身份,成为王国的一分子。维佐人拒绝将他们的祖先交给那一架编织历史的权力机器,他们知道,交出历史就是交出了现在。讽刺的是,萨卡拉瓦王国以及它的后继者最终湮灭无存,没有历史的维佐人却依然在海滩上蹑足行走。
为了生者与死者
《依海之人》最微妙的地方,在它的后半部。尽管维佐人的身份只关乎一个人现在的状态,但人终归要面对死亡,成为一个只属于过去的人,这样的人还能够是维佐人吗?丽塔认为,在人死后,他将被归入死者的序列,不再是维佐人。不过,虽然死亡让他不再被认为是维佐人,他也照样可以拥有一个身份。
这个新身份就像一个词语,一个词语的意义是由它在语言链条上的位置决定的。同理,一个死者的身份,也是由他在亲属关系——马达加斯加语称为“菲隆共尔”(filongoa)——决定的。
维佐人常说,“活着的人有八个壤葬”。这里的“壤葬”,是指“过去死掉的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八个壤葬指的是八位死去的曾祖,父母两边各有四位。这就造成了疑难,当一个维佐人死去时,他并不被允许平均地葬在这八个壤葬中,他必须选择其中一边:父亲这边或母亲这边。
由此便有了索颅仪式。在一对夫妻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孩子父亲要向孩子母亲一家的壤葬献上祭品,索取将来安葬孩子遗体的权利。如果没有举行过索颅,则这个孩子将来便只能归于母亲的壤葬。
维佐人把刚出生的婴儿看成是没有骨头的“水宝宝”,它是由海洋赠送给他们的生灵,是他们对它的爱使它生出了支撑自己一生的骨头。正是因为爱,他们才如此认真地考虑死亡。诚然,他们不会像马斯克罗人一样长时间地守灵,直到死者的遗体腐烂。对死亡,他们的态度有时近乎唯物主义。死亡就是死亡,死者已再无知觉,所以,他们的葬俗是简便的。
但这简便之外也有动人的地方。不习惯攒钱的维佐人,为了给逝去的亲人更换混凝土十字架,可以拿出捕鱼旺季全部的收入,举行一场盛大的十字架仪式。不同于葬礼,十字架仪式是一种召唤。它召唤那些死去亲人的灵魂重新回来昨日一同生活的村落,召唤他们去看,他们不在的时候他们的子孙是怎样为他们开枝散叶,召唤他们去看融入了海水的夕阳,去看满载星光与渔获的独木舟……
死者与生者分享着记忆,一同狂欢。沉重的混凝土十字架,在平放时,就是死者的另一副永不腐败的身体。人们为它漆上新漆,抚爱它,与它游戏,仿佛它有血肉。欢快的人群扛着这十字架,他们不时停下,开始跳舞,或者向举行仪式的人家索要朗姆酒。而当它伫立于墓园,取代原本吱呀作响的木质十字架,它就是死者灵魂复生的证明。
虽然他的手上不会再有鱼线留下的新鲜勒痕,虽然依照习惯死者已不再是维佐人,但只要他仍在这壤葬之中,他就仍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存在。只要他不被遗忘,他就永远是他们的亲人,永远是这世界上的一部分,向着海洋而生的一部分。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