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法就是人与世界的连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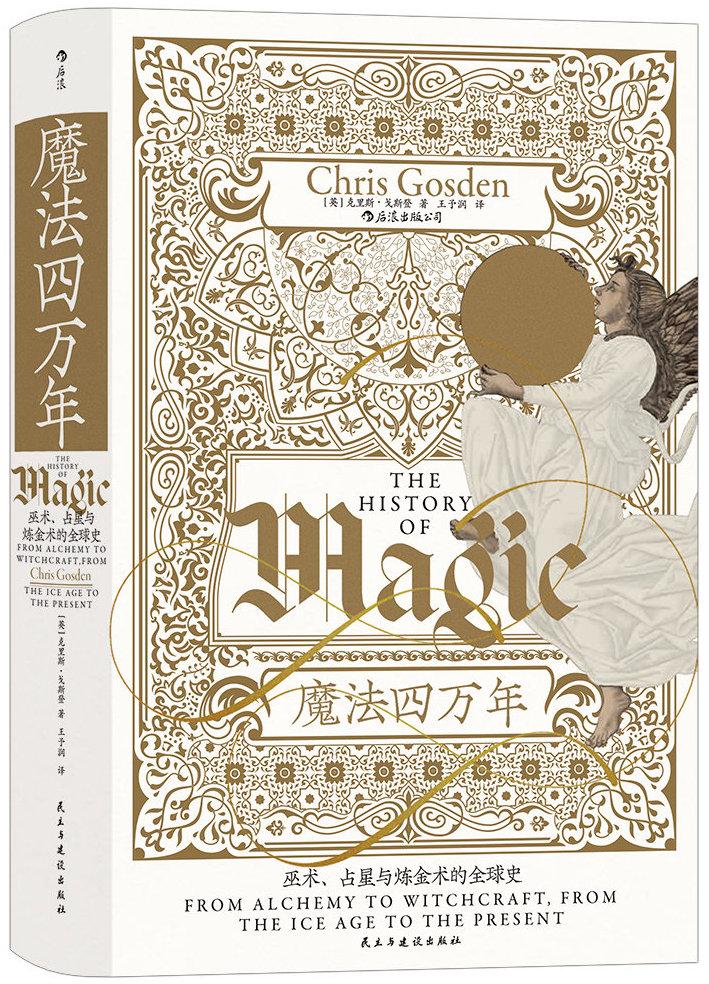
福尔摩斯之父柯南·道尔(Conan Doyle),和科学家牛顿都曾醉心于魔法。这虽然并不意味着魔法优于科学和理性,但也可见魔法的顽强生命力。
在本书作者、英国考古学教授克里斯·戈斯登(Chris Gosden)看来,魔法不是早已落伍的迷信思想或拙劣的骗术,更有着值得现代人借鉴的伦理内核。正如作者所说:“我们将继续使用科学来理解和改变世界。但魔法能够扮演兄长的角色,让科学技术的能量平静下来,让我们思考科学发现的终点在何处。”
魔法与科学并非水火不容
那是1897年的一个春天,铁打的汉子福尔摩斯也熬不住常年的辛劳,只好去英国西南角的康沃尔(Cornwall)海滨休假。在柯南·道尔笔下,康沃尔是一片“远离现代文明的地方”,就连语言也与迦勒底语相似。迦勒底(Chaldea)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自己的国家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灭亡,大致相当于春秋中期晋国与楚国争霸的年代。到了公元前后,迦勒底人的名称都几近湮灭,他们在外人乃至自己口中都叫做叙利亚人或亚述人。
在这里,福尔摩斯再次遇到了死亡事件。前一天晚上,三兄弟和妹妹在家里打牌;到了第二天早晨,却只留下两个兄弟疯疯癫癫地跳舞,妹妹则已经殒命。在还原现场的过程中,福尔摩斯和华生更是经历了凶险而诡异的体验:“眼前出现一片浓黑的烟雾……在这些烟云中,即使现在还看不见,但会跳出某种令我惊恐的、邪恶的东西,它极端恐怖,是宇宙中最最可怕的恶魔。在黑色的云边,一些模糊的形状盘旋其中,每个看起来都那样地险恶,似乎凶险随时都会降临,又像门槛边有某些不知道的可怕东西将进来摧毁我的灵魂。”
当然,与崇尚理性与文明的19世纪大不列颠一样,福尔摩斯的世界绝没有真的魔鬼与恶魔。见多识广的福尔摩斯其实早就认出,这烟来自一种产自非洲的根茎类植物,燃烧后就会产生致幻的神经毒素。至于真正的罪魁祸首,十有八九还是人,也就是四兄妹中唯一的幸存者。以上就是《魔鬼之足》故事的梗概。
从文学技法的角度来说,用幽远诡秘的环境来烘托气氛、制造悬念,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对当时的福尔摩斯之父、英国小说家道尔来说,故事中也带有着现实亲身经历的影子。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道尔对超验世界与精神追求就越来越感兴趣,频繁参加降神会,相信能够借助灵媒与死者沟通。降神会通常在阴暗的房间里进行,就算是夜晚也要拉上厚厚的窗帘,浓重到呛人的熏香也是常见配置。
《魔鬼之足》发表于1917年,而在下一年,道尔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灵性主义著作《新启示》。道尔的这种信仰一直保持到他1930年去世,甚至在去世之前三年,他还在访谈中畅谈福尔摩斯与灵性的内在关系。
长期以来,这被认为是道尔人生中的一大污点,为他作传的人要么避而不谈,要么不得不用大段篇幅来解释福尔摩斯之父为什么会“鬼上身”。毕竟,当时就有人指出道尔被骗了,他信以为真的所谓通灵现象,不过是拙劣的障眼法或者早期的照片修改技术。另外,道尔是战争的间接受害者。他虽然没有亲自上战场,但他的次子当了侦察兵,而且最后死于肆虐欧洲的西班牙流感。他观察和听闻的战争惨状,再加上丧子之痛,或许就是他遁入虚无环境的根本原因。
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即便当时还有许多大人物同样热衷此道,比如弗洛伊德、狄更斯、叶芝等等,这也并不能证明真的存在另一个世界。不过,我们也不妨想一想,是怎样的愿望和追求驱动着这些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聪明人。《魔法四万年》中对此给出了一种有力的正面答案:“其他世界的存在者也可能掌握我们所没有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灵魂能看到未来,或是理解事件的深层肇因,而那是我们普通人无法知道的。”
这种思维方式由来已久,比科学乃至宗教都要久远得多,而且曾长期与两者共存。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说:“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后一位魔法师。”
牛顿醉心于炼金术,留下了上百万字的研究文稿,还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安装了两个室内冶炼炉,后来为了方便实验,才把场地转移到学院门口的小屋内。显然,炼金术并不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是真心以炼金术士自居的。除了做实验以外,他还将大量精力用于破解古代先哲的文本。与所有炼金术士一样,他想要造出最纯粹的哲人石。只不过,他并不指望靠点石成金赚钱,也对长生不老意兴阑珊,他的最高追求是窥测万物化生的大道。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威廉·纽曼(William Newman)所说:“牛顿甚至发展出了一种‘万有理论’,通过一套涉及金属蒸汽、大气和各种形式的以太的交互作用循环系统,来解释有机生命体、热量和火焰的起源,引力的机械性起因,内聚力、金属和矿物的生成等万事万物。”
当然,从效果来说,牛顿的万有理论失败了。尽管直到20世纪初,牛顿三定律都是人类理解自然世界的基本框架,但牛顿万有理论对具体现象的解释力远比不上后世提出的物理学理论,也从来没有得到学界和大众的普遍认可。
由此可见,牛顿与其说是理性时代与蒙昧时代的分水岭,不如说是试图融合机械世界观与魔法世界观的最后一座高峰。在他之后,以科学为代表的机械世界观凯歌高奏,将炼金术、占星术、巫术这些老伙计远远甩在身后。到了科学昌盛的维多利亚时代,试图穿透物理现象世界、洞悉终极真理的种种秘术早已沦落,只能以怀旧或欺骗的形式苟延残喘,至今依然如此。
关怀是魔法世界观的核心
道尔和牛顿并不是在追求邪魔歪道,反而是在传承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这种传统能够超越停留在感官表象的自然科学。至少,他们两人自己是这样认为的,而且这条传统也确实存在。戈斯登将其称作“魔法”。在他看来,魔法就是人类直接参与到宇宙中,宇宙则反过来影响和塑造人类。科学则是将人类与世界抽离,用抽象的语言来观察和理解世界,最终操纵世界。
两相对比,魔法似乎就显得接地气一些,多了些温度。难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会带着乡愁写道,与禁欲的新教相比,“对于各种民间宗教而言……这个世界还是个巨大的魔法花园”。这一点,在古埃及的魔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现代大众文化中,古埃及魔法是一种可怕的黑魔法,比如图坦卡蒙的诅咒,他是一位英年早逝的法老。1923年,英国考古学家卡那封伯爵(Earl of Carnavon)发掘了图坦卡蒙的陵墓。按照中文世界的通行说法,图坦卡蒙的墓室中有一句诅咒:“任何怀有不纯之心进这坟墓的,我要像扼一只鸟儿一样扼住他的脖子。”结果,卡那封没过几周真的就去世了。
上述说法基本属实,只是诅咒其实来自另一位法老的墓室,而那位法老生活的年代比图坦卡蒙大约早了一千年。在古埃及题材的神话影视作品《蝎子王》与《木乃伊》系列中,埃及魔法的主要作用也是破坏、杀戮与复仇。
但在现实中,古埃及魔法的主要意图是保护生者与亡灵。就拿《亡灵书》来说吧,这其实不是一本书,而是古埃及坟墓铭文的汇编。古埃及人相信死者必须经历冥界的一系列恐怖之事,然后才能过好人生的后半程。墓室铭文就相当于地图和小抄,帮助死者找到正确的方位路径,妥帖地回答问题,尤其是在负责审判死者功过善恶的奥西里斯面前。如果冥界中有鬼神质疑死者有没有权利获得面包,死者应该这样说:“我是在赫利奥波利斯拥有面包之人,我的面包在天上由太阳神保管,在地上由大地之神克卜保管。夜船和日船会从太阳神处,将我要吃的面包送来。”否则,可怜的亡灵可能就要在冥界饿肚子了。
古埃及陵墓中的经文是为了保护墓主个人及其家族,而气势恢宏的古埃及神庙则是为了守护世界的秩序。与基督教堂、犹太教会堂、清真寺、佛寺不同的是,古埃及神庙并非信徒膜拜神灵的场所,而是避开世人的神灵居所。正因如此,典型的古埃及神庙尺度巨大,采光不足,也没有信徒聚会的空间。在古埃及人眼中,世间万物都是由魔力(heka)创造和维系的。魔力本身无所谓善恶,只看使用者是好心还是坏心。诸神比人类更善于利用魔力,这也意味着神一旦用魔力做坏事,就会让世界陷入混乱,比如尼罗河不规律的泛滥。
为了维护世界的秩序,古埃及人修建了神庙,还开发了包罗万象的咒语与护符,只有经过常年艰苦训练的祭司才能正确进行复杂的仪式。正如《魔法四万年》中所说:“古埃及人寻求的秩序的基础是种种形式的宗教和魔法,它们将生者与死者、诸神所在的宇宙与人类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魔法就是善的。古往今来,诅咒一直是魔法的重要用途。比方说,一座位于今叙利亚的希腊古城,出土了一块大约1500年前的石板。石板作者大概是一名赌马的人,马车竞速是古典世界的一种热门运动。石板请求神灵,绑住对方赛马或赛车手的“双脚、双手、肌腱、眼睛、膝盖、勇气、跳跃、马鞭、胜利和桂冠”。
在英国史学家埃丝特·埃丁诺(Esther Eidinow)看来,这种带有强烈功利与竞争意识的魔法来自古希腊的焦虑文化,根源是变幻不定的人际关系。换句话说,古希腊人对世界还是怀有敬畏之心的,并不企图驾驭宇宙力量为己所用。与强调和谐与专业技术的古埃及魔法相比,古希腊魔法具有更强的主观意识,但这并没有改变一个基本观念:魔法的本质是参与,是融入到星辰、鸟兽、草木和人共存的世界中。
在《魔法四万年》的作者看来,从改造世界和生产器物的维度来看,魔法永远不是科学的对手,但那也从来不是魔法的追求目标。正如戈斯登所说:“从几乎所有意义重大的魔法世界观的衷心,我们都能看到一种关怀的伦理。守护者的职责至关重要,其核心在于希望将一个处于有益状态的世界传给后代,而不是一个被破坏的世界。”在全球环境危机频发的今天,魔法或许提供了一种共同生活的可能性。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