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现代帝都的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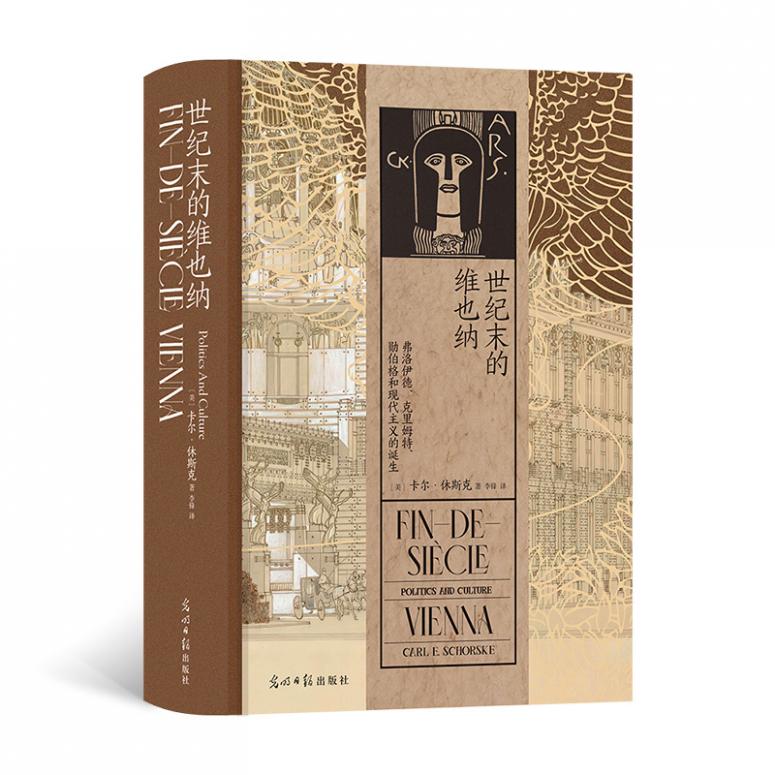
美籍德裔学者卡尔·休斯克(Carl E. Schorske),教授现代欧洲思想史,他以切身体会写下《世纪末的维也纳》。他感受到,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思想“进入一个无限创新的漩涡中”,没有任何一个概念能把握万花筒般的知识界图景。19世纪末的维也纳新旧精英杂糅,知识界革新乃至革命层出不穷,恰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回溯与分析的理想样本。
他采用了“挖洞插杆”的方法,分别考察了文学、政治、精神分析、美术等领域的内部发展历程,让它们彼此照亮,共同搭建一个连贯的世界。而维也纳环城大道正是他插下的一根杆子。休斯克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理论反思切入,探讨了19世纪城市形态的变化与思想界的反应。
迟暮的要塞
1908年,一名来自奥地利西北边陲小镇的19岁青年,来到帝国首都维也纳,追求艺术事业。他的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多年后,他在监狱里这样描写自己当时的感受:“我能一连几个小时站在歌剧院前,一连几个小时盯着议会大厦看;对我而言,整个环城大道有如《一千零一夜》中的魔法。”
这些恢宏大气的纪念碑式建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的主张恰恰与环城大道建设者的议会自由主义思想背道而驰。30年后,他将以德国元首的身份重返环城大道,检阅即将荼毒欧洲的大军。那么,环城大道是什么呢?
简言之,环城大道是19世纪中叶维也纳城市大改造的核心成果。与大约同时期开展的巴黎改造项目一样,环城大道是现代城市规划早期的硕果,而且它们都与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有着直接的关系。
2月22日,巴黎民众在狭窄的街道上构筑工事,与政府军发生冲突,最终导致首相辞职,国王流亡海外。受此鼓舞,维也纳在不到一个月后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奥军无力镇压,退出城外,执掌国政近30年的首相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下台。
但是,尽管有着相似的军事和政治背景,维也纳和巴黎在改造前的格局并不一致,一个最显著的区别是,维也纳有一大片现成的“缓冲区”。从1844年的地图来看,维也纳城区分为三个圈层,中央是内城,然后是一圈空白,最外面是郊区。如果只从民用角度来看的话,这是最糟糕的规划:空地不仅浪费空间,而且隔绝了内外城的交通与互动。
不过,内城与外城边缘的犬牙状曲线揭示了这种格局的由来:维也纳原本是一座巨型要塞。敌人在攻破最外层的城墙之后,先要穿过居民区,来到一片最长可达1公里以上的开阔地。中央堡垒中的守军享有一览无余的视野与射界,对攻城敌军造成致命的杀伤。就算敌人要挖地道,缓冲区也能为守军争取到更多待援时间。连绵不断的犬牙,是一座座外凸的墙体,方便守军从两侧夹击来攻的敌军。自中世纪以来,类似格局的要塞城市在欧洲遍地开花,至今还遗留着不少,比如以同名桌游闻名的法国南部城市卡尔卡松(Carcassonne)。
维也纳在16和17世纪多次遭到土耳其军队围攻,小规模劫掠更是家常便饭。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维护军事功能无疑是必要的。但到了19世纪,奥斯曼帝国即将或已经沦为“西亚病夫”,古老的先军格局就显得很过时了。正如休斯克所说:“维也纳能在其中心位置有一大片用于现代开发的空地,是它在历史上的落后使然。在其他欧洲都城将自己的防御工事夷为平地多年之后,维也纳却依然完好地保存着它。”这就决定了维也纳城市改造的基本方针:军事缓冲区民用化。
为了镇压暴动方便,军方抵制多年,最后也保留了一些要地,尤其是火车站旁的巨大军营。然而,时代的潮流终究不可阻挡。1857年,皇帝颁布法令,宣布成立城市扩建委员会。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一座座象征着新时代的纪念碑式建筑,在缓冲区上拔地而起,为新的掌权者加冕。
装着新酒的仿古瓶
环城大道上有一连串宏大的公共建筑,均匀分布。正西侧的大广场周围,有市政厅、维也纳大学、城堡剧院和国会大厦。沿着逆时针的方向走,我们会接连遇到一连串文艺场所:特蕾莎广场两侧的自然史博物馆和艺术史博物馆,《唐璜》首演场地维也纳国立歌剧院,还有紧贴环城大道外侧的金色大厅。国会大厦的设计者是丹麦建筑师特奥费尔·汉森(Theophil Hansen),位于内城一侧的证券交易所也是他的手笔。
从游客的视角来看,这些建筑无疑古色古香。维也纳市政厅有一排哥特式建筑的标志性高塔,看上去和建于15世纪的布鲁塞尔市政厅差不多,甚至和始建于13世纪的科隆大教堂也区别不大。外立面宽阔且中央突出,内有大幅天顶画和大量雕塑装饰的城堡剧院,则神似法国的卢浮宫。这种观感并非无知游客的错觉,环城大道也不是批量制造的当代商业化古城。
仿古一方面是为了唤起市民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也尴尬地体现了自由主义者的浅薄根基。对奥地利来说,代议制是晚近的舶来品。这就意味着,奥地利议员们不能像英国人一样在国会广场里摆放历任首相的雕像,更不可能用纪念碑来缅怀逼迫国王签订《大宪章》的男爵们,或者建立英吉利共和国的克伦威尔。于是,环城大道上出现了8位古希腊罗马历史学家的雕像,议会大厦正前方有了一座巨型雅典娜雕像。
新建筑或许借用了教堂与王宫的外在形式,但从规整的格局与建筑的功用中,我们都能窥见19世纪欧洲自由主义鼎盛时代的灵魂,尤其是市政广场周围的建筑群。正如休斯克所说:“它们……代表了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议会大厦中的议会政府,市政厅中的市政自治,大学中的高等教育,以及城堡剧院中的戏剧艺术。”
与封闭的内城王宫相比,环城大道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布满了任何人至少理论上都可以进入的艺术文化殿堂。而与污秽杂乱的平民区相比,这里又洋溢着典雅文化氛围。因此,环城大道不仅是空间上的中间地带,沟通了内城与外城,同时也代表着普罗大众与封建贵族之间的社会群体,也就是以精神贵族自诩的新兴资产阶级。
在这个意义上,环城大道是资产阶级为自己开辟的空间领域。他们在议会大厦中参与国政,在大学中培养下一代的政治与文化精英,在剧院和博物馆中接受历史与审美的熏陶。当然,这是奋力抗争的结果。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维也纳大学。
维也纳大学原本位于内城,但由于大学师生在革命中奋力抗争,政府将校址迁出到了多座分散的外城楼宇中。之后,筹建集中新校区的运动,持续了整整15年。直到1870年,在自由派掌控的市议会支持下,皇帝才同意建立新校区。令人惊讶的是,新校址不仅就在国会大厦对面,而且原本是军方的阅兵场。维也纳大学新校区是环城大道最晚一批落成的建筑,是奥地利自由主义者的一次重大胜利。
反思城市病的先驱
宏伟的公共建筑需要海量的经费,这笔钱从何而来呢?简而言之:卖地。城市扩建委员会将环城大道划分成一个个地块,拍卖给开发商,所得收入用于修建公园、博物馆和剧院。这种如今司空见惯的模式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而且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于是,一批批适应资产阶级生活的新式住宅楼涌现了出来。
最先出现的,是面向中产阶级的小户型公寓楼。从街道一侧看,这种楼就像一个个方盒子挤在一起。老港片中不乏类似格局的街道,只是香港的同类建筑楼层更多,街道更窄,而环城大道没有花花绿绿的招牌,以维护帝都的威严市容。接着出现了贫富混居的公寓楼。奢华不亚于王宫的大楼梯,只通到下面两三层,再往上就只有简易楼梯间了。
除此之外,针对拿下了一整个地块的大开发商,前面提到的议会大厦设计者汉森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团体公寓楼。顾名思义,一座团体公寓楼可以看作众多单体公寓楼的组团,但有统一设计的外立面和共享的内部庭院。从鸟瞰视角看的话,团体公寓楼有点像放大拔高版的四合院;而从功能角度看,又像是多户混居的大杂院,只是风格上往往要恢宏得多。
尽管这些新式住宅楼的格局、风格、价位、地段、目标人群都有显著差异,但它们也有着突出的共同点,那就是整齐划一的高密度网格模式。于是,建筑师卡米洛·西特(Camillo Sitte)对“我们这个数学世纪(即指19世纪)”发起了挑战。
他说:“一座城市的建造必须让其公民同时感到安全和幸福。为了实现后一个目标,城市建设就绝不能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最高意义上的美学问题。”放到现在,这句话也许听上去是一句俗气而空洞的口号,甚至是开发商自抬身价的虚伪标榜。但回到“现代大都市”还是一个纯粹的褒义词的19世纪,西特的思想无疑是有些超前了。事实上,西特的实际作品并不多,他的主要成就在于传播人文城市的思想。
西特的核心现实主张是广场,但不是4万平方米的维也纳市政厅广场,更不是44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而是从街道自然围合与延伸形成的小空间。用现在的话说,西特应该会主张布置大量贴近居民的街心花园。他的眼光是向历史回溯的。
他心目中的模板,是古希腊的集市(agora)、古罗马的论坛(forum)和欧洲中世纪城镇的广场(town square)。它们虽然有不同的叫法,虽然从汉语通用译名来看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其实都是同一类空间:市民交流、活动与会面的场所。货品买卖、聆听发言、哲学讨论、集结出城只是它们众多功能中的一小部分。
但正如休斯克所说,西特的执着“并非仅仅出于一种学究气的浪漫怀旧”。他出身工匠,致力于保全在奥地利尚未彻底死去的手工业。在现代学术的框架下,西特出任国立职业学校的校长,开设了从陶艺到木雕的大量工艺课程,以期在工厂世界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出一块生存空间。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