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诗人也斯的成长史

香港,2013年1月5日,一个潮湿却温和的星期六。相较前几日,能见度变低了,整整9小时,人们都看不清这座城市。电视里滚动着新闻:位于离岛喜灵洲的惩教所里,中港与印巴裔的两帮男囚互殴;一种新的“夜光”蝴蝶兰被培育出来,这一年是蛇年,兰花供应商也让兰花与蛇押韵,培育出了“蛇纹”兰花。
就在这天,罹患肺癌3年之久的香港作家、诗人也斯(原名梁秉钧)辞世。就像一粒石子落入水中,留下回声与涟漪,却只被少数知音听见。
如同他的笔名,由两个常见的文言虚词组成:“之乎者也”的“也”,“彼何人斯”的“斯”。他希望透过两个无意义字眼的组合,悬置读者对他的阅读期待。一个甜腻的笔名,例如“琼瑶”,让读者只见其名就能预料到她的风格。也斯却让自己的笔名保持着神秘感,仿佛他料想到,在香港这座常被认为高度商业化的城市,他与他的文字会是寂寞的,近乎“空”。
但他的创作绝非如卡夫卡般向内塌陷,而是极为丰盛地向外打开。也斯的作品涉及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摄影、评论、文化研究等领域。自1970年代起,他参与编辑《中国学生周报》《大拇指》等报刊杂志,在内地及港台出版《雷声与蝉鸣》《游离的诗》《博物馆》《也斯的香港》等书。
他亦曾多次赴美国讲学,更在1998年应德国学术交流协会奖学金之邀,成为驻柏林艺术家。在香港文坛,他被视为“对话王”,经常大胆跨界,与艺术家及社会公众分享他的创作。
借着文学艺术,他的足迹踏遍欧美与两岸。每到一地,他都会用文字与图像为它做一次精确、细致的速写,他的诗因此也是极为具体与生活化的。
我们可以想象,也斯嚼着栗子,写下《苏黎世的栗子》,一首描述他在欧洲思乡的诗。诗开头,是他在“优雅拥挤的餐厅中”,吃了一盘用甜栗与酸菜调味的小鹿肉。行至结尾,他却又选择去单独买了包栗子,携带这仿佛有家乡风味的物什,继续浪游。
他在一座桥上停下来。桥下河水幽蓝、平静,仿佛一块琥珀,对面是钟楼的尖顶。白墙黑顶的德式民居,在清冷的空气中显得像一张火车时刻表一般精确而淡漠。他就只是从沾着逐渐发冷的油的纸包中,取出一枚栗子,放在石质桥栏上,也放在他相片的最下方。尽管他此刻必定是在眺望远处的他乡,视线却也总要经过这枚栗子,栗子的阴影在渐暗的天空下不断拖长如回声。他凝视这一枚栗子,就像凝视他的故乡。
作为非生于斯却长于斯的香港人,他不单用他的诗歌语言处理香港的本土经验,也以这本土为根系,让他的诗行在普世的阳光下枝繁叶茂。
他还是位极为早慧的作家,20多岁便在报纸上拥有了自己的专栏。他作为作家的早期阶段,贯穿1960年代末的香港。而当我们透过文字照见他最初的起点,他人生画卷中的第一笔浓墨便在此舒展开来。
在苦岁中生长
人们常认为,诗人是过分敏感的。尽管当我们在杂志上遇到成名后的也斯时,几乎每一张照片上,他都戴着他标志性的灰色画家帽,方形框架眼镜,也露齿笑着,毫不拘束。我们也能看到他少年时的照片:抿着厚厚的嘴唇,头发一丝不苟地绑在发胶里,着西服,正襟危坐。
拍下这张照片时是1964年,也斯15岁,已在《中国学生周报》发表过一些诗作,也度过了他最艰辛的童年。
1949年,也斯在广东新会出生。翌年,父母便带着他一起去香港讨生活。也斯4岁时,父亲去世,这成为他终身的隐痛,此后他一直忌讳别人谈论自己的父亲。
在香港最初那几年,他和母亲及外祖父在香港仔黄竹坑生活。该地位于港岛南部,1950年代时尚未开发,却是香港岛上少见的平原,故一直扮演着港岛农业基地的角色。
清代黄竹坑即有被称为“香港围”的村落,这一村落也是“香港”这一名字的来源之一。后随着人口增长,香港围又分出“旧围”、“新围”两村,在黄竹坑平原种稻米、芋头、红薯,养牲畜与家禽。但1930年代黄竹坑因有疟疾肆虐,政府下令禁止“竖禾” (即种水稻),只有今日高华花园一带的农业生产仍得到保留。
也斯的外祖父,便在黄竹坑的一家农场务农。母亲一开始也在农场工作,后来则开始接一些手工活,例如穿胶花、粘火柴盒。1950至1970年代时,制造业曾是香港的龙头产业。不少工厂都会将生产工序外包给个人,以节约成本,类似浙江的家庭工场。前香港特首梁振英童年时,也曾帮母亲穿胶花补贴家用。
胶花,也就是人造花,亦可视作香港人“狮子山精神”的象征。李嘉诚从一间小小的胶花厂起家,成为首富。1972年时,在不计算童工的情况下,仍有13%的香港工人从事胶花行业。当时,香港是世界上最大的胶花产地。
在结束一天劳作后,也斯一家人便围在一起。母亲卸下她背来的胶花零件,有时边听收音机边在昏黄的灯光下做工,有时教也斯读她从内地带到香港的书。它们多半是古典文学,诸如《长恨歌》《琵琶行》《赤壁赋》《李陵答苏武书》之类。
农业生活有一种深沉而富诗意的疲倦感,但这种疲倦很少磨损人的精神,反而会让闲暇成为真正能为人掌握,而非为各类指南书宰割的时间。家中的男主人——也斯的外祖父是一个热爱诗词,擅写书法与对联的前现代知识分子,在闲时常和也斯讲起伦文叙的故事。
伦文叙是广府人,后迁居南海魁冈(今佛山市石湾镇黎涌村)。他是明朝弘治十二年(1499年)的状元,治家教子有方。正德十一年(1516年),其长子伦以谅获广东乡试第一名,即解元。第二年,次子伦以训又中会试第一名,即会元。一家父子连中三元,时人称之为“南海三伦”。在南海,这样的例子是极罕见的。
讲这些故事的外祖父,也许正是抱着某种“耕读传家”的朴素期望,希冀也斯透过升学,改善一家人寒微的现状。
1954年,他们迁至北角居住,从港岛南端来到最北端,也从农村生活切换到高密度的现代城市生活。也斯也因此在端正小学北角道分校就读,与后来的奇情小说家、《花花公子》中文版主编、《天龙八部》编剧沈西城成为同班同学。
北角是港岛较早开发的地区之一。在1974年的诗歌《北角汽车渡海码头》中,也斯如此描述此地:亲近海的肌肤,油污上有彩虹,高楼投影在上面,巍峨晃荡不定。
小学6年,他出没于唐楼内的狭小校舍与港岛各地,感受这城市的缓慢成型。1950年代,港九地区兴建的屋邨多为高层建筑,卖甘草橄榄的小贩常将橄榄直接掷向高层的买主,仿佛棒球投手般又高又准。买主在窗边等待,不必下楼,只要听那小小纸包落在地板上的一声脆响,交易便完成了。人们称这极具表演性的交易方式为“飞机榄”。
这是他对高密度都市生活的最初印象之一。多年后,也斯仍记得此情此景,在《现象香港》一诗中,他写道:“叫卖的人把飞机榄掷入后现代高楼。”
法国建筑设计师勒·柯布西耶说过:“住宅是生活的机器。”在现代建筑设计史上,这句话如此重要,以至身处其阴影下的我们,早已习惯它带给我们的晦暗。香港的公共屋邨设计亦受影响,变成了也斯笔下的“后现代高楼”。
但在旧长型屋邨庞大的外立面上,原来光洁、严肃的水泥墙,逐渐染上住户的个人色彩,他们向这逼仄的城市争抢空间。加上花盆、藤蔓、涂鸦、冷气机的锈水,生活的意象如同茧一样缓慢生成,并进入也斯的诗行。他是第一个写香港地景的诗人。
搬家时,家中的卷卷藏书从内地到香港,从黄竹坑到北角,尽管一路波折,也从未像其他物件般被遗弃掉。书籍对仍保有士大夫心态的前现代知识分子,譬如也斯的外祖父来说,就意味着一种打开未来生活的可能性。所以,尽管在香港的初期生活十分艰苦,他们依然可以有精神上的追求。
家中收藏的新文学作品,即成为小学时期也斯的精神食粮。他曾表示:“朱自清编的《新文学大系》诗歌卷是我的新诗启蒙。当时的香港旧书店老板还用速印机翻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诗集,我买过卞之琳、穆旦、李广田、王辛笛的诗集。”

也斯 (梁秉钧)
用阅读穿过光影的暗门
1960年9月,也斯入读巴富街官立中学(今何文田官立中学)。香港的中学分Band1至 Band3三级,今日的何文田官立中学大概属于Band2B-2A,是一间比较中庸的学校。1960年代时,香港以英文教育为主,中文中学较难升学,而该中学的教学语言却是中文。
关于这段经历,也斯在接受《晶报》访谈时说道:“香港的父母很爱把儿女送到英文中学,很少人念中文中学,我就很反叛。我中学就念的是中文中学,但是我很不满意。我的老师很古板的,每一句话都要用成语。”
虽然在课堂上,也斯无法学到他想学的,但他经常去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读书。1962年3月5日,大会堂公共图书馆在中环香港大会堂落成,这是香港在二战后兴建的首家公共图书馆。该馆占地3277平方米,现时按面积计,它是香港第6大图书馆。
2001年5月17日中央图书馆启用前,大会堂图书馆一直作为香港公共图书馆的总部存在。但1960年代建馆时,馆内仅有2万册藏书,不过这也挡不住香港市民阅读的热情。建馆仅一月有余,大会堂图书馆便签发了1万余张借书证,馆方只好规定每人每次只能外借1册图书。
也斯一家那时从北角迁居到了何文田,离中环仅半小时车程。自然,这1万余张借书证中也有1张属于他。他开始从大会堂图书馆有限的馆藏里淘金,借阅内地、台湾、俄罗斯、英美、欧陆的各种小说与诗歌。
除读书外,他亦关注文学杂志。1960年代,港台两地都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文学杂志。它们一般是由一些青年诗人、作家为纯粹文学的目的而创办,有强烈同仁色彩,而少商业与意识形态色彩。
如在台湾,有1954年洛夫、张默、痖弦于高雄左营军区创办的《创世纪》,1960年台湾大学英文系学生白先勇等人的《现代文学》。在香港,则有丁平与韦陀于1962年创办的《华侨文艺》,以及刘以鬯主编的《香港时报·浅水湾》。这些都是也斯中学前期的重要读物。
这几份报刊虽然归属地各不相同,彼此间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洛夫就经常为《华侨文艺》撰稿,韦陀的学生古兆申后来回忆道:“《华侨文艺》上有很多逃难到台湾的军中诗人的作品。”藏书家许定铭也提到,“由于(《华侨文艺》的)编者与台湾蓝星诗社创办人覃子豪深交,故此蓝星诸人大力供稿。”
这些刊物大都倾向于扶持年轻人的创作。丁平如此描述《华侨文艺》的选稿倾向:“我们每期都刊出三分之一名家的作品,其余的则拨给年轻新人,尽量给他们发表作品的机会。”彼时,散在城市各处的年轻人,因为文学聚拢在一起,如涓滴般汇聚成文社、诗社。他们泳在共读诗歌的优游岁月里,一同分享创作及投稿的经验。
1963年,也斯加入了“文秀文社”。这家文社由当时在皇仁书院读中学的胡国贤(笔名羁魂)于1961年创立。胡国贤是1946年生人,大也斯3岁,组织“文秀文社”时在《中国学生周报》《星岛日报》等报刊已多有作品发表。也斯或许曾在报上读到过文秀文社的作品,因为文社给《星岛日报·青年园地》的稿件,编辑都会尽量刊出。
“那时候,大家在创作路上尚处于摸索阶段,并没有强调什么门派。不过,从也斯翻译的作品看到,他中学时期已倾心西方文学,而我则较倾向古典。也斯很少在《星岛日报》发表作品,主要投稿给《中国学生周报》。当时,他应已醉心现代文学创作,但从不标榜。”胡国贤这样谈起中学时对也斯的印象。
也斯书桌上的读物越来越多了。穿梭在港九地区,从旧书摊寻找琳琅的文学刊物:《诗朵》《文艺新潮》《好望角》《人人文学》。

他也在摸索着写作,10月18日,气温下降,他披上外套去报摊找那份《中国学生周报》。这是他最初发表的诗,名为《致自慰的落第者》。他把这一页剪下来保存。但由蓝色圆珠笔的手稿转成这棱角分明的铅字,他总觉得奇怪,仿佛每个字都摇摇欲坠。
这并非让人满意的创作,可其他的诗又如何?“尽是红叶和夕阳,要不就是老气横秋地把文句扭来扭去。”他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于是我又翻回去看(《周报》的)电影版,心里想诗应该写得像电影那么好看才对。”
也斯的诗常用所谓“楼梯体”来制造蒙太奇效果,也追求用词与词的跳接带出一种镜头感。这些技巧,得益于他早年大量观看法国电影的经验。
为了能看到更多电影,15岁的也斯报名加入了香港规模最大的电影协会Studio One。当时,法国文化协会每年也会出借最新的法国电影给会员。也斯被这一优惠吸引,虽然拮据,仍用稿费缴会费,积极跟进新浪潮电影的动态。
阿兰·雷奈的电影《广岛之恋》与《去年在马伦巴》,给也斯带来巨大的美学冲击。他回忆“当时已经读了不少传统和现代小说”,但《广岛之恋》是他“第一次从银幕上感觉到视觉空间发挥不顺应时序的叙事力量”。
而他第一次从法国文化协会借到的《去年在马伦巴》,是纯法语原版,没有中文抑或英文字幕。他还没开始学法语,完全看不懂电影的所指,却“被它冷冽的诗意和优美视象吸引过去”。透过这些电影,他与法语及法国新小说结下不解之缘。玛格丽特·杜拉斯与罗伯·格里耶的创作,启发他去写那些更克制、更先锋的文字。
1966年,他入读浸会学院(今香港浸会大学)英文系时,便开始修读法语。他的法语老师由社会系的一名教授兼任,他来自湖南,无论普通话、粤语,还是法语,都夹杂浓浓乡音。
不过,也斯学法语的目的是为了看法国文学与电影。相对枯燥的日常会语、词性、词格及文法变化,令他十分头疼,应付考试更是让他痛苦。2004年应《黄巴士》之邀,回忆这段写作的前史时,也斯表示他“对学习语文一向没有很大兴趣”,而只是喜欢带上一本厚厚的字典去读法语诗,抑或透过英译本或英法对照本,阅读罗伯·格里耶、杜拉斯及贝克特等人的作品。
年轻的专栏作家
香港报纸的尺寸往往比内地大一倍有余,一个版面上能塞下三四个专栏。也斯是在1967年,即他大二时,开始在报纸上有这一小块园地的。当时他在《星岛日报》有一个《大学文艺》栏目,隔年又在《香港时报》撰写《文艺断想》专栏。在这之前,他只发表过零星的一些诗歌。
这年7月25日是值得纪念的。这天《星岛日报》的《大学文艺》栏目,刊登了也斯的两篇文章,《电影漫谈》《略谈当前文艺》。
后一篇文章中,这位18岁的青年作者,毫不留情地批评香港文坛“高谈阔论的人太多”。这些人对西方现代文学诸如意识流小说,只有东拼西凑的论述,时效性亦不足,因为“台湾的《现代文学》早为吴尔芙、乔哀思出过专辑,最近更把《都柏林人》全译过来,并加以分析评论了”。
写专栏时,他也许会想起与外祖父在黄竹坑务农的日子,就像谢默斯·希尼在一首诗里将自己用笔进行的挖掘与父辈在田野中的挖掘联系在一起。昔日的专栏只依作家的个性,不必太注重商业性,也少匠气,多是平易近人的语调,既能与读者沟通,亦能保持自己文字的章法。
作者想在专栏里种下什么种子,收获怎样的果实,都是自由的。1998年,在为《香港文学》写的一篇文章中,也斯回忆道:“6、70年代本身没有什么偏见,既无学院派执着一种理论否定他人,亦无人打着流行的旗号否定严肃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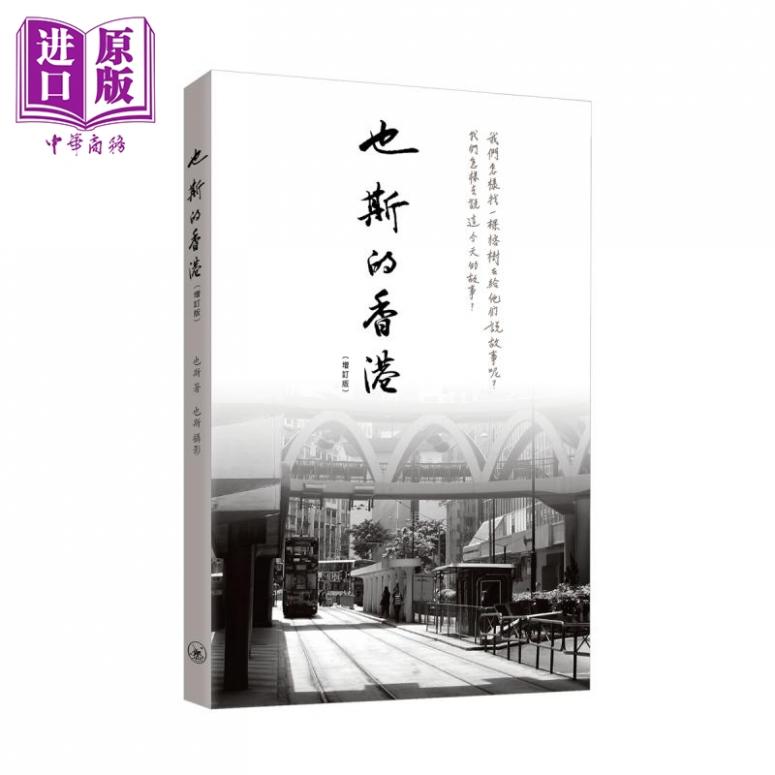
刘以鬯的意识流小说《酒徒》,在《星岛晚报》上发布时,被诸多言情小说与政论包围,与新派武侠小说连载时别无二致。1960年代末,《纯文学》杂志亦曾采访过金庸及写《经纪日记》的三苏(又名高雄、经纪拉)。
也斯的专栏既有诗一般的文字,也有精辟的评述与动情的自白。它们记录着他学习、译介法国新小说、美国地下文学等文学前沿的过程,同时亦承载他的欢欣与苦闷。
在动荡不宁、充满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一个年轻人希冀在文艺中找到自己的立身之本,就必然与世俗观念冲突。1968年11月的某个深夜,他在灯下漫笔写他《文艺断想》的专栏。沐着月光,发白的街道上狗吠声连成一片,电车经过,在远处停下,“叮”的一声仿佛壶中的水预感到沸腾。他写道:“在一些人的笔下,年轻人写诗的就一定是头发肮脏,看电影的就一定是逃避现实,画画的就一定是寄生虫——一个又一个的模型,这样的骂法也未免太缺乏想像力了。”
究竟自己算不算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进入1960年代末,也斯很困惑,他不认为自己与那些在报纸上胡写一气的人是一路。对艾略特式的书斋诗,他只觉得隔膜。“文秀”的胡国贤后来去了香港大学中文系,他与许定铭等人办“蓝马文社”时,也斯没有被邀请。大抵他们也写后来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诗,而不看好也斯的诗观。
余光中来了。那是1969年2月28日,星期五,地点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虽然也斯并不喜欢他的诗风,却也去现场听了他的朗诵,预备在专栏中报道此事。
一进会场,他就看见崇基的学生举着小旗,上书“欢迎中国的缪司(内地翻译成缪斯,港台是缪司)余光中”。他第一次见到诗人在香港竟也能如此受欢迎。比起如护卫般在余光中左右的“香港文人”,余的外貌“更谦虚,也更有学者的风度”,“听他在会上幽默而无伤大雅的谈吐,锋利而不令人难堪的答问,倒觉得他是一位比他的作品更吸引人的人物”。或许正是这次经历启发了也斯,让他终身都保持着与公众、社会及时代对话的热情。
时间终于来到毕业的那天。大学四年,他写作、翻译的诗文塞满了抽屉。他常把自己的作品剪下,用铅笔订正一些语句,方便日后翻阅。这是1970年末的一天,他在码头边等船载他去离岛上班,他在那里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船轻轻啮过码头,经过洋流时,他望向身后的港岛与九龙,他突然想起,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首诗切实地写过它们,写它们的街道,写街道上人们的生活。
而这,正是1970年代的诗人也斯要做的工作。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