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三国与文学三国:历史折叠之处的情感与想象
公元220年,魏王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登坛称帝,立国号为“魏”,史称“曹魏”,改元“黄初”,定都洛阳——大魏立国之日,即是东汉消亡之时,时为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历时一百九十五年的东汉王朝寿终正寝。
次年,刘备称帝,立国号为“汉”,史称“蜀汉”,年号“章武”。刘备登基之日,祭告天地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
东汉消亡于建安二十五年,并无二十六年一说。刘备之所以使用这个不存在的年号祭告天地,自然是不能以曹魏的年号为标识,只好继续沿用已经消亡的东汉的年号,而这个并不存在的建安二十六年,既成为刘备“祚于汉家”的时间节点,亦是向世人昭告,蜀汉政权延续汉祚的合法性。
李庆西先生将他的新著取名为《建安二十六年》,同样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刘备以“逆取”而谋事,借“承祧”而立国,他的光复汉业的诉求,无疑是用以凝聚部众的路线和纲领,而蜀汉立国的正义叙事,首先即源于这种向心力。
作为一部以三国魏晋为话题的学术随笔著作,李先生将史实中的三国魏晋与文学叙事中的三国魏晋相互对照,据以叙事角度比较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异同,对二者加以辨析和领会,从中发现历史折叠之处的有趣话题。
这些话题或许并不涉及宏大叙事,却能够触及历史的幽微细节,而这些细节则构成了历史的另一种面向,既能够让人脑洞大开,同时又能够从史家和小说家不同的叙事策略中,领会到历史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三国魏晋时期原本是一个短促的历史过程,但纵观这一历史过程,不仅“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律廓然而现,连同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群雄竞起、攻战杀伐、同室操戈、鸠占鹊巢,乃至钩心斗角、宫廷内斗也并不缺少,为李先生的研究提供了足够多的素材。
李先生的新著主要探讨的是三国建政的政治伦理和历史机缘,尤其是站在蜀汉的角度,去观照和解读三国各自不同的建政叙事——诸如三国不同的国家构想和立国理念各是什么?从法理上讲,哪个国家最具有执政的合法性?三国之中实力最为弱小的蜀汉,何以会成为文学叙事的主体?又如何被注入了担当正义的精神内涵?
其中,史家的叙事注重事实,常常将王朝更替视作历史演化的必然;小说家的叙事注重情怀,实际上却折射出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
正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陈寿在《三国志》中的叙事法则明明是以曹魏为正统,一旦到了小说和戏曲里,却偏偏变成了蜀汉一家的光荣叙事,个中的反转不仅仅取决于文学手段,从中亦不难体会到,沉淀于民俗风习之中的历史感受同样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将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参稽互证,本来并不是什么新方法,但李先生的新著却别出机杼,以传统史学的严密考证与富于幽默感的文字相互结合,既颇具抽丝剥茧、指点迷津的意趣,且以之“倾聆史官和文人的兴废之叹”,从不同的声音里解读出不同的思维或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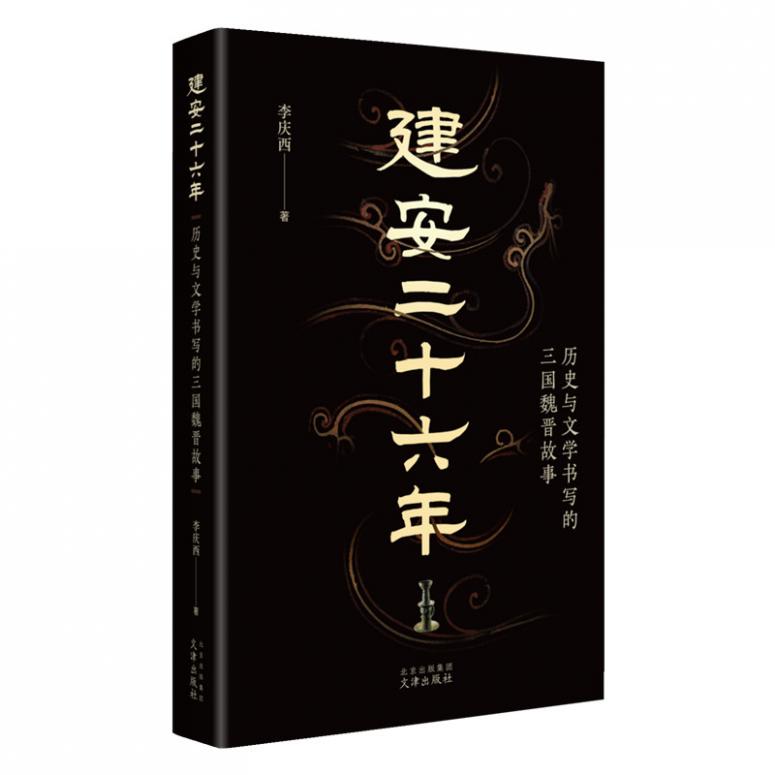
三国建政:各自不同的国家构想和话语体系
按照传统的帝王纪年,三国的历史应该从曹魏代汉开始算起,终结于吴国的灭亡,亦即从公元220年到280年,此间六十年的时间,便囊括了三国的全部历史。然而,至曹魏延熙二年(265),司马炎已然以晋代魏,此时的三国只剩下东吴尚在苟延残喘,三国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亦不妨视作下一个朝代的肇始,这样看来,三国从头到尾只有四十五年(220—265)。
但不管是六十年,还是四十五年,魏蜀吴从各自建国之日起,便开始构建各自不同的国家构想和话语内容,以之赋予政权的合法性,并在彼此之间的攻战杀伐中占有主动权,这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首先看曹魏,曹丕践祚并不是直接废掉傀儡皇帝,而是不厌其烦地履行了一套禅让程序:汉献帝本人宣布退位,并将皇帝之位“禅让”给曹丕,曹丕则故作姿态,一再推辞,最终在文武百官的劝进之下才“答允”接受。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两种形式,曹魏以禅让的方式取得政权,承继汉朝之大统,已经在法理上获得了先机,曹丕之所以履行这套繁琐的禅让程序,目的无非是为了昭告天下,他接受汉献帝的禅让,乃是民心所向、天经地义的事情。
再看蜀汉。刘备起兵之初,即以“匡扶汉室”为名义招徕人心,汉室宗亲的身份,亦即所谓的“大汉皇叔”,无疑是他获得话语权的最大资本,刘备之所以由弱小而渐强大,大概率得益于此。曹魏代汉的第二年,刘备即以血脉之亲“祚于汉家”,他不仅在登基文告中宣示其“率土式望,在备一人”的嗣国资格,而且还直指曹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乃是不折不扣的篡逆之辈。
正是因为这样,尽管蜀汉朝廷偏安西南一隅,但刘备君臣却始终抱有大汉王朝的帝国心态,一方面以遥领的方式主张其领土主权,另一方面以“汉贼不两立”为意旨,执意伐魏——对于蜀汉来说,军事上的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伐魏释放出的政治诉求;疆土是否得到拓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断强化其政治正义性,因为这意味着蜀汉立国的根本。
与曹丕和刘备相比,孙权既不具备禅让的优势,又不具有汉室宗亲的身份,所以对于何时称帝,孙权一直犹疑不定。直至曹丕称帝的第三年,孙权才以“黄武”建元,迈出了试探性的第一步,而真正称帝,则是曹魏立国九年之后的公元229年了。
与魏蜀两国截然不同,东吴完全抛开了两国建政的路数,将立国的合法性归结为天命——所谓“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意思是只有东吴当得起“神飨”二字,孙权称帝乃是真正的“奉天承运”,根本不需要有别的理由了。
正史中的三国叙事与文学中的三国叙事
如上所述,三国建政伊始,即首先确立了各自不同的话语体系,以证实自己立国的合法性。然而,在文学的叙事中,史家奉曹魏为正统,并以之书写三国历史演进的叙事却遭到了颠覆,民间显然不认同史家成王败寇的历史观,而是以儒家的道德纲常伦理为归依,塑造自己理想的人物形象。
他们信奉非白即黑的是非标准,将历史进展的过程简化为好人与坏人斗法的过程,从而认准了刘备承祧汉室的合法性,以“尊刘抑曹”作为小说或者戏曲创作的基调,尽管魏蜀吴奉行的都是适者生存的机会主义战略,却被他们分出了其间的高下,目的就是让受众明辨蕴含于其中的春秋大义。
事实上,刘备的立国之由,可以上溯到他三顾茅庐时,接受诸葛亮“隆中对”的宏大意旨。赤壁之战结束后,刘备虽然分得荆州之一部,却立足未稳,且时时处于曹魏与东吴的挤压之中,他要有所进取,就必须争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尽快实现“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而地处西南的益州,即成为魏蜀吴三方均欲争夺的目标。
刘备得到益州的过程虽然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却无可避免地带有一丝同室操戈、鸠占鹊巢的色彩,文学创作欲将其演绎为一种正义的叙事,就必须强调其“匡扶汉室”的终极伦理,以目标之崇高掩盖其手段之卑劣。而刘备采纳庞统的建议,除掉刘璋手下部将杨怀和高沛也是如此,《三国演义》将这场主动的杀戮变为被动的杀戮,演绎成一种“你不仁,我才不义”的叙事路径,从而维护了刘备的仁厚形象。
对于诸葛亮的塑造,小说和戏曲的叙事也基本上沿袭了同样的套路——诸葛亮既是忠诚与智慧的化身,而他带领蜀汉以弱击强,却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局,又带有浓浓的传奇性和悲剧色彩。
我们从中看到的无疑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几近完美的人物形象,甚至连鲁迅先生也认为,《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虽然均有过分拔高之嫌,却契合受众心理,很容易让人产生某种代入感。
这也再次印证了李先生的论断——文学创作中的三国叙事,反映出的是民众眼中的三国是怎样的,民众希望的三国是怎样的。小说家和戏曲家显然更懂得民众心理,他们的创作所透露出的,其实是主流的政治伦理和民众文化心理之间的差异与衍变。
民间语汇中的三国叙事
三国叙事同时又衍生出许多民谚、俗语和歇后语,这些跟三国相关的泛民间语汇,有些出自各类体裁的三国文本,有些则是世俗生活中的话语生成。前者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刘备摔孩子”“周瑜打黄盖”“赔了夫人又折兵”“大意失荆州”之类,大抵都脱胎于三国故事;后者像“事后诸葛亮”“关公门前耍大刀”,乃至“张飞绣花——粗中有细”“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等,却并非完全出自三国故事。
另外,还有诸多由三国典故衍生出来的成语,诸如关于吕布的“三姓家奴”,关于关羽的“单刀赴会”“刮骨疗伤”,关于诸葛亮的“舌战群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中无不蕴含着普通大众对三国人物的喜恶与爱憎。
由这些流传甚广的泛民间语汇,可以看出三国叙事在公共传播层面上的深远影响。民间话语显然更能够证明三国故事和人物在一般民众心目中的分量,折射出他们的是非观念和价值取舍。
比如,“天不灭曹”是恶人难除的譬喻;“韬晦之计”表现出刘备处于危难之际的生存策略;“锦囊妙计”是对诸葛亮卓越智慧的赞美;“乐不思蜀”透露出的则是对蜀汉后继无人的深深失望。民间语汇中的三国叙事或许有悖于史家叙事的初衷,甚或与史家叙事相抵牾,却更为民间大众喜闻乐见,它们独立于正史之外,构成了一种另类的文化存在。
诚如李先生所言,《三国演义》之所以改写陈寿的述史立场,除了代入某种情感因素之外,同时亦是从陈寿的记述中发现了理想的组织形式和礼制范式。而这种理想的组织形式和礼制范式,才是世俗大众真正需要的东西。
所以,李先生最终这样总结道:“如果不是专门做历史研究,这里不需要你考证什么历史真相。其实,真相是一种讲述历史的话语方式。三国乃或魏晋的故事告诉你,文学的叙史方式所诉说的实是国人的一种心灵史”。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