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死后的生日来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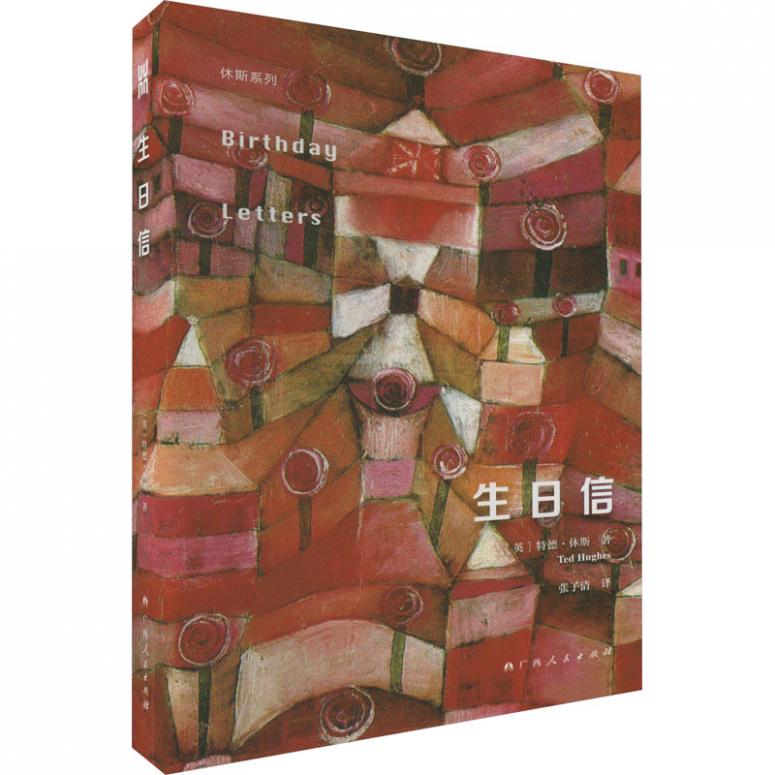
关于二十世纪美国和世界文坛中,普利策诗歌奖获奖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与英国桂冠诗人泰德·休斯的恩怨纠葛,爱恨情仇,早已成为一桩众所周知的公案。
其中细节,譬如关于二人如何在一次《圣伯托弗评论》(St.Botolph’s Review)杂志的酒会上一见钟情,从而双双坠入爱河;后来二人又如何因为休斯的出轨而分道扬镳,普拉斯又是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情形之下在1963年2月与休斯办理离婚事务期间突然决定开煤气自毁;以及,休斯后来的妻子诗人阿霞·维韦尔(Assia Wevill)如何在婚姻中神秘地走向了与普拉斯同样的命运……这些文坛公案,已经有众多文章和传记、八卦不断重复描写。
最新再版的《生日信》(Birthday Letters)一书,进入的则是休斯和普拉斯的生活和诗歌世界。本书的第一版,名字叫做《生日信札》(2001年,译林出版社),据说已经脱销并炒到了很高的价格。最新的《生日信》将旧版做了重新修订,译者张子清教授又补充了前言和后记。出版方表示,每一首诗几乎都做了新的、仔细、认真的修订。
用你的方式来重新思考我们的关系
《生日信》中的88首诗歌,是休斯写给普拉斯,更是写给自己的一封长信。诗集中,休斯一反常态,打破自己惯常写作的风格特征,转而采用普拉斯的方式(也就是普拉斯所归属的自白派的方式)来重新回顾自己与普拉斯的关系。这是一种企图重新认识那个个性极度复杂的神秘女诗人普拉斯的唯一方式。
自白派是二十世纪美国诗歌一种重要流派。该流派采用一种自白的方式来写作诗歌,以罗伯特·洛威尔为先导,开创了一种以直接告白和心灵倾诉的方式写诗的方法。普拉斯本人则在这种方式中取得了巨大的、无可磨灭的诗歌成就。
而休斯自身的写作风格是克制、冷峻的,可以说与普拉斯的思维模式和精神构型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但是在《生日信》这本诗集中,休斯采用“自白”写法,一方面是向普拉斯这个同行致敬,同时,也是对于普拉斯精神内部构型的一次尝试性探测。
如果说美国诗歌有什么流派的诗人的个性是最为复杂、难懂的话,自白派的诗人可以算作是在精神层面探测最为深入、彻底的。同时,这一流派的诗人罗伯特·洛威尔、约翰·贝里曼、安·塞克斯顿等由于天然的宿命(他们几乎都伴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疾病的困扰)使得他们的诗歌情感强度巨大,对于人的精神危机、精神与自我的剖析也是最为剧烈的。
这种写法一方面是由于宿命,另一方面,本身也加剧了这些艺术家精神走向崩溃的可能性。因为这一写法对于人、人的精神、人的关系都进行了剧烈的解构性摧毁和重建。这种勇毅的果敢,并不是人人都能够胜任的。而普拉斯无疑是这一流派的当之无愧的女王。她的迷人的个性,她的诗歌当中的复杂性,她的尖利,她的彻底的摧毁性,都让人印象深刻,过目不忘。
《生日信》当中的每一首诗歌都可以看成是活着的休斯企图与死去的普拉斯跨越生死两界的对话。这些诗歌的写作历时二十多年,原本休斯只是为了“去除胸中的某些郁积……”并不是打算发表。后来,随着越写越多,诗歌在数量上达到了一定的指标,同时在诗艺上也达到了休斯的某种认可,于是他同意出版。
但是,这本书的出版引起的轩然大波,并不是休斯可以预见到的,诗集的出版激起了女权主义者广泛的声讨,同时也重燃了当年普拉斯自杀所带来的那种极度浓烈的社会回应。
诗歌之外的普拉斯和休斯
作为《生日信》中诗歌所写的主人公,普拉斯无疑是一个诗歌天才。在后人看来,她接近和加入自白派,用自白派的方式写诗,完全是一种命中注定。
普拉斯拥有不幸的童年,父亲的早亡在她心中刻下了对神的愤怒,父亲的死对普拉斯打击巨大。在诗中,普拉斯甚至表示过,从此以后不再与上帝对话。由此可见普拉斯性情当中的叛逆与倔强,也可以瞥见她的高傲与盲目。
从少女时期开始,普拉斯就经历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她几次试图自杀,但是都未能成功。与休斯结合以后,普拉斯接连孕育了两个儿女,这让她沦为家庭妇女,而诗歌是她唯一的抵抗男权规定命运的武器。
在诗中,普拉斯无数次描写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那种不适应,她不断倾诉、拆解着自己,也不断与外在世界展开对话(虽然绝大多数是以分裂和对抗的姿态),然而对于这些,休斯真的能够感同身受吗?在那个将女性圈囿于家庭生活被视为理所应当的年代,普拉斯的命运,确确实实是当时主流的美国女性的普遍命运选择。如果大家读过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或许会对这一处境有更深的了解。
然而,对于休斯而言,普拉斯当时的心理境遇并不一定能够被他捕捉到。或许二人相互之间的鸿沟深不可测,毕竟,休斯面对的是一个内心世界极度复杂、充满张力,颇有一些神经质的天才女诗人!因此可以说,普拉斯和休斯几乎是一对注定要走向分离的夫妻。
同时,如果对普拉斯和休斯的诗歌写作稍有洞察,也不难发现两人的性情天壤之别,冰块与烈火,熔岩与礁石,差别巨大。虽然二人相识相爱如电光火石,但是,真正的婚姻当中却难以平衡彼此精神内部朝着相反运动的洪流。
普拉斯死后,激起了女权主义集体的同情,一时间她被奉为女权主义的精神领袖,而休斯也一直面临着各种形式的攻击与嘲讽。更有人喊出“杀人犯”来指责休斯,甚至在他住过的房间里焚烧了他的诗稿作为抗议(见译者序)。可见,当时普拉斯粉丝对于休斯的愤怒。
可以说,自普拉斯死后,休斯一直生活在她的阴影中,面对世人的指责,休斯一直保持沉默。对于二人的纷争孰是孰非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普拉斯的个性导致了二人的悲剧。他们说普拉斯是一个贪婪、挑衅、自私的魔鬼。但是也有人说普拉斯讨人喜欢、慷慨、可爱。而对于休斯,有人说他自负、暴躁,吹毛求疵;而另一个版本是他长期遭受普拉斯的压抑而产生精神痛苦(斯蒂芬·格洛弗)。
事实究竟如何,我想即使是二人身边亲近的朋友也很难道出一个所以然来。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生日信》当中休斯的笔触来窥知一二。虽然,休斯的写作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中立(多多少少有为自己洗白的倾向),但是,对于热爱普拉斯和休斯的人来说,这几乎是唯一的可以依凭的根据了。
以诗歌记录两人的另一面
《生日信》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休斯与普拉斯的相识、相爱、结合到分开的整个过程。诗集的第一首诗歌《富布莱特奖学金学生》一诗,就描写了休斯观看一张普拉斯获得奖学金时的合影照片的感受。当时休斯25岁,他以清快的笔触描写了照片中的普拉斯带给他的那种生动的印象。
而在《女像柱》中,休斯谈了他对普拉斯诗歌的感受:单薄、脆弱,感情冷淡。可见休斯对于普拉斯的诗歌缺乏理解。这或许是他们关系出现问题的一个潜在隐患。
后面,我们会越来越发现,休斯对于普拉斯的不理解,或者说迷惑。例如《射击》一诗中,休斯写道:“你通过我而变得清白——终于把你自己埋在这恶煞似的神心里。”在另外的一首名为《机器》的诗中,他写道:“当你父母的古怪面具隐现。”另外一首《像基督那样》的诗中,写道:“虽然你漫步在对你父亲的爱里,/虽然你盯着你形同陌生人的母亲。”可见,普拉斯与母亲关系的糟糕和疏远。另外,也可以瞥见,休斯对于普拉斯的爱。
在《杨柳街九号》的诗中,休斯写道:“我难以理解处在恐惧的忐忑不安中的/你。我张开黑色翅膀包住你。”不难看出休斯对于普拉斯的爱当中混杂着猜不透普拉斯的一种视角。而在同一首诗里面,他也写道:“你的新诗句/折磨着你,一只精确记录你/精神的残酷计算机,每天/更新——每个字母都是针。”从这些句子中又可以看出休斯对于普拉斯写作方式的警惕和心疼,由此,我们也能够瞥见,普拉斯用生命燃烧自己锻造诗句的决心。
同样是在这首诗里,休斯还感叹道:“在你眼里,我像是你玻璃钟形罩里的小矮人。”不禁令人惊讶,向来给人印象果决的休斯竟然在普拉斯的强力之下感觉到自己的无力与渺小。这是一种极端复杂的境地,可能只有当事人能够了解其中的滋味。在《生日信》中的休斯,是一个近乎木讷的诗人、学者、父亲、丈夫的形象。
总的说来,在《生日信》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另外一个普拉斯和未经发现的休斯。这些发现未免让热爱他们诗歌艺术的我们感觉到心弦震颤。
休斯的诗歌成就
《生日信》虽然充满了自白和传记色彩,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这是一部泰德·休斯的个人诗集。虽然我们前文已经强调过了,这部诗集是休斯以普拉斯的自白派写法来写的,可是,如果对普拉斯的诗歌写作成就有整体深入的把握,我们就不难发现,实际上,休斯只是在表面意义上仿效着普拉斯。
自白和叙事只是外壳,普拉斯所代表的自白派实际上真正的源流是精神分析的嫡传。他们表面看来运用的是叙事的手法,写的是一种叙事诗歌,实际上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他们自己内心,或者说是他们的精神状况,说大一点是人类的精神的深度状况。
在这个基础上,普拉斯的诗歌倾向于一种渎神的反叛性,一种深刻的自我解剖,以及精神上的赤裸。这一点,虽然,休斯在说到《生日信》的出版时说:“事实上,我是六月前才决定出版的……我试图所做的一切是脱光衣服,成为赤子,跋涉于其中。”但是,无论休斯多么希望“赤裸”,都不如他的枕边人普拉斯“赤裸”。
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休斯整本诗集的写作成就。这部诗集虽然不是休斯风格的代表,也完全不能代表休斯的写作成就,但是在这部诗集当中,休斯体现出了一种与他以往的精确、幽微、克制、神秘的诗歌风格完全不同的风格。整部诗集松弛自然娓娓道来,字里行间不乏对于普拉斯的爱,“我辞掉了工作,/挥霍我所有的积蓄,/苦苦追求的是你。”(《忠实》)。
实际上,在整本诗集中,休斯也做到了“赤裸”,但是,他终究不是一个摧毁自己的托尔斯泰式的忏悔者,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能够真实地完全地面对自己曾经的罪责与过错,都是一件太难的事。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