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世界的魅惑与欢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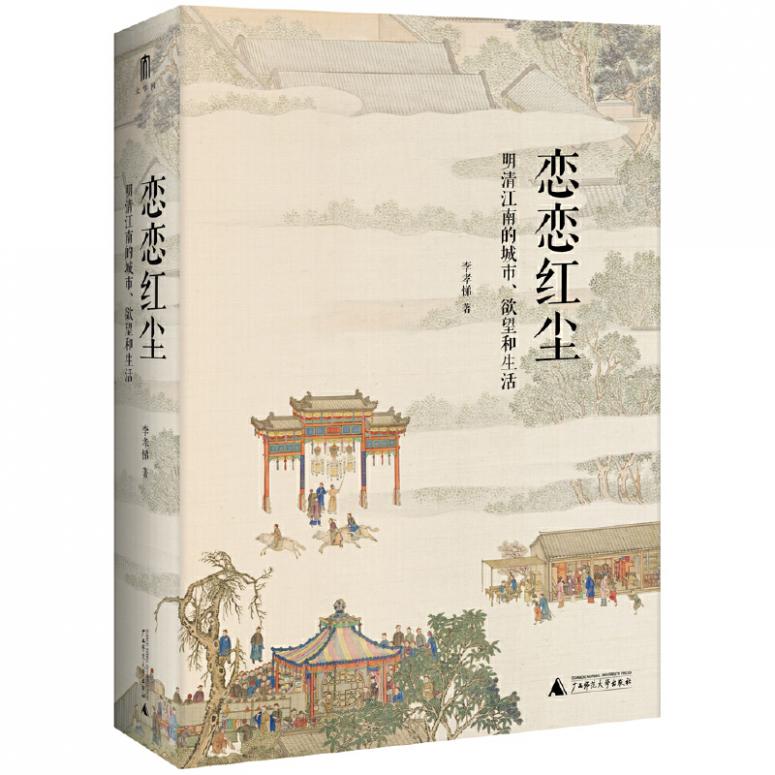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孔尚任的传奇戏曲《桃花扇》一纸风行,已经渐渐湮没的南明历史再度进入时人的视野;侯方域和李香君的香艳故事,也再度成为前朝遗老遗少茶前饭后的谈资——秦淮风月,名士风流,楼台烟水,新声明月,前朝的风雅遗韵又一次唤起了遗老遗少们的禾黍之悲,令他们感慨系之,唏嘘不已。
公元十六世纪是明代的中后期。自这一时期开始,以克俭克勤、质朴务实为治国理念的大明王朝正在悄悄地发生着一些潜变:原本循规蹈矩的士商阶层纷纷抛弃了他们一直恪守的生活理念,转而追求一种纵情声色、醉心诗酒的逸乐生活——这自然是与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分不开的。
逸乐,作为一种价值观念,首先在一般士大夫和商人阶层蔓延开来,渐而在城市市民之间普及,终于蔚然成风,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历史学家李孝悌先生的《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一书,即是以逸乐、情欲和城市为主题,聚焦明清文人的心理和生活世界,进而以丰富多彩的细节还原了它们的真实面貌。
在主流历史叙事之外寻找日常琐碎
在主流历史的叙述中,我们往往只能看到一般历史人物正襟危坐的一面,盖因这种叙述更注重从思想史、学术史和政治史的角度探讨历史人物,却将历史人物日常生活的细节置之不顾。这种叙述虽然也塑造了或“高大上”、或“矮矬俗”的人物形象,但这种人物形象却趋于扁平化,缺少温暖的人性色彩和人情味,所造成的也只是一种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效果,忽视了个体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而在《恋恋红尘》一书中,李孝悌关注的则是历史人物的另一面: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交游娱乐,他们的审美爱好,他们的爱恨情仇……从生活史和文化史的角度聚焦他们的私人生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性情毕现的历史人物;在官方的政治秩序和儒家的价值规范之外探讨他们的心灵世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许许多多异质的存在。
诚如李孝悌所说的那样:“缺少了城市、园林、山水,缺少了狂乱的宗教想象和诗酒流连,我们对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建构,势必丧失了原有的血脉精髓和声音色彩。”李先生写作《恋恋红尘》的目的,即是以由小见大的种种细节,去尽力沟通与弥合明清士大夫个人化的血脉精髓,还原明清社会日常生活的声音色彩——
他以侯方域、冒辟疆、王士禛、袁枚、郑板桥等人为代表人物,巨细靡遗地描写他们儒雅风流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世界;他以十七至十九世纪的南京、扬州、上海等城市为主要场景,不厌其详地描述这些城市的文化生活和休闲娱乐。
这些城市既为明清士大夫的个人品味和精致生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舞台,从中却也不难看出,时代变迁之于城市转型的潜移默化:戏曲、情歌、广告、画报……恰是这些琐屑之物,见证了其间的微妙之处。
是以,李先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或理学,虽然是形塑明清士大夫的价值观和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却不是唯一的因素;如果将那些足以影响城市转型的琐屑之物放在生态史和制度史的脉络下去考察,不仅能够使原来看似干涩的典章制度产生新的意涵,同时也可以让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琐屑之物承载更严肃的使命。
总之,欲考察明清社会的人物和城市,仅仅关注主流历史的叙述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主流历史的叙述之外,发掘出更多的非主流、暗流、潜流,乃至逆流,才能够加深我们对明清人物的理解,把握住明清社会的本质特征。
《桃花扇》:一种有别于正史的历史记忆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李洁非教授曾经把十七世纪上半叶的南京称作一座“非典型”的城市。彼时的南京有两个最鲜明的关键词:一个是“革命”,一个是“爱情”。而彼时的秦淮河畔,则让人不自觉地想起世纪末的巴黎塞纳河左岸:同样沉溺在一种张扬不羁、纵情声色的情绪中;同样充斥着从精神到肉体的自我放逐。
在频繁流连于秦淮河畔、穿梭在花柳丛中的明末才子中,侯方域和冒辟疆无疑都是出镜率极高的人物。对于南京,他们都曾见证了“大江南北,名士才人,悉萃于此”的盛况,也都曾感受过南京鼎盛时期奢华靡丽的生活。不同的是,侯方域英年早逝,他只看到易代之际逸乐生活骤然断裂的刻痕;冒辟疆则得享高寿,易代之后,他移居家乡如皋的水绘园中,将南京的逸乐生活加以复制,饮酒高会,诗酒逍遥,重现昔日金陵的繁华岁月。
在很多人看来,明末南京的风流笙歌,在臻于极致之际骤然断裂,一个逸乐的时代就此落幕,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相对严苛的时期。对于新兴的清朝来说,它不仅带来了一整套新的政治秩序,同时也试图解决前朝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清政府伊始就有强化道德的保守主义倾向,固然是事实,然而,如果就此认为风流笙歌的逸乐生活,已经从士大夫的个人世界中完全清除,却也带有一些想当然的成分。
事实上,任何社会都不是铁板一块,也都存在着一些与主流并行的暗流,这既与皇权的统治能力有关,更涉及到世俗生活自身的逻辑。尽管主流社会设置了许多禁锢和限制,但人性本然,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化,依然是世俗人生最大的追求。
或许可以将《桃花扇》当作明末士人逸乐生活的一个样本,它不仅书写了一个朝代、一座城市和一条河流的历史,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有别于正史的历史记忆,让后人得以进入明末南京特有的城市氛围。而冒辟疆在水绘园中的风流笙歌,则让我们看到了明末逸乐生活的某种延续,正是冒辟疆的个人选择让我们相信,在十七至十八世纪的皇权和礼教论述之外,的确还存在着一个政治势力和主流学术无法扼杀的个人世界。这个世界处于时代的缝隙之中,虽然并不强大,却为后来者点燃起一束希望之光。
王士禛和袁枚的幸福生活
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仅二十七岁的新科进士王士禛出任扬州推官,正式开启了他在扬州做官的生涯。彼时的扬州刚刚经过易代的创痛,正在慢慢的复苏之中,但尽管如此,这座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帝国都市依然焕发出迷人的魅力,令王士禛沉吟流连,陶醉其中。
在扬州为官的五年间,王士禛除了每天应对繁忙的公务,就是“访三山之名胜,吊六代之故墟”,既“顾贻上方用政事自奋,而又能饰以风雅,有登临啸歌之乐”。正是在案牍劳形之余,王士禛居然写下了数百首诗篇,可谓数量惊人,与之同时,他还多次发起诸如红桥修禊之类的文人雅集,与文人旧交宴饮狂欢,打成一片。王士禛在官员与诗人两种角色之间转换,他既是一名推官,又是一个能够打破对立、超越藩篱与疆界的浪漫诗人和风流名士。
如果说朝代的兴亡切断了冒辟疆的仕途举业和经世宏图,却让他得以全心全意地享受生活,在水绘园中经营出一个充满雅致、逸乐气息的世外桃源;那么,生活在太平年间,且仕途顺遂的王士禛,却并没有因为他的官员身份而停止追逐逸乐的生活。王士禛实际上是接续了冒辟疆等明末士人的余绪,既超脱于政治与族姓的纷扰之外,且“经由历史、文化的传承,为自己当下的情境和存在,创设出更丰富的意义”。
王士禛如此,生活在清朝鼎盛时期的袁枚也莫不如此。与王士禛相似,袁枚很早就考中进士,同样是科举考试的幸运儿。但不同的是,袁枚在少壮之年即脱离了官场,急流勇退,优游林下,而他辞去官职的理由也非常简单,就是忠于自我感受,“不甘为大官作奴”。辞官后的袁枚侨居于由他亲手设计的随园之中,极尽声色犬马之好,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甚而赢得了“山中宰相”的美誉。
诗文之外,袁枚精于园林、美食、古玩、旅行等各种娱乐,他常常“登山临水,寻花问柳”,而且“已为海内有名客,又占世间长命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袁枚的一生可谓淋漓尽致地展示出传统士大夫生活品味上的极致追求,进而为他们的精致文化和生活风貌树立了一个典范。
通过考察王士禛和袁枚的人生经历,我们隐然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十八世纪的传统文化和社会面貌,其实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冷酷森严。在令人窒息的乾嘉礼学背后,世俗社会依然有着相对广阔的个人生活空间,王士禛和袁枚不过是在这个空间中营造自己的生活,将个别的面向集于一身,并推向一个高峰。
明清社会的另一种面向
清代乾隆年间,汉学考据之风大盛,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然而在民间社会,却有两本小书在悄然流行,一本名为《霓裳续谱》,一本名为《白雪遗音》。这两本小书均为彼时流传于民间的情歌选和戏曲曲文,其中收录的或为“衢巷之语”,或为“市井之谣”。因为内容涉及“淫猥”,这些情歌和戏曲均曾被清政府明令禁止,却屡禁不止,经由民间艺人、艺伎和歌童吟诵,口口相传,散布在各地,得以让底层民众和四方商旅一慰平生。
相较于当时的社会风气,这些情歌和戏曲的流行显然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情。因为彼时清政府提倡的是“礼学”和“贞洁”,但民间社会却反其道而行之,乃至出现了“禁者自禁,演者自演,唱者自唱”的局面,对情歌和戏曲的吟诵,甚至达到了“户诵家弦,远出于圣经贤传之上”的程度。
这一方面固然与清政府鞭长莫及的管理能力有关,另一方面未免不是自然发展的趋势——对于大多数底层民众而言,主流社会的“礼学论述”不过是另一个世界的呓语,反倒是“淫词小曲”更能打动他们的人性本能,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
正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些情歌和戏曲的渲染力量,既起到了一种辐射与交流的作用,为民间社会提供了一条发泄的渠道;而在底层民众价值观或行为模式的塑造上,又厥功至伟。它们展示出的其实是一种自然、原始的民间文化风貌,这种民间文化既富有弹性,又具有一定的包容度;既与官方文化大相径庭,却也更真实,更接地气,更能反映出民间社会的真相。
正是这种流行于底层社会的民间文化,与侯方域、冒辟疆、王士禛、袁枚们私密的个人空间交织在一起,自上而下,构成了明清社会的另一种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