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学透视失败国家的泥潭
摘要:吊诡的是,最需要生产资料的非洲有着全球最高的资本外逃率。改变的关键,是提高国家信誉。这需要持续长期的和平与改革,不是表面的政治制度改革就能解决的。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一个内战与政变频发的区域,至今没有平息的明确迹象。英国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在《最底层的十亿人》中,剖析了内战风险的原因。他提出重点不在于政治压迫、族裔仇恨或收入不平等,而在于经济增长。
吊诡的是,最需要生产资料的非洲有着全球最高的资本外逃率。改变的关键,是提高国家信誉。这需要持续长期的和平与改革,不是表面的政治制度改革就能解决的。
冲突陷阱:发展才能带来和平
2022年7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布了一则令人心酸的喜讯,题目是“刚果民主共和国:83名因武装冲突而失散的儿童最终与亲人团聚”。这场寻人行动从2017年持续至今,迄今为止共寻回了2000多名儿童。这些孩子中有几名来自首都附近,但大部分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各省。
尽管两次内战名义上在2003年就结束了,2006年举行了民主选举,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战乱从未停歇,尤其是与卢旺达、乌干达等国接壤的东部地区。2008年,保罗·科利尔写道:“内战会留下一种遗产:有组织的杀戮。这种遗产是很难被根除的。对作奸犯科之人来说,暴力与敲诈勒索有利可图。杀戮是他们唯一知晓的谋生之道。我都有枪了,我还用去干别的事吗?”在十余年后的今天,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依然在不断为这句话提供着鲜活的证据。
科利尔在《最底层的十亿人》中,用“冲突陷阱”来描述这个常年困扰着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武装冲突时断时续,时强时弱,但几乎没有尽头。按照科利尔团队的模型,失败国家摆脱失败状态所需的平均期望时长是59年。当然,与现象描述相比,追根溯源更加重要,尤其是戳破错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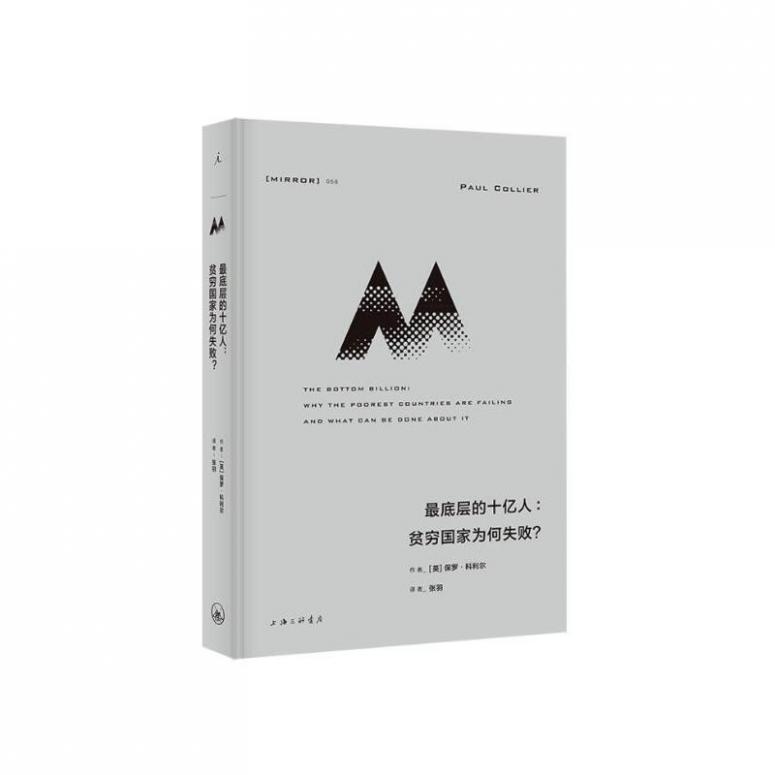
《最底层的十亿人:贫穷国家为何失败?》【英】保罗·科利尔 著张羽 译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9月
人们常常认为一些因素与内战冲突关系密切,甚至冠以“根本原因”的名号,但它们其实禁不起实证检验。这就是错觉。一个重要的错觉,是社会正义。反叛运动的参与者常常声称,自己举事的原因是政府对少数族群的压迫,族群和区域间收入分配不平等,或者归咎于数十年前殖民者留下的遗毒。
刚果民主共和国将军洛朗·恩孔达(Laurent Nkunda),是一名图西族人,与邻国卢旺达境内的图西族人是同胞。他参与过推翻卢旺达胡图族政权的战争,在第二次刚果内战爆发后与政府军对抗,即使在2003年停火协议签订后,他领导的队伍依然选择进入丛林打游击。2008年,英国广播公司采访了恩孔达,他当时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虐待图西族人,他拿起武器是为了保护同胞。类似的表述不绝于耳,真真假假。即便是没有立场的局外人,也常常默认,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不过,科利尔说得好:“公然的不满之于一场反叛运动,如同企业形象之于企业。”换句话说,反抗压迫是叛军打出来的旗号。旗号未必是假的,但如果认为旗号是决定反叛运动是否发生、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那就是自欺欺人了。
2003年,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吉姆·费伦(Jim Fearon)和戴维·莱廷(David Laitin),发表了一篇被广为引用的文章,题目是“族裔、反叛与内战”。通过考察1945年至1999年之间161个国家的冲突与内战,作者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一个民族是否受到政治压迫与内战风险无关;族群之间是否存在仇恨也与内战风险无关。与内战风险存在显著关联的因素有:贫困、政治不稳定、地形崎岖与人口众多。
当然,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与因果关系还有着相当远的距离,更不意味着应该纵容作恶的政策与行为。但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至少能够起到廓清的作用,避免陈词滥调阻碍真正有效的行动。
作为一名发展经济学家,科利尔详细分析了增大内战风险的经济条件。他认为,最重要的三个经济因素是收入低下、增长缓慢、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值得注意的是,收入不平等与内战风险不相关。这乍看起来违背直觉,但有一位前非洲国家副总统的话颇有启发性。在一场会议上,科利尔问这位被政变赶下台的副总统为什么提前不做防备,副总统说:“我们掌权的时候,国家已经穷到没有什么可窃取的了。”
科利尔测算了经济增长率与内战爆发风险的关系,大体上是成一比一反比的关系:经济增长率每增加1%,爆发内战的风险就会降低1%。当然,反向的因果关系看上去也是合理的。没有多少公司想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地方投资,援助机构往往也会等待局势稳定后再恢复注资。于是,科利尔选择后退一步,找一个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率,但与内战风险没有直接关系的因素,然后看它会不会提升内战爆发的可能性。他找到的因素是降雨异常。
在依赖农业且基础设施条件差的低收入国家,尤其是热带国家,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风险因素。在极端天气肆虐全球的今年,孟加拉国和缅甸城市被淹的画面频繁登上新闻。尼日利亚等西非国家也爆发了猛烈的洪灾,一位州长表示,全州10年的预算总额都不足以解决洪水侵蚀土地的问题。尽管降雨异常与人类活动有关,但毕竟是一种自然现象,不会受内战的影响。不管武装分子有没有屠村或者攻陷总统府,该发生的洪灾和旱灾都会发生。如此一来,反向因果关系就被排除了。
经济学家将这种方法称为“工具变量法”,它不仅是一种确定因果方向的技术手段,也有着切实的指导意义。确切的宏观因果方向意味着,一些西方政客常年挂在嘴边的方案可能只是刻舟求剑,比如向内战后国家的人民宣讲和平是多么重要和美好,劝说大家以礼相待,举止得体。正如科利尔所说:“在脆弱不堪的社会中……更加直接的解决方案可能是让这个社会变得不那么脆弱,也就是要发展经济。”
资本外逃率40%的非洲
指出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是一码事,提出促进增长的有效策略是另一码事,这里涉及到科利尔对世界的划分。自冷战结束以来,人们惯于按照收入水平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另一个类似的说法是“南北分歧”。但专攻非洲研究多年的科利尔认为,发展中国家中最贫穷的10亿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质的区别。
正如他所说:“全球贸易的增长对亚洲来说再好不过了。但是不要指望贸易可以帮助最底层的10亿人。”这意味着,适用于“亚洲四小龙”或印度尼西亚的增长路径,未必能够复制到中非共和国、塞拉利昂或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中间的关键区别在于资本流向。简单地说,在亚洲国家,资本是在积累和流入的,而在最底层的10亿人生活的国家,资本是在耗散和流出的。
在一篇1999年的论文中,科利尔估算了到1990年为止非洲资本外逃的状况,得出的结果令人震惊。在非洲人的全部私人财富中,海外持有的比例高达40%,甚至比中东国家还要高,而东亚当时的平均资本外逃率仅为6%。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日常情况相比,连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资本外逃都只能相形见绌。对于汹涌的资本外逃,一个常见的解释是政治动荡、腐败和不利的政策环境。
这是一部分原因,但并不能解释全部。1980年代的韩国是一个高度腐败的国家,1981年至1982年爆发的张玲子事件是震动全亚洲的金融诈骗案,沉重打击了时任韩国总统全斗焕的公众形象。张玲子是全斗焕妻子的叔父的小姨子,其丈夫李圭光是前任韩国中央情报部次长。借用这层关系,夫妇二人倒卖超额期票牟利,总额约合2.5亿美元。在舆论压力下,全斗焕暂时拘捕了李圭光,但随即给予假释。类似事件在当时的军政府统治下司空见惯,但并没有妨碍同时期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根本原因在于信誉。正如科利尔所说:“即使最不发达国家成功摆脱了政治动荡与政策环境恶劣的问题,仍然会被先入为主地视为风险地区。投资者会担心这些国家开倒车,因而拒绝向其投资。”信誉本身是一种观念或者刻板印象,但改善和维持信誉需要长期的现实努力,有时甚至需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
资本是逐利的,也是关注风险的。对大规模投资的投资者来说,最严重的风险之一就是政府先宣称要实行改革,等资金到位后悍然毁约。这意味着,鉴别改革的真假是海外投资项目的必修课。从这一点出发,科利尔提出了改善信誉的关键策略:实施假改革者绝对不会推行的改革措施,比如主动归还财产和裁减公务员,尤其是在没有国际机构以撤销援助相要挟的情况下。对政变或内战胜利后上台的国家来说,领导人手下拿着枪的弟兄们一般都在等着分赃,实行这种政策无疑有着巨大的政治反弹风险。
除了资本流出以外,另一个大问题出在资本流入的行业上。事实上,不少非洲国家并不缺少资本流入,但大部分情况下不是流入制造业,而是石油、钻石、矿产等资源开采行业。经济弊病是一方面。当自然资源开采成为一个国家最方便、最主要的外汇来源时,其他创汇手段会受到挤压和萎缩,尤其是对后发国家至关重要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这就是所谓的“荷兰病”。
科利尔还重点强调了另一个较少受关注的因素: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社会治理的侵蚀。萨达姆等石油独裁者的故事广为人知,但这并不意味着西式民主就是破解“资源诅咒”的万灵药。为了摆脱对中东国家的石油依赖,美国从1980年代就开始寻找和扶持实行西方制度的产油国,比如非洲的冈比亚和塞内加尔、亚洲的东帝汶、加勒比海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尽管发现了新油田,这些国家的经济依然鲜有起色。科利尔举出了一个直观的数字,在自然资源带来的盈余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低于8%时,西方体制国家的增长快于独裁政权;而占比超过8%时,增长优势就消失了。
对迷信西式民主的人来说,这不啻是晴天霹雳。但结合低收入民主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结果倒也并不意外。在通常情况下,吸引选票的手段是造福于民,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但在缺乏多元信息渠道、社群领袖控制力强的国家,直接用来收买地头蛇,或者干脆收买选票是更快捷的竞选手段。开采资源带来的巨额收入只会持续为这种作弊行为输血,反而让良性的治理生态更难建立。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