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凯恩斯”高桥是清
摘要:中国与日本对于战后的这两次和会,有着不同的历史记忆,但在相异之中也不乏共同之处。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巴黎和会固然是耻,华盛顿会议也不遑多让;而在日本人看来,巴黎和会只给了日本口惠而实不至的列强虚名,这一切在华盛顿会议之后又再度幻灭。此消彼长,一进一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让东亚两国都颇有怨望、耿耿于怀,种下了今后更具破坏力的种子。
中日两国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的会外签署条约,日本将山东交还中国。时任日本首相高桥是清(尽管他只做了几个月的首相),成为日本政坛对华友善(不是“亲善”)的代表。
这位“日本的凯恩斯”是如何炼成的?“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他,又走过了怎样曲折的人生历程?
从巴黎和会到凡尔赛会议,中日关系的竞合沉浮
1919年巴黎和会成为中国“国耻”,并且诱发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其实短短三年之后,中国就在国际舞台上“消除”了这些国耻,不论是文字意义还是暂时性质。
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列强对日本称霸远东的野心予以猛烈抨击与坚决压制。这不仅重新调整了远东与太平洋的格局,还打破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重新使中国回到多个列强共同支配的战前状态”。
中国与日本对于战后的这两次和会,有着不同的历史记忆,但在相异之中也不乏共同之处。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巴黎和会固然是耻,华盛顿会议也不遑多让;而在日本人看来,巴黎和会只给了日本口惠而实不至的列强虚名,这一切在华盛顿会议之后又再度幻灭。此消彼长,一进一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让东亚两国都颇有怨望、耿耿于怀,种下了今后更具破坏力的种子。
但至少在1919年到1922年三年里,中日两国从“彼此怨怼”竟然走向了短暂的“惺惺相惜”,这一变化与甲午战争前后极其相似。明明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两个汉字国家却因为西方列强的压制而有了一点点同病相怜。
中国这边,痛恨欧美纵容日本侵略是一开始的主旋律,但在欧美白人的傲慢面前,中国人也生发出了“东亚主义”、“黄种人联合”的心态,二十年代孙中山也在鼓吹的“大亚洲主义”就是明证。
日本这边,用松冈洋右的俏皮话说就是:“西方列强教会了日本如何赌博,但他们在拿走筹码之后就宣布游戏不道德并离开牌桌,剥夺了日本继续上桌的资格。”巴黎和会上日本人“种族平等”的提案惨遭否决,还被调侃为凡尔赛宫里“沉默的小伙伴”。至于华盛顿会议前后,日本感受到的更是被压制被霸凌的耻辱:身为一战战胜国,日本的海军吨位被严格限制;独占中国的既成事实,遭到列强的否定与逼退;美国国会1924年通过的移民法案(俗称“排日法案”)加剧了这一情绪。
1922年,中日两国在华盛顿会议的会外签署条约,日本将山东交还中国。日本的这一决定在当时颇有一些不心甘情愿,但在会后无意中推高了“中日联合”的气氛。时任日本首相高桥是清(尽管他只做了几个月的首相),成为日本政坛对华友善(不是所谓“亲善”)的代表。
高桥是清在一战战后(那时他只是藏相)向首相原敬递交了《内外国策私见》,以及《树立东亚经济实力之意见》这两篇备忘录。这两篇在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的文章,会让人觉得有点惊世骇俗,因为它不符合日本长期以来的国策。
一战战后,日本派兵干涉西伯利亚,劳师糜饷而且一无所获,陆军在西伯利亚的无知妄作让高桥是清大为光火。这次出兵不仅代价高昂,也危及了日本与高桥眼中主要盟友的外交关系。但在高桥看来最严重的事情是,这件事标志着军部不愿服从首相及其内阁的领导。日本军队兵临西伯利亚之后,上原周作就声称,所谓“无上统帅权”已经落地。也就是说,由天皇而非首相指挥军队:军部只需向自己报告,首相也无权置喙或是下令终止军事行动。
大为触动的高桥,在1920年9月的《内外国策私见》里表示:“我国制度给外国的印象就像是一个陆军参谋本部统治的军国主义国家一样……正是拜参谋本部所赐,我国的军事机构并不隶属于内阁,而是独立游离于国家政治制度之外的。陆军一刻不停地计划派兵出国大兴征伐,这同时干扰到了外交经济两方面的国策,导致我国缺少统一的外交政策……正因为陆军参谋本部屡屡干涉其他国务机构,我们就当废止这个机构,统一陆军的组织架构。很高兴的是,海军参谋本部并没有像陆军那样惹是生非,但这毕竟也是一个不必要的机构。我们应当在同一时间废止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参谋本部。”
这是极富远见与洞见的判断,但不幸的是高桥本人与日本国运,都因为备忘录里指出的问题而在昭和年间惨遭毁灭。
高桥不但警惕军部的过度扩张,也极力反对日本对中国变本加厉的侵略。同样是出于日本自身利益考虑,高桥的国策意见却与那些满脑子大陆政策的军部人士不同,他希望以和平发展谋求日本的长远利益。
高桥认为日本应当促成中国的统一,与中国政府通力合作,尊重中国民众的意愿,打造中日经济联盟,与英美展开经济而非军事竞争。因此高桥反对“二十一条”与西原借款,也不赞成对中国大陆任何形式的军事干涉。
1921年5月,高桥在《树立东亚经济实力之意见》里写道:日本应当从中国撤出全部军队,关闭所有军事基地,停止以贷款换取铁路、矿产的政策,放弃在华的其他特权,以及用来迫使中国雇用日本专家、顾问的那些手段;取消强迫中国以当前或是未来政府收入(取自增税)作为贷款抵押的政策;此外,限制单方面向中国大陆地区性势力或是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借款的行为。高桥也反对“满洲是独立于中国的政治实体”的观点,不认为日本在那里有什么特别的利益和权利。
高桥重申,日本从一个强盛、工业化的中国盟友那里获得的好处,要胜过被日本金元外交和军事干涉肢解的那个孱弱分裂的中国。高桥深信,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很快就会造就一个统一的中国,而中日两大东亚国家的联盟一体就能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力量,抵抗盎格鲁-美利坚的经济霸权。
不过高桥也强调,他想打造的是经济而非军事同盟,而且这个经济同盟也应当在国际通行的贸易框架之内,与西方列强开展经济竞争。日本的中国政策,应当着眼于统一的中国,而不是满洲这样的局部地区。备忘录也提出,欢迎欧洲和北美资本到中国做生意。不过高桥补充说,如果欧美资本不来,日本就当单独行动。
这些观点无疑与当时的军部不相枘凿,也与绝大部分文官领袖和不少公共舆论南辕北辙。原敬首相也在看过这份备忘录后,给这份文件打上了“必须反对的书生之见,我们应当警惕、不让这份文件泄露”的标签。
高桥是清的对华政策思路并非心血来潮,从1907年见到张之洞开始,高桥就深信一个独立稳定而且统一的中国对日本更有好处,而不是那个四分五裂国贫民弱的中国。高桥这种独特的中国观,又是如何形成的?
本来不该对华友善的高桥是清
回顾高桥是清的一生履历行止,他似乎不应该是个对华友善的人。
高桥是清出身破落的仙台藩士之家,生父曾是幕府的御用画师,养父则是最低等的武士——足轻。而与同样出身低等武士的“幕末三杰”相比,高桥的年资相对较晚,还不够赶上幕末时代风云的机会,出身佐幕藩的背景也一度给他带来不少麻烦。
他的教育背景也非常特殊:既没有接受传统武士的汉文(朱子学、阳明学)教育,也未能赶上明治维新初年的新式教育。终其一生,高桥甚至从未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他的所有知识与能力,都源于自学与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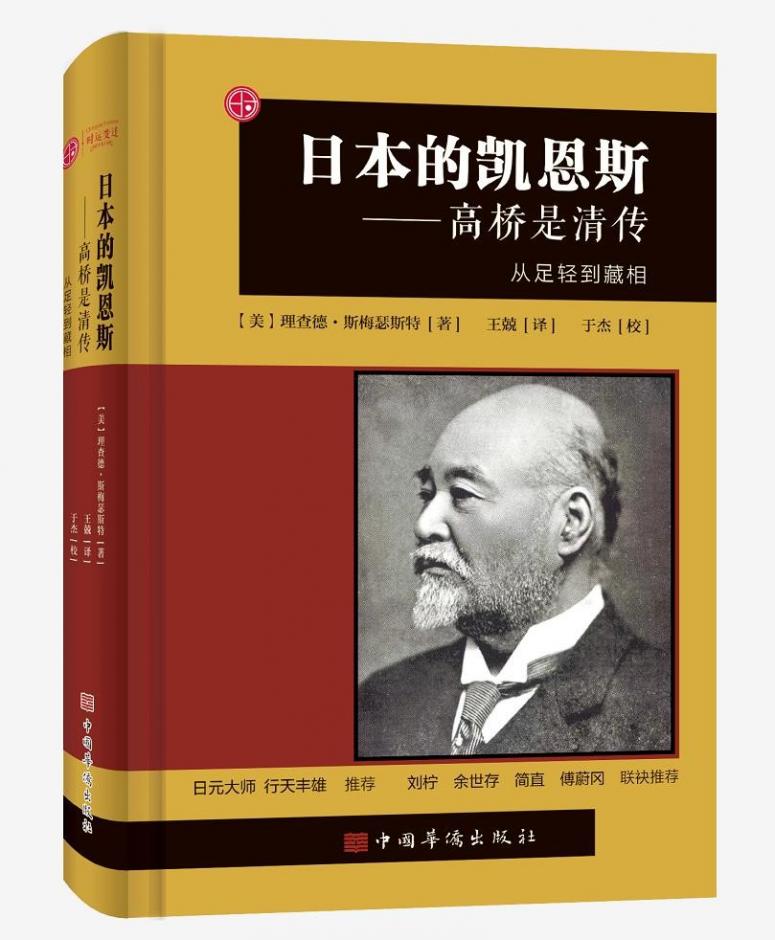
高桥很不幸地生在了一个剧烈变动的世界,也很幸运地生在了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
1854年(嘉永六年),高桥是清出生于东京,生父是幕府御用画师川村庄右卫门。幼年高桥可谓命途多舛,他的青少年时代也折射出日本社会在幕末明治年间的震荡。生父身为御用画师,本来家境优渥,却在黑船来航之后与幕藩体制一样走向败落;养父高桥是忠,只是幕府最低等级别的武士(足轻),如果幕藩体制延续下去,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阶层提升的机会。
高桥的幸运在于,他赶上了时代变动的窗口期,而旧有的武士身份又给了他提升的可能性。如果日本开国之后他仍然由生父抚养的话,宫廷画师之子反而不容易有出人头地的机会。1870年代,高桥凭借英语能力做上翻译与教师的时候,薪酬之高已经足以借给生父家里一笔钱。这是那个日本社会阶层变动剧烈时代的一个缩影。
高桥非常幸运地摊上了一名深明大义的养祖母——高桥喜代子。正是在养祖母与养父同侪武士的帮助下,幼小的高桥就有机会前往横滨,跟从第一批到达日本的西洋人士学习英语。他的英语老师正是那个发明了平文式罗马字的詹姆斯·赫本之妻——克拉丽莎·赫本。13岁那年即1867年,也就是明治维新大局底定之前,高桥是清就踏上了留学之路,与其他几名武士幼童一起登船赴美。
一个10岁孩子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他会遇到何等艰辛与何等考验?本来按照约定,高桥赴美之后会在加州的范·里德夫妇家里做长工、学徒,顺便学习英语,然而,下船之后的高桥见到范·里德之后,事情的走向就完全不同了。范·里德热情“引荐”高桥去他加州奥克兰的富裕朋友布朗夫妇家里,英语水平一般的高桥与同行的一条十次郎糊里糊涂地签下了公证机关的一纸文书。这是一张契约奴隶的卖身契,为期三年。
布朗夫妇骗了他,但高桥起初浑然不觉。彼时的奥克兰仍然是近乎蛮荒的拓殖城市,高桥在这里的头几个月里悠然自得。布朗夫人教他英语书法与阅读,还为他置办衣物。高桥负责照顾他们的婴儿,下厨做饭,照顾马匹。然而,他与布朗家的华工厨师意外地发生了激烈冲突。差点拿起斧子与华工厨师同归于尽的高桥决定离开,得到的答案则是“我们买了你三年,你不能走”。
幸运的是,布朗夫妇仍然对高桥很好,哪怕他总是想着逃跑还几次罢工,也继续发给他薪水,同时依照契约奴隶的条款教他英语。凭着在布朗夫妇家打工挣到的几十美元,借助美国友人的法律服务(美国内战之后,贩奴已经违法),抓住老布朗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机会,高桥是清成功摆脱了契约奴隶生涯,并在1868年12月成功回国。
高桥在美国被迫卖身为奴的18个月里,对他的一生影响良多。他在这段时间里密集接触了中国人与美国人,独特的经历让他认识了中美两大文明的方式(这也是影响日本最大的两大文明),与同时期的其他日本人都颇为不同。
赴美船上让他难以下咽的“南京红烧肉”、同船衣衫褴褛的华工、在美期间给他使绊子穿小鞋的中国厨师,让他童年就接触到了大量中国人。居高临下但又不乏温情的美国主人,照章办事的美国社会,也让高桥在与美国人交往时找到了英美文明的密码。

从小就与中美两种文化密集接触,让高桥毕生都免于先入为主的偏见,也没有沾上各种窒碍终生的意识形态。被美国人占有、保护、教育的幼年经历,让高桥终其一生都可以灵活娴熟地与西方人打交道而不卑不亢,身段柔软而又长袖善舞。
历尽艰辛回国后,高桥的人生如走马灯一样变换。他做过翻译,吃过软饭,当过老师,炒过期货,玩过矿场,起草过日本第一批商标与专利法,靠着英语能力混出了头,在横滨正金银行任上起飞,在日俄战争期间一战(借)成名。高桥一身兼具勇敢、变通、坚韧与自我的素质,他热爱交际,性情开朗,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毫不害羞,成为数十年来日本政坛洋务派的代表。
日俄战争是高桥一生的高光时刻。他衔命出使欧洲,在欧美财团之间纵横捭阖,发动各种外交攻势与私人交情,成功扭转了欧美“将日本与中国同等看待”的霸权心态,从西方借到了价值8亿56万6000日元(8200万英镑)的日本国债,筹集了占总额47%的日俄战争军费,帮助日本打赢了这场跻身大国地位的战争。在此期间,高桥是清与犹太银行家雅各布·希夫等人的深入交往,让他更深入地浸淫欧美金融市场,一生言思学行已然臻于化境。
高桥被认为是日本最杰出的藏相。他在1930年代初推行的一系列“逆周期”经济政策(货币贬值提振出口,宽松财政刺激经济),为他赢得了“日本的凯恩斯”的美名,率领日本第一个走出了大萧条。甚至于,高桥的经济政策还要早于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出版时间。
高桥支持日本的帝国工程,但他仅仅支持英美秩序框架之内的日本帝国大业,这在后世被称为“小日本主义”。高桥深信,加入世界经济秩序会大大有益于他的“富国”目标,但他反对一切威胁日本世界经济秩序地位的无知妄作之举,尤其是穷兵黩武挑战英美的疯狂行为。1930年代的一次五相会议上,高桥当场飙骂陆相荒木贞夫:“是不是军部真有一些白痴觉得,日本可以赢得与美国的战争?”
多年从事金融实务的经历,也让高桥成为极少数意识到中国对于世界秩序之意义的日本人。1895年供职横滨正金银行时,高桥就不无惊讶地发现,决定日元汇率的并非这家日本官方的外汇银行,而是位于香港与上海的汇丰银行。外国公司甚至大一点的日本公司,都舍近求远从汇丰等外国银行购买外汇,而不是就近找正金银行。如果日本贸然进攻中国本土,冲击香港上海这两个世界金融节点,日本就不止是在入侵中国,也是向世界、英美秩序宣战。
高桥从甲午战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已经看出,过度侵略中国的恶果不但有极大可能激发中国的反日情绪,而且会挑战英美主宰的国际秩序、引发列强干涉,最终面临被中国与英美夹击的局面。日本想要突出重围,难度可如登天。
高桥非常清楚,日本能够打赢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靠的恰恰是与英美合作。三次战争胜利的结果应该告诉日本,继续安处于英美秩序之下和平发展是最好的选项,而不是重蹈德国与沙俄的覆辙。
1915年一战期间,高桥就批评“二十一条”政策“笑止千万”。他所担心的是,“独占中国”的需索无度不但将带来浩大的军费开支,也会再度引发中国人的敌意,让日本外交落入与英美对抗的险境。
同年4月,高桥在致雅各布·希夫的信中说:“我个人本来对本国政治风云没什么兴趣,但是现在内阁的外交做法还是让我不得不忧心忡忡,特别是他们与中国的这几轮谈判。加藤男爵对谈判内容统统守口如瓶,即便那些已经结束的谈判也不例外。我们不得不根据国外流传的新闻报道推测谈判情况。如果我的焦虑最终被证明是无稽之谈那最好不过了,但若是恰恰相反,也就是外国传来的这些报道并非捕风捉影的话,那么我焦虑的理由可就太多了。原因在于,我们的外交工作似乎太当儿戏了……你认为中日关系应当是天然同盟,这一点甚合我意;但我更担心的是内阁现在的中国政策势必将把中国人推得更远,强化他们对日本的恐惧仇恨之意。”
数年之后,高桥依然流露出对“二十一条”的负面看法:“我们已经伤害了中国的自尊心……二十一条里的头五条几乎侵蚀了中国的主权。”
在那个英美秩序笼罩全球(包括东亚地区)的时代,高桥是清敏锐而正确地认识到了西方资金、技术、市场的重要性,意识到未来的全球竞争将是以贸易手段为主的经济竞争,不再是老旧的帝国主义领土扩张。
1936 年新年,高桥接受《朝日新闻》专访时,就批评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如果一个国家意欲称霸并耗费大量金钱,那么又能带来多大利益呢?在收获利益之前,本国还得扛着殖民地这个负担。”
“内在文化堡垒”与日本人的中国观
传记作家在评价高桥时,常常将他称为一名世界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这是彼时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帝国主义双峰对峙的另一大思潮。高桥的中国观与其说是“日本人看中国”,毋宁说是“从小接受美国教育的日本人,带着美国滤镜看中国”。
如此一来,高桥与同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观如此迥异,也就不难理解了。
正如日本历史学家辻康吾所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观处在一种“双轨制”:一个是主要为汉学所一路承担下来的对古典中国的憧憬与研究,其后,并无关中国的政治变动,只是单纯作为日本教养的一部分被继承下来;另一方面,明治以降,以深刻关涉日本“国益”的形式而勃兴的对近现代中国的关注,同样在经历一番变动之后,成了今天中国研究的主流。
一方面仍然继续尊重、研究、阐扬古代中国,另一方面则对晚清中国极尽刻薄、贬损与提防,这种奇特的“两条路线并存”的矛盾现象,始终贯穿于明治到昭和的七八十年时间里,甚至到今天也还不无存在感。仔细观瞻这两条路线就不难发现,日本人的教育背景与成长经历,与他们“中国观”的成型密切相关。
英国学者乔治·桑松曾就日本文明提出一个命题:日本人虽然在表面上大量“借用”(borrowing)许多东西,但却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内在文化堡垒”(inner cultural citadel)。
这个命题直至今天,仍然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幕末维新志士几乎无一例外接受了传统的汉文教育(朱子学,阳明学),但在日本开国接受西方文明之后,立即生发出了对西方文明的景仰之情,随之而来的是对晚清中国的蔑视之意。
在他们看来,剃发易服而又积贫积弱的晚清早已失去代表中国的资格,引领东亚文明的重任落到了日本头上。汉学修养极好的吉田松阴、西乡隆盛、陆奥宗光对华强硬,从美国回来以后还要请人补习汉文的高桥是清却对华较为友善,同时期的币原重喜郎、滨口雄幸亦然。不能不说,是他们“闻道有先后”带来的歧异。
如果将日本人的这种”内在文化堡垒”视为一层又一层的同心圆,那么先接触汉学同心圆再接触洋学同心圆的日本人容易接触“脱亚论”、“征韩论”、“进取满蒙”的大日本心态,用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话语掩饰扩张侵略之实。反倒是先接触洋学同心圆,再接触汉学同心圆的日本人,更容易理解二十世纪初以来扶摇直上的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对中国表示同情与帮助。
日本对华的复杂态度,正好与日本对英美的复杂态度互为表里。这种双重的复杂态度造就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高桥是清”,也塑造了近代以来日本“激荡的百年史”。如果结合“内在文化堡垒”这个命题,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就谅非难事了。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