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情绪本能的天气图景
摘要:在背景和边缘,亮黄色的火焰舔舐着大半个天际线,滚滚浓烟从窗户和屋顶中冒出。这分明是一场已经蔓延开来,无可挽救的野火。因此,贯通天地的火柱也好,猩红色的水滴也好,它们想要表达的必然不是野火的来源,而或许是受灾者的心理感受。对身处火场的人来说,最直观的体验大概就是飞来横祸。
从2022年6月份开始,异常高温席卷整个北半球,从欧洲到北美频现40摄氏度以上气温,突破历史最高纪录。德国气象学家弗里德丽克·奥托(Friederike Otto)评论道,极端天气“不仅是天灾,很大程度上更是人祸”。
事实上,天气与气候从来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更与人的风俗、信念乃至生存密切相关。人类一面遭受着野火、浓雾等灾害的荼毒,寻找着预防减灾的法门,一面试图用人工降雨等积极手段操控天气。美国设计师劳伦·瑞德尼斯(Lauren Redniss)的《电闪雷鸣》,借助一幅幅粗粝而富有力量的图画,展现了人类与天气千百年来的拉锯战。
天火落湖心
《电闪雷鸣》原书出版于2015年,其中有一章叫做“热”,主题就是森林大火,又名野火。作者采访了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教授戴维·鲍曼(David Bowman)。鲍曼口中的野火“就像野生动物,像蛇”,照片中的野火是真切而骇人的,常见的元素有只剩树干的大树、漫天的浓烟、熊熊燃烧中的屋舍、努力扑救的消防人员等等,远景下的山火更是恍如红莲地狱。
然而,真实性与现场性也为摄影这一载体施加了天然的限制。比如,自然界中未必能恰好出现最有冲击力的组合与瞬间,丰富的细节也容易让人的注意力失焦,脑海中只留下“好可怕”的单调印象。而这正是画作所能够弥补的方面。
瑞德尼斯的一幅图乍看令人费解,一道粗壮的火柱从左下角贯通到上方中央,覆盖了三分之一的画面。火柱下方有一个头朝上看的人,似乎是从窗户里向外呼救。再加上火柱两旁是密密麻麻的红色“雨点”,我起初以为这是天火。那么,也许作者想要描绘的是一场陨石引发的火灾?不过,尽管陨石在电影中常常表现为火球,但接触地表的陨石温度通常并不高,甚至用手摸都不会被烫到,自然也不会引发大规模的火灾。即使是重达几吨的陨石,造成伤害主要靠的也是动能,而非热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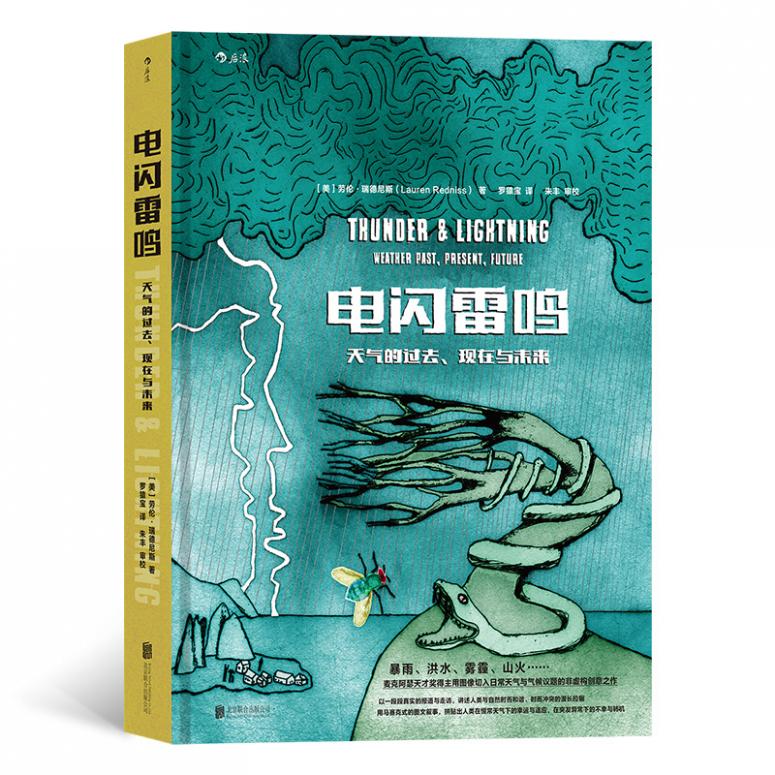
《电闪雷鸣:天气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美】劳伦·瑞德尼斯 著罗猿宝 译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5月
在背景和边缘,亮黄色的火焰舔舐着大半个天际线,滚滚浓烟从窗户和屋顶中冒出。这分明是一场已经蔓延开来,无可挽救的野火。因此,贯通天地的火柱也好,猩红色的水滴也好,它们想要表达的必然不是野火的来源,而或许是受灾者的心理感受。对身处火场的人来说,最直观的体验大概就是飞来横祸。
当然,野火的到来并非毫无预兆。气象学家可以利用往年数据建构模型,并利用监测数据预测野火发生的可能性,并通过政府和组织发布警告。但正如瑞德尼斯所说:“最近的火灾,即使对最有准备的人来说,也是很大的灾难。”
2009年发生在澳大利亚东南部维多利亚州(Victoria)的一场真实野火,为图画提供了另一种解读。临近中午时分,山丘出现了少许烟雾,但火灾此时其实已经无法控制。几分钟后,赶到现场的消防队员发现了“两股火舌”。在强劲的西北风吹拂下,大火一路向海岸狂飙。到了傍晚,风向变化让6公里宽的火场一下子拓展为50公里宽。
这场大火最终荼毒了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三分之二个上海市的面积。一名幸存者跳进湖中躲避,他事后回忆:“狭长的橘黄色火焰爬过河岸草地,它像一个生物一样……我能从水下看到余烬下降,就像橘色的灯光透过绿色的玻璃一样。”
对应这段描述,图中的人应该就是那位跳湖求生的幸存者,而形似雨点的东西是房屋爆炸后产生,接着落入湖水中的灰烬。不过,这幅图画依然应该从心理图像的层面来解读。毕竟,房屋不可能漂浮在水面上,火焰也并没有烧进湖中央。但在幸存者看来,他或许正是被天火席卷,被灰烬环绕,火焰则代替了地面,承载着正在化为焦炭的建筑物。
瑞德尼斯没有给这幅画起名,也没有给出确切的描述。整本书都是如此,甚至有一章(“天空”)没有任何文字。在很大程度上,作者的创作意图隐而不现,读者只能凭借文字线索和想象力来解读画面给自己的强烈冲击力。这是一种被迫却心甘情愿的主动阅读,寻找画中与画外之意的过程出奇地愉悦。
八页大雾
纽芬兰岛(Newfoundland)位于加拿大最东侧,当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暖流在岛最东端的斯必尔角(Cape Spear)相遇时,浓雾就会出现。用前灯塔管理员格里·坎特韦尔(Gerry Cantwell)的话说:“雾气虽然不像窗帘一样垂下来,但也差不多了。”
瑞德尼斯采用了一种不吝惜页数的方式,来直观呈现海角的浓雾。首先是两个整页的岛屿景象,暗绿色的草地上点缀着黄色和红色的球形小花,近处还有一朵画得比较精细的花草,看样子大概是一种在当地叫做“圣约翰草”的植物。圣约翰(St John)是纽芬兰最大的城市,斯必尔角就在圣约翰东南方向不到10公里处。圣约翰草的中文名是贯叶连翘,它的叶子没有叶柄,末端紧贴着茎,彼此又靠近密集,看上去就好像被茎贯穿一样,故名。
瑞德尼斯的图中准确地描绘出了这一特点。尽管图中的上半部分都是灰色的,但整体给人的感觉并不压抑。读者站在离大海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享受着纯净的空气与天然的美景。
然而,从读者翻开下一页的开始,体验就发生了突变。接下来的整整8张16开纸全部都是灰色,稍微深一点的灰色代表大块的物体,可能是岸上的丘陵,也可能是海上的冰川,甚至可能是幻觉。大雾的倒数第二页上印着一位船长的感言:“去年夏天,海上有雾气,我们航行着寻找岸边的灯火,也在寻找冰山。我那时在想,‘噢看哪!我看到那里有一束光。有人看到了吗?’不,没有人看到。我以为我看到了,其实没有。当我读到雷达表盘读数时,我想明白了,哦,我们已经行驶了5千米,能见度不到1千米。我绝对不可能看到那束光。”
这还是已经有了雷达的现代。如果回到100多年前,在这片水域航行该有多危险呢?在延续了8页的大雾散去后,迎接读者的不是熙熙攘攘的港口,而是一场海难。1854年,号称当时最坚固、最快的蒸汽轮船“北极”号从英国利物浦(Liverpool)启航,驶往大西洋对岸的纽约。7天后,“北极”号在斯比尔角南侧与一艘法国船只相撞。在浓雾中,当“北极”号三副大喊“右满舵”的时候,一切都已经迟了。撞击发生后不到一分钟,船就消失在了大洋中,408名乘客中只有86人生还。
海难惨剧之后,瑞德尼斯终于允许读者喘一口气了。我们看到了传统灯塔中使用的两种奇特器械:一种是圆锥形的雾角,末端直径有一人多高,按照固定间隔发出悠长而低沉的声音;另一种名叫阿尔冈空心灯芯灯,工作人员从末端的开口添油,油顺着管道流到装着油脂的碗里,燃烧的灯芯漂浮在碗中,核心构造是一个内凹的灯罩,起到聚焦的作用,从而将光线投射到海上。
进入20世纪后,电力和自动机械灯取代了旧式设备、旧灯塔和旧灯塔管理员。但正如一位加拿大海岸警卫队的警长所说:“绝大多数海员,即使他们配备了雷达,也还是喜欢向外看时能获得慰藉……比如看到水里的浮标,或是听到雾角的声音。”
人定胜天的迷信
在与天气的交往中,人类并不总是消极应对的一方。早在原始社会中,巫师们就试图控制天气,而且发展出了形形色色的巫术。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James G. Frazer),在名著《金枝》中记载了俄罗斯、北美、东非、印度、澳大利亚等众多地区的求雨术和止雨术。印度东南方有一种“火克水”的仪式,就是让一名赤身裸体的女孩手持燃烧的木柴,走进雨中。弗雷泽认为:“那个燃烧的木柴,便是让她拿给雨水看的。”
与其说巫术体现了古人的愚蠢与狂妄,倒不如说反映了人类根深蒂固的社群精神。仪式既是演给天看的,更是演给人看的。这一点在苏轼的祈雨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且起。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简言之,苏轼是站在地方官的立场上,斥责雨神渎职,令小民无辜受苦,之后更是责令雨神整改。
当然,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仪式基本都是无效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才开始了实用的人工降雨实验。除了农业以外,战争是人工降雨的另一个重要用途。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云物理学家本·利文斯顿(Ben Livingston)对越南实施了数十次“播云”,目的是让林中小路更加泥泞,从而妨碍敌军行动。
在利文斯顿以本人为主角原型创作的一部小说中,人工降雨甚至拯救了世界。一场流星雨将毒云带到了地球,如果飘浮到人口密集地区,必将造成巨大灾难。于是,一位气象学博士决定向毒云投放硝酸钾,将毒云打散,最后用碘化银让小块毒云化为大雨,降落在大西洋上。瑞德尼斯绘制了毒云爆炸的壮观插图,看上去就像太阳凌空爆炸一般。更动人心魄的图却不是这一张,在爆炸图的前一页,博士手中握着粉色的毒云,笑容中洋溢着自信,用将军下令的口吻布置着摧毁毒云的任务。
如今,为了对抗全球气候变化,地球工程学应运而生。一些设想着眼于全球,比如减少抵达地表的阳光的“太空遮阳伞”;另一些设想的目标是更积极地引导局部天气。
利文斯顿便投身于这项事业,可惜成果寥寥。他说:“我给华盛顿特区的每一名参议员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计划。天哪,他们完全不想碰这个事情。他们能想到各种各样的理由劝说我不应该和自然作对。”
显然,人对天气的顺应与改造还将持续下去。不过,从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极端天气来看,留给人类的时间大概不多了。
在接受中文译者的采访时,瑞德尼斯对天气预报有一段富有深意的评论:“我觉得其实对于天气,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而这种‘迷信’也是我们在试图掌控不确定天气的路上的一种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