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否由寄生虫操纵?
每个人都与寄生生物有着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头上的虱子让我们头痒难耐,由柑橘木虱传播的黄龙病威胁着我国19个柑橘生产省中的11个,弓形虫更是许多猫主人的恒久隐忧。
美国科普作家凯瑟琳·麦考利夫(Kathleen McAuliffe),在《我脑子里的不速之客》一书中则更进一步,提出:“处于进化阶梯高层的宿主可能会像牵线木偶一样被简单的寄生生物……玩弄于股掌之间。”她还用大量前沿科研成果进行了论证,比如一个证明感染弓形虫的小鼠会不怕猫的巧妙实验。
寄生生物与人类社会文化也有着深层的关联,尽管常常掩盖在宗教、文学、美食的面纱之下。比方说,通过人类学与医学的交叉比照,也许吸血鬼的原型正是狂犬病患者。
不怕猫的快乐老鼠
经典动画片《黑猫警长》中,有三只生猛的非洲“吃猫鼠”,他们是一直与森林警局作对的老鼠“一只耳”的舅舅。身穿蓝衣的鼠舅舅,一出场就霸气十足,只见他昂首阔步,右手攥着一把阔刃大刀,左手提着一只水桶,桶里装着一只比“一只耳”还大两三倍的猫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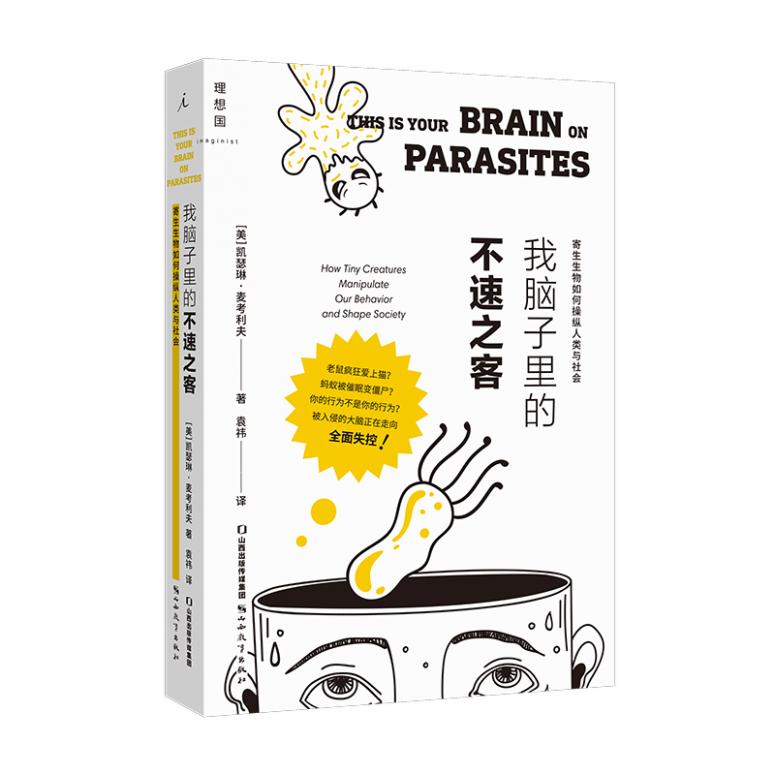
《我脑子里的不速之客:寄生生物如何操纵人类与社会》
他走道连路也不屑于看,一脚踢飞正躺在海滩上休息的一只耳,还张嘴就骂:“你这野小子,敢挡住我的去路。”经过侄子的一番挑唆,脾气火爆的蓝衣吃猫鼠叫上大哥二哥,远渡重洋,率领群鼠冲进派出所,打死了黑猫警长的得力干将白猫班长。
吃猫鼠自然是幻想出来的动物,但不怕猫的老鼠确实存在。《我脑子里的不速之客》中就讲述了一个真实案例,只不过这些不怕猫的老鼠并不是胆大,而是被寄生生物操纵的工具。
2000年,英国科学家乔安妮·韦伯斯特(Joanne Webster)率先研究了弓形虫对老鼠的影响。弓形虫是一种寄生虫,已知宿主是猫,但也可以感染包括人在内的许多恒温哺乳动物。正因如此,网络上才会常常见到“弓形虫病——别再让猫背锅了!”一类的辟谣文章。但是,韦伯斯特在小鼠身上发现了更惊人的结果。
她在一个大型户外围栏的四角分别放上了水、猫尿、兔尿和鼠尿,同时让一部分小鼠感染了弓形虫。虽然人、兔子、老鼠都可以携带弓形虫,也可能造成多种症状,甚至改变携带者的性格,但弓形虫只有在猫体内才能繁殖。因此,用一种不是很准确的拟人手法说,为了去往“应许之地”,也就是猫的肠道上皮细胞,弓形虫需要尽快让携带着自己的小鼠接触猫。
这是寄生生物的常见套路,比如最近在抖音上流行的“僵尸蜗牛”视频。正常蜗牛的触角是不起眼的乳白色或淡黄色,但被彩蚴(yòu)吸虫寄生的蜗牛会长着闪烁的彩色触角,在人类看来像是理发店门口的旋转灯柱,在鸟儿看来则像是肥美的毛毛虫。
不仅如此,被寄生蜗牛的行动也会大大加快,用韦伯斯特的话说,相当于“蜗牛奥运选手的速度”。这一切都有利于鸟儿发现并吃掉可怜的宿主,彩蚴吸虫继而会进入鸟儿的肠道,鸟儿排出的粪便会被新的蜗牛吃掉,一个闭环就这样形成了。
回到小鼠围栏实验。基于寄生虫的常见习性,韦伯斯特预计携带弓形虫的小鼠会不那么厌恶猫的尿液。但实验结果发现,感染小鼠平均接触猫尿的次数,比未感染小鼠多将近50%。如果把场景换到一个养着猫的谷仓中,这或许意味着感染小鼠去招惹天敌的可能性要高将近一半,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韦伯斯特在论文中提到,自己所在团队的研究结果“可能从功能角度解释了感染弓形虫的人类的行为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假说,因为早在1980年代,捷克科学家亚洛斯拉夫·弗莱格(Jaroslav Flegr)就怀疑弓形虫病与人类精神分裂症相关。他发现“有些东西在妨碍我保护自己”,比如虽然他会空手道,但受到攻击时也不会反击,甚至明知被店主欺骗也会吃哑巴亏。他告诉麦考利夫:“我估计每年有多达100万例道路交通死亡可以归咎于弓形虫。”
当然,弓形虫病与人类性格的关系是复杂的,也不能把小鼠的“症状”直接推广到人类身上,除非能证明感染弓形虫是人类越来越喜欢猫的原因。换言之,在微观神经层面,弓形虫病仍然是一个“黑箱”。
直到2009年,这个黑箱才被揭开了一角。研究疟疾的英国寄生虫学家格伦·A.麦克柯奇(Glenn A.McConkey)意识到,尽管疟疾的病原体(疟原虫)与弓形虫有亲缘关系,但只有弓形虫对大脑有亲和力。
接着,他对比了两种寄生生物的基因序列,发现弓形虫有一段特殊的基因编码,而这段编码与多巴胺合成有关。多巴胺俗称“快乐激素”,可以让人兴奋和感觉良好。人在品尝美食和享受性爱时,多巴胺水平都会飙升。冰毒的机理正是刺激多巴胺生成。
这或许意味着,感染弓形虫的老鼠不怕猫也好,感染弓形虫的人不怕冲过来的卡车也好,其实都是多巴胺水平高涨的反映。正如麦克柯奇所说:“多巴胺的功能与对受感染老鼠的观察结果如此吻合,我感到很震惊。”两年后,韦伯斯特与麦克柯奇进一步发现,携带寄生虫的神经元产生的多巴胺,是正常状态下的3.5倍。
在追溯从鼠到人的传播链,从弓形虫感染大脑到多巴胺分泌增多的因果链的过程中,有一个隐秘的主题如影随形:操纵。弓形虫是否在“操纵”人的思想与行为?对于这个问题,从《我脑子里的不速之客》的副标题中就能看出麦考利夫的答案:寄生生物如何操纵人类与社会。
正如她在导言中所说:“被我们称作‘自然选择’的奇观,背后往往是寄生生物在指挥行动,影响着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斗争结果。”当然,所谓的“神经寄生虫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人类与寄生虫之间的深层关系早已渗入我们的文化中,即使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
吸血鬼与咖喱
除了吸血以外,吸血鬼的最突出特征之一就是永生。爱尔兰作家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的开创性小说《德古拉》中写道:“当他们变成吸血鬼,对不死的人的诅咒就会发生变化。他们不会死,而是年复一年地增加新的受害者和世界上的邪恶力量。所有的受害者都会变成不死的人,然后继续捕获自己的同胞。所以这个圈子越来越大,就像石头扔进水里形成的涟漪。”
而在吸血鬼传说的发源地罗马尼亚,当地流传的习俗与《德古拉》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不同点。
首先,坟墓中经常会有小火炉、酒杯和食盘。罗马尼亚人类学家米哈伊·费弗尔(Mihayi Fifor)对此的解读是:“从周一到周三,村里的女人会在墓里点三天灯,给死者照点亮。死者感觉冷,怕黑,而且常常又饥又渴。”这与常见的供品不同。摆放供品时,我们完全清楚祖先已经离世了,不会来真的吃掉供品。但是,一周三天点灯送食的女人似乎是把墓中之物当作活人来照顾的。
其次,“死者”变成吸血鬼分为两个阶段。在前40天中,“死者”会在晚上四处游走。但过了40天,他们就可能变成“莫洛伊”(moroi),不管在黑夜还是白天都会发狂咬人。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罗马尼亚人倾向于用神学来解读40天,比如耶稣复活后在世间活动了40天。
但是,在讲述寄生虫对人类影响时,麦考利夫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人被疯狗咬了之后被送入坟墓中,所以要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狂犬病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恰好是40天左右,发病者中有三分之一会在麻痹中缓慢死去,其余会进入狂暴阶段,通常几天后就会死去。
这样说来,吸血鬼就是狂犬病患者,“坟墓”在前40天是隔离所,之后才变成真正的长眠之地。当然,古人不知道的是,狂犬病并非只能通过咬人传播。根据现代研究,早在发狂之前,患者唾液中的病毒就达到了高浓度。
但是,狂犬病患者与吸血鬼还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无药可救。斯托克借吸血鬼猎人范海辛(Van Helsig)之口说道:“但如果吸血鬼真真正正地死了,一切都会停止。”狂犬病也是如此,除非在短暂的窗口期内注射疫苗,否则患者几乎必死无疑。
因此,在1882年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氏消毒法”的发明者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制成狂犬疫苗之前,人类应对狂犬病的手段只有两条:隔离和扑杀。前者就是原始吸血鬼传说中的坟墓,后者就是范海辛的银子弹——当然,现实中的狂犬病患者用任何子弹都可以消灭。
寄生生物与宿主的“军备竞赛”已经持续了上亿年。麦考利夫在《我脑子里的不速之客》中举出了许多个例子:线形虫与蟋蟀、蟹奴与螃蟹、蛇形草属真菌与蚂蚁……正如她所说:“寄生生物惊人的群体规模,令我们相形见绌,而且它们快速的复制率确保了总会有少数占据优势的幸运变异体存活下来。宿主和寄生生物之间的战斗是一场无休止的军备竞赛。”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寄生生物面前束手无策,事实上,我们有许多反制措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发烧。
对恒温动物来说,提升体温需要消耗大量能量。麦考利夫说:“哪怕只是将正常体温调高1摄氏度,所需的热量也相当于普通成年人步行40千米消耗的热量。”因此,发烧时会浑身乏力,也就不奇怪了。
发烧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寄生生物通常对温度非常敏感,比如头虱的最适宜温度区间是29至32摄氏度,超过44摄氏度就会死亡。除了生理机制以外,有证据表明,包括黑猩猩在内的灵长类动物,会自主寻找并传承有驱除寄生生物作用的物质。西非村民常用的豆蔻中含有类似窄谱抗生素的物质,由20多种香料配成的咖喱则被麦考利夫称作“广谱抗菌混合物”。从这种基于经验的医学传统出发,香料逐渐形成了口味的文化偏好。在这个意义上,药食同源的根基之一,正是我们与寄生生物的斗争。
凯瑟琳·麦考利夫曾荣获“最佳美国科学与自然写作奖”。《科学美国人》对《我脑子里的不速之客》的评价是:“作者以生动的笔触深入探索了新兴领域,编织出如此迷人的故事,其中充满了让你迫不及待想分享给别人的趣闻。”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