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屠杀幸存者笔下的谷物与人的历史
一部谷物人文史《了不起的面包》,记录了从农业黎明时代的一粒小麦和小米,到黑麦、燕麦、大麦这些徘徊于口粮、饲料、酿酒原料之间的“杂粮”,再到美洲的馈赠玉米和马铃薯,以及亚洲的主食水稻。在记者兼作家H.E.雅各布(H.E.Jacob)笔下,几乎涵盖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主流或非主流谷物。
贯穿《了不起的面包》的主线,是人与谷物的关系,以及依托于谷物的人际关系。面包构成了古埃及人今生与来世的一条主轴,而对于与面包密切相关的发酵与农耕生活,同期的犹太人则深怀恐惧。在中世纪欧洲,农民、磨坊主、面包师与市民之间有着密切依赖又相互猜疑歧视的别扭关系。如果雅各布来到今天的话,以藜麦为代表的超级谷物与中产生活方式的关系中,他一定不会缺席。
神秘的发酵面团
在前言中,作者解释了自己投入20多年时间研究面包的缘起。粮商叔叔对四五岁的雅各布说:“你只需要研究人类历史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化学、农业、神学,还是经济史、政治和法律,都研究一番。用上二十年搜集资料,然后差不多就可以开始动笔了!”
人与谷物的关系自始至终具有张力与复杂性,从古埃及人与古以色列人对待农耕的态度中就可见一斑。
雅各布说:“埃及全国就像是一个长长的烤炉一样。”这不仅是指古埃及的农业文明属性,更有两个更深层的意涵。首先,古埃及是最早有意识利用空气中的酵母菌来制作饮食的文明发源地之一,也就是说,他们会制作发面饼和啤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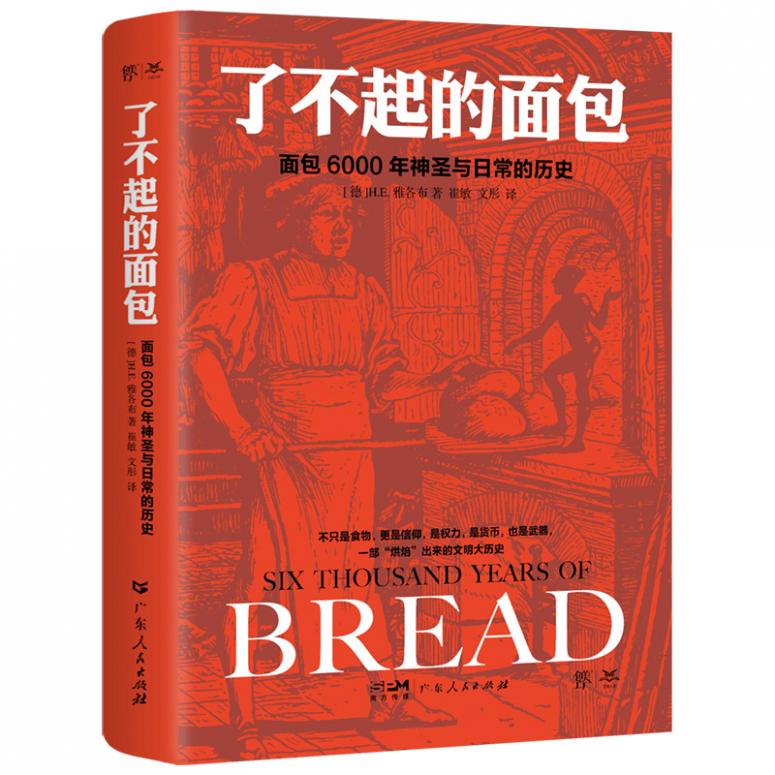
《了不起的面包:面包6000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
古埃及人自称chemt,意为“黑土的子民”,指的是尼罗河退潮后留下的富含矿物质和有机质的肥沃黑土。周边民族对他们的一个称呼则更直接——“吃面包的人”。古罗马人的传统主食是麦粥,古希腊人吃的是炭火烤的煎饼,日耳曼人吃的是去壳的燕麦粒,而5000年前古埃及人口中的面包的制作方法已经和今天相差无几了。磨粉,揉面团,放置在空气中或利用“老面头”发酵,最后放进砖制的烤炉。据雅各布说,埃及人开发出了50款不同的面包。对古埃及人来说,最大的奥秘或许不在天上或死后,而就在尼罗河的涨落和面团的涨发之中。
除了物质生活外,面包在古埃及人的文化与精神世界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古埃及圣书体中有一个字母写作,形如饱满的面饼,读作t。而在埃及人视死如归的传统中,亡灵必须得到娱乐和供养,所以面包和面包房会出现在墓穴壁画中也就不奇怪了。
不仅如此,大名鼎鼎的《亡灵书》中也不乏面包的身影。与电影《木乃伊归来》中能够复活死者、制造骷髅大军的黑色魔法书不同,《亡灵书》其实是一部冥界生存与通行手册。亡灵填饱肚子的需求,不亚于拿着旅游杂志《孤独星球》在异国小镇觅食的游客。比如,《亡灵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面包在天上由太阳神保管,在地上由大地之神克卜保管。夜船和日船,会从太阳神处,将我要吃的面包送来。”
与尼罗河和金字塔一样,面包定义了古埃及的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埃及人对围绕耕耘和面包展开的生活完全满意。有一首歌谣写道:“从种出粮食,到磨成面粉,难道就不能让我们休息一下吗?粮仓都这么满了,谷物堆到溢出来了。”懂得农业是史上最大骗局的人,不止有《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古埃及人自己就有切身体会。赫拉利的祖先以色列人更是清晰有力地表达了同样的态度。
《出埃及记》中写道:“这七日(逾越节)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由此而论,面包似乎成为了奴役的代名词。相比于吃面包,爱面包,甚至以面包为货币的埃及人,以及曾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都对面包有着矛盾的感情。
一方面,犹太人在纪念脱离埃及的逾越节期间都不会食用发酵饼,献祭时也绝不会使用发酵饼;另一方面,美味的烤制发酵面团早已成为犹太人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风靡东地中海各民族的口袋饼(pita)。
但不可用发酵饼敬神的传统,要比离开“奴役之家”更加遥远,其根源是认为发酵等于腐败。事实上,中国人厌恶蓝纹奶酪,西方人吃不惯臭豆腐,道理也是相通的。只是在祛魅的时代,我们倾向于用卫生的话语来包装自发的生理厌恶,而远古人倾向于用祭祀和禁忌的语言来表达。
除此之外,对以放牧为业的古犹太人来说,终生不出田间地头的农耕生活,无疑形同监牢。或许《创世记》中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后受到的告诫,就蕴含着对农耕生活的恐惧,甚至可以说是对农民的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调包的磨坊主与偷面团的面包师
面包不仅能够区分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生活方式,甚至能够在工序的上下游之间创造出鄙视链乃至仇视链。
中世纪欧洲市民的主食是面包,而制作面包首先需要种植小麦,然后将麦粒磨成面粉,最后送到面包房烤制。农民、磨坊主、面包师、市民被生存的必要性拴在同一个链条上,而且几乎每天都要打交道。
那么按照常理,他们理应形成牢固而天然的纽带。但中世纪的情况是:农民痛恨磨坊主,面包师看不起磨坊主,市民则将饿肚子归罪于磨坊主和面包师。
从公元4世纪开始,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伦巴底人、法兰克人等“蛮族”纷纷迁入罗马帝国境内,并逐步反客为主,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秩序,史称“民族大迁徙”。欧洲的新主人们不仅占有了都市与财富,还发现了一种神秘的设施——水磨。

按照日耳曼人的信仰,水磨是奴役了溪流的魔鬼。同理,后来兴起于英格兰、荷兰等欧洲北部地区的风车,也承担着同样的恶名。直到13世纪,意大利大诗人但丁还在《神曲·地狱篇》中用风车的形象来描绘碾碎灵魂的魔鬼:“头有三个面孔……每个面孔以下生了两只大翅膀,适合于大鸟的飞扬……不过翅膀上面并不长着羽毛,只是和蝙蝠的一样质地,鼓翼生风,风吹三面。”
但是,如今遍及欧洲的蛮族很快就认识到了磨坊的用处和重要性,磨坊甚至成为了许多村庄的核心。讽刺的是,随着磨坊地位的提升,磨坊主的地位却下降了。土地与磨坊一起成为了领主的财产,磨坊主成为了掌握核心技术的技师。同时,为了保护自身的产业价值,领主又普遍赋予现有磨坊垄断权利,要求下属的所有农民只能将粮食送给指定的磨坊,并禁止建立新的磨坊。
既具有外人无法理解的强大力量,但又不属于统治阶层的人,向来是恐惧和嘲弄的对象。读者不妨看一下奇幻电视剧《权力的游戏》中火术士的形象,他们制造的燃烧弹“野火”可以顷刻间毁灭数百艘战舰,自身却被描绘为佝偻着身子、肮脏龌龊、毫无道德底线的贱民。
当然,除此之外,磨坊主中饱私囊的行为确实存在,比如用细砂调包磨好的面粉。上至君王贵妇,下至贩夫走卒,都对捉弄恶磨坊主的故事津津乐道。在14世纪英国作家乔叟的名著《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磨坊主的女儿甚至因为父亲的狡诈吝啬而失去了贞节。
面包师与磨坊主的矛盾,则缘于空间的隔绝。磨坊主住在乡下,面包师住在城里。在古罗马和现代世界,市民都以开阔的视野自诩,相信并切身感受着自己是宏大天地的一员。而在罗马秩序崩溃、连公爵出城旅行都会被打劫的中世纪,墙内的城市更像是堡垒乃至监狱。
正如雅各布所说:“在人为局限于封闭式小镇经济的市民当中,产生出一种奇怪的地方自豪感,一种对小镇狭隘的热爱。”城墙隔开了本应联系密切的磨坊与面包房,也制造了磨坊主与面包房的隔阂。
在城墙之内,行会制度与细密的行规,同样离间了面包师与购买面包的人。在行会制度的束缚性保护下,面包师是一份辛苦但无法被剥夺、免于竞争、只需按照规定方法操作的终身职业。正如农民不信任磨坊主一样,市民也猜忌着面包师。
雪上加霜的是,大众不理解面包价格是会波动的,将面包变贵一概归咎于面包师漫天要价,并惩罚不诚实的面包师,比如深受伦敦人民喜爱的颈手枷。一名19世纪英国作家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中世纪面包师:“面包师确实熟练而巧妙地在烘烤房的桌子上开了一个洞……面包师的一个亲戚会藏在桌底,小心翼翼地从下面打开那个洞,一点一点、一块一块地,巧妙地偷走部分面团。”
在中世纪之后,《了不起的面包》继续探讨了源于美洲的玉米与马铃薯,19世纪的化肥、农业机械与大宗粮食买卖,最后来到战乱频仍、环境危机初现的20世纪上半叶。在全书的末尾,作者动情地写道:“我还活着,还能吃到真正的面包,这对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这句话源于他的个人经历。
作为一名出生于德国柏林的犹太人,雅各布在1938年3月德奥合并后被纳粹政权逮捕,先后关押在臭名昭著的达豪(Dachau)和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在布痕瓦尔德,我们根本没有真正的面包;所谓的面包是土豆粉、豌豆和锯末的混合物。面包芯的颜色像铅一样,外皮和口感都像铁一样……然而,我们还是把它叫做面包,为的是纪念我们以前吃过的真正的面包。”
在女友的努力援救下,雅各布于1939年1月获释,随后流亡美国,用德语创作了《了不起的面包》一书,1944年英文版面世。正如美国传奇面包师、《学徒面包师》作者彼得·莱因哈特(Peter Reinhardt)所说:“这本书并不会教你如何制作面包,这是一本关于面包作为个人和历史变革的象征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