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讲述西方情报合作机构50年历程
五眼联盟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组成的国际情报共享团体,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建立的特殊关系。二战后,尽管各成员国的政治、国防与情报制度都发生过巨大的变化,但五眼联盟的情报合作不曾中断。
英国情报学专家、曾在英美情报机构工作50年的安东尼·韦尔斯(Anthony Wells),在《五眼联盟》一书中追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讲述了自己亲眼见证的五眼联盟,并给出了自己的反思与新技术格局下的展望。
英国皇家海军上将艾伦·韦斯特(Allan West)在推荐序中写道:“我想不出有谁比他更适合解读其中的复杂关系以及‘五眼联盟’形成以来的发展状况。”
一部第三人称的回忆录
相比于英国军情六处(MI6)、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等情报机关,“五眼联盟”(Five Eyes)的知名度并不高。五眼联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英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的“特殊关系”,标志是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北部纽芬兰(Newfoundland)的会面,此次会面的主要成果就是著名的《大西洋宪章》。两国的情报合作关系延续到了战后,跨越冷战,一直到今天。
韦尔斯1968年开始在剑桥大学教授、情报史研究者哈里·欣斯利(Harry Hinsley)指导下研究情报学,从此开始了长达50年的情报生涯,直到2018年退休。自1972年出任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讲师一职以来,他便频繁参与英美两国的情报与学术活动,并于1983年加入美国国籍,从此将活动重心转移到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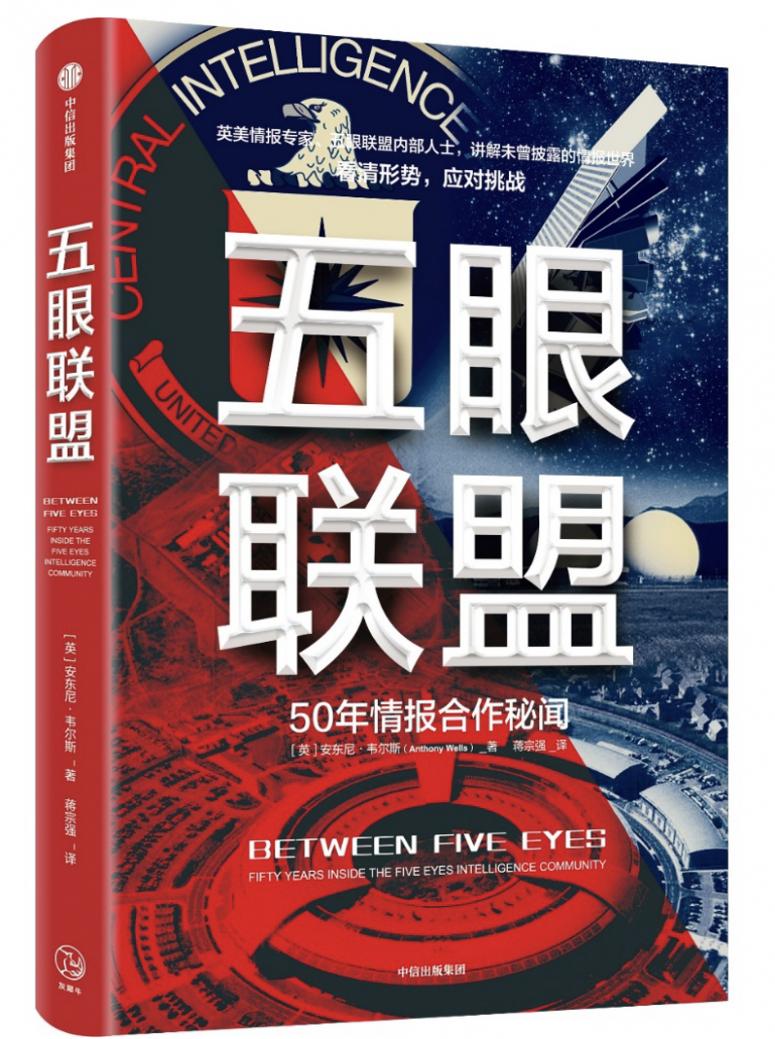
《五眼联盟:50年情报合作秘闻》
作为一部“没有违反美国、英国或五眼联盟其他成员国情报组织的任何安全法规或程序”的著作,《五眼联盟》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公开出版物以及作者本人收藏的大量非机密信息。
曾任英国海军舰队总司令和安全部长的英国皇家海军上将艾伦·韦斯特,为《五眼联盟》撰写了推荐序,称该书“是对五眼联盟较为详尽的介绍”。事实上,无论从本书涵盖内容还是编写体例来看,《五眼联盟》既不是一本以讲故事为宗旨的大众社科类读物,也不是专注于史实细节的学术研究,而更像是一本内部资深亲历者的回忆录。
不过,与许多沉湎于过去的辉煌业绩,或者竭力为自己开脱,甚至不惜甩锅给同僚的人不同,韦尔斯采取了一种更为超脱的姿态。似乎他只是一条不起眼的线索,串起了五眼联盟半个多世纪的历程。
这一点,从划分章节的时间节点中就可见一斑。全书共分为七章,除了以展望未来为主题的最后一章外,其余六章皆有对应的时间段,共涉及7个年份(时间段并非严格的前后相继)。
他是在世的唯一一位曾以英国公民身份为英国情报机关工作,又以美国公民身份为美国情报机构工作的人。除了没有明确意义的1990年、“9·11”事件发生的2001年以外,其余年份都对应作者本人职业生涯中的里程碑。
如前所述,1968年是韦尔斯与情报界结缘的年份。1974年,他开始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漫长课程”,也就是辗转于各类船只和岗位的专业培训课程,类似于医生的轮岗培训。1978年,韦尔斯从英国回到美国,次年开始与多个英美情报机构合作。1983年,他正式加入美国国籍。他2018年退休,现居美国弗吉尼亚州。
但以回忆录的标准来衡量,《五眼联盟》又有大量表面上与作者本人经历,甚至与五眼联盟没有直接关联的宏观观察与反思。以第三章为例,这一章的题目是“政治变革和国防架构变革”,介绍了英国国防体制在“二战”后的总体性变化,其核心是建立自上而下的集中化管理模式,强化原本相互独立的军种之间的协调关系,但也造成了官僚化和海军政治影响力下降等弊端。
接下来,作者将英国与美国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并将原因追溯到美国行政与立法分立的政治制度。作者马上指出,尽管英美两国的政治体制都发生了大幅变动,但五眼联盟留存并持续发展壮大,其原因在于“各种正式的法律协议以及外交交流只是‘五眼联盟’成员国关系的外在表现,而这种关系的核心和灵魂其实在于各国建立起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持久的私人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美两国情报合作的关系一帆风顺。
作为亲历者,韦尔斯目睹了美国情报界在1970年代的“自满”状态,也不得不采取“谨慎圆滑的外交风格”,以说服美国同行实施针对苏联的切实行动。作者随后说:“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不仅在个人层面和职业层面改变了我,还改变了我的生活和家庭,也是我在移民美国37年后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他没有说明,“一件事”到底是什么事。
除此之外,作者在第三章中的个人出场并不多,而且有时是以“我们”的口吻在说话。这想必与保密政策有关,但更主要的因素可能在于韦尔斯的写作目的。毕竟,如果作者愿意的话,他可以填入无数不涉密的细枝末节与趣闻轶事,轻松将书的篇幅扩充到两倍以上。
老把戏与新科技
韦尔斯用大量篇幅,说明了情报部门使用的技术。冷战期间,五眼联盟的一项重大成就是针对核潜艇的声学情报搜集。
在航行过程中,核潜艇会发出噪声。噪声的一大来源是螺旋桨等机械部件,另一大来源是海水经过潜艇上方的围壳时产生的湍流噪声。为了减少潜艇被发现和打击的可能性,消音是潜艇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军事杂志上也常会出现“某某型潜艇的噪声水平为100分贝”之类的说法。但对于需要追踪和监控敌方核潜艇数量与型号的情报机构来说,更重要的是每一级、每一艘潜艇的关键缺陷及其产生的噪声特征。韦尔斯称之为“潜艇的DNA”。英美以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潜艇也参与了这种任务,并且延续到了冷战之后。
另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当代议题,是信息安全。依靠卫星网络、陆地线路和海底电缆,英美及其主要盟国在全球数字通信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正如韦尔斯所说:“五眼联盟的每个成员国都拥有拦截内部通信的技术和组织能力。”即使一个美国人从家里给另一个美国人发出一条信息,这条信息也可能会通过其他国家的服务器和路由器,从而被拦截和监控。同理适用于其他所有国家的互联网通信。
换句话说,国内通信与国际通信的区别非常微妙。一方面,国内窃听成为了西方国家的一个公共议题,比如2013年的棱镜门事件(PRISM)。棱镜计划是美国国家安全局与联邦调查局于2007年启动的秘密监控项目,可以直接进入微软、雅虎、谷歌、脸书、苹果等公司的中心服务器挖掘数据。
站在情报机构的立场上,韦尔斯将棱镜计划爆料者、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职员斯诺登(Edward Joseph Snowden)视为“内部背叛行为”,并以此为例呼吁建立一套新的风险管理系统。“当另一个斯诺登开始访问高度机密的数据,试图将其下载到拇指存储器时,这套新的风险管理系统不仅会立即发出预警,追踪和询问这些行为,还会从一开始就动用最严格的人工智能应用阻止此人访问。”
另一方面,为了应对信息安全议题,多国政府推出了更严格的法规来保护公民的隐私。例如,英国政府2016年出台了《调查权力法案》,禁止大规模搜罗公民元数据。2018年,欧盟开始实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保护欧盟公民免受网络攻击。但正如韦尔斯所说,五眼联盟的情报机构一直能够“合法”地获取一国公民通过他国媒介发出的信息。信息安全法规或许对情报机构构成了一定的妨碍,但与如何利用拦截到的海量数据相比,那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Anthony R.Wells
但是,在第六章“情报角色、任务和行动(1990—2018年)”中,韦尔斯抛出了一个问题:“当下的技术进步确实改变了情报搜集的硬件设备,但在当代技术变革的喧嚣中,过去种种挑战及创新都消失了吗?”对于这个问题,韦尔斯在两个层面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在直接层面上,信息技术的发展会迫使犯罪团伙和外国情报机构转向手机、电子邮件以外的传统联络方式,比如传口信。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在互联网和蜂窝网络普及之后才出现的新问题。
早在18世纪初,英国女王安妮(Anne)就在一封写给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的信中说,她“害怕有意外发生”,所以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给他写信,而是选择利用贴身侍女探望父亲的机会给公爵传信。马尔伯勒公爵是“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先祖,当时正在欧洲大陆指挥大军对抗法国。
在间接层面上,韦尔斯主张:“解决技术问题的核心在于人!”他承认技术采购在情报工作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但也认为政府在技术开发和采购方面的迟钝缓慢“令人感到悲哀”。为此,开放式的项目小组配合严密的分隔措施,有望同时提高效率与安全性。在第四章的末尾,韦尔斯举出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1990年代美国太平洋第3舰队自行推动变革方案。
尽管韦尔斯说,“情报界不应该制定政策,也不应该影响重大战略的制定”,但这并不是假装政治不存在的鸵鸟态度。恰恰相反,他对英美政治变革的比较、对苏联政治体制的分析,以及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政治思考都表明,他很清楚政治与情报工作的互动关系。
此外,他强调情报机构应该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采取行动,这些原因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利益和五眼联盟的集体利益。这无疑是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之一。至于这些重大的利益是什么,韦尔斯没有置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