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由人类策划的反人类行为
卢旺达总统出国访问期间,1994年4月6日,座机被击中,与多名政要一起丧命。短短几天后,一场持续100多天的大屠杀开始了,联合国将此次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
法国作家让·哈茨菲尔德(Jean Hatzfeld)的“卢旺达三部曲”,分别记录了幸存者、屠杀者、屠杀后重建过程中的一手资料,连缀起一个个故事,而又尽可能保留了原初口述的力量。在沼泽地中遭到重击后侥幸不死的女子;迅速学会用砍香蕉的手法杀人的农民;驱散求救民众的镇长;开起网吧的中年阿姨……在哈茨菲尔德笔下,这些人物不能简化为鲜明的形象或画面。
正如《卫报》所说,“哈茨菲尔德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尝试理解——至少是更好地理解——那些人类无法理解的东西。”
我们不能把心掏给外国人看
《与屠刀为邻》是法国记者让·哈茨菲尔德三部作品的合订本,这三部作品即2000年出版的《赤裸生命》、2003年出版的《屠刀一季》、2007年出版的《羚羊战略》。三部作品都是当事人讲述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受访者均来自卢旺达南部小镇尼亚马塔(Nyamata)。
《赤裸生命》和《屠刀一季》,分别请受害者与屠杀者讲述了屠杀的过程;《羚羊战略》则相当于后传或重访,聚焦于当事人重新建立生活的努力。
卢旺达是东非国家,生活着三大族群:胡图族、图西族和特瓦族。胡图族务农,图西族放牧,特瓦族栖身于密林之中。卢旺达原本由本土国王统治,19世纪末沦为德国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转入比利时手中,直到1962年独立。
卢旺达西部位于东非大裂谷之上,以高原为主,与刚果民主共和国隔基伍湖(Lake Kivu)相望。东部是全球闻名的卡盖拉国家公园(Akagera National Park),山峦起伏,有“千丘之国”的美誉,生活着众多野生动物,尤其是有多达12种羚羊。首都基加利(Kigali)位于国土正中,距离尼亚马塔约30千米。尼亚马塔镇附近有一片树林,东北方和西方有大片纸莎草沼泽。在1994年4月11日至5月14日,树林和沼泽成为了屠杀者的“狩猎场”。
在战争中,哪怕是实力悬殊的游击战或不对称战争,双方总是有来有往,相互警惕,卢旺达大屠杀则是一场有组织的猎杀。胡图族民兵和平民每天上午九点半分成小组上山,搜杀图西族,下午四点收工。如此周而复始,一直持续了30多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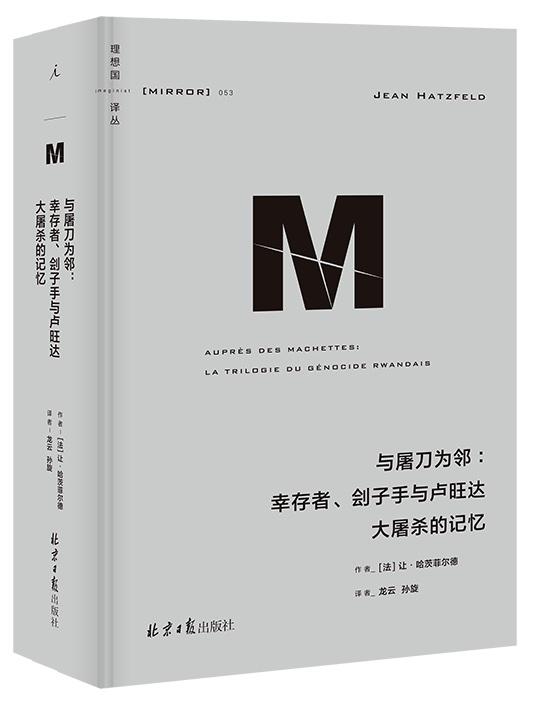
《与屠刀为邻:幸存者、刽子手与卢旺达大屠杀的记忆》
大屠杀结束后,哈茨菲尔德来到了卢旺达。但是,本书的大部分资料来自1997年之后。当时,他第二次来到尼亚马塔,逗留了好几个月,与熟人介绍的屠杀幸存者聊天,整理后即成《赤裸生命》。每一节为一个主题,采用相同的格式,先是作者的简短背景介绍,然后是一名或几名幸存者的发言实录。
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视角,说明评论与直陈叙述的周期性变换中,读者在任何一位幸存者身上停留的时间都不会太长,有充分的机会体会那段惨痛经历的各个侧面。事实上,尽管《赤裸生命》完全是幸存者的声音,却绝不单调,以至于读完后几乎无法概括,勉强提取出一些共同的“要素”也只能是干瘪而不真诚的,对于这样一个主题是完全不适当的。
受访者对访谈本身的反思值得注意。哈茨菲尔德进行采访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尼亚马塔主干道上的小酒馆,开朗体贴的酒馆老板娘玛丽-路易·卡戈伊雷(Marie-Louise Kagoyire)经常听顾客讲述自己是如何活下来的,也因此对两种谈话有着深切的认识。
老板娘说:“幸存者会不厌其烦地讨论大屠杀之后的局面。我们互相讲述一些难忘的时刻,分析原因,互相逗乐……但是,要把我们的心掏给一个外国人看,谈论我们的感受,袒露作为幸存者的感受,这让我们很反感,无法接受。”
另一位幸存者也说,自己与外国人交谈时自然可以说一些“漂亮话”。但是,他们明明与哈茨菲尔德说了很多话,而且肯定还有更多话没有形诸文字。
我不想政府门前血流成河
《屠刀一季》的采访对象,转向了当年参与屠杀的胡图族平民和民兵。大屠杀开始后,图西族在邻国乌干达建立的卢旺达爱国阵线,立即向国内发起反攻,7月4日夺取首都基加利。同月,大批胡图族难民进入西侧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年11月,爱国阵线攻入刚果民主共和国,推翻该国政权,胡图族难民大多返回国内。在尼亚马塔犯下罪行的胡图族杀手被判刑,关押于镇子东北方向的里利马(Rilima)监狱。
与《赤裸生命》中个别访谈幸存者的形式不同,《屠刀一季》的访谈对象是一个监狱中的小团体,行文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每一节仍然选择一个主题,但不再是一个或几个访谈者的大段独白,而是有些像小组讨论。哈茨菲尔德的角色类似于讨论课教师,确定好主题后向访谈者抛出问题,然后访谈者给出回答。哈茨菲尔德的访谈都是单独进行的,并且保证不会将谈话内容泄露给外界或团体成员,除非有疑难问题需要大家当面确认。
哈茨菲尔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屠杀者比幸存者面临的压力更大,总体上也更不诚实。如果不能预先取得信任的话,访谈者必然一无所获。在这种情况下,先通过物质奖励和保密承诺说服小团体的首领,然后通过首领与团体成员建立关系就成为了一种可行的方式。当然,团体成员平时有很多交流机会。
尽管由于保密措施,他们无法在具体问题上“串供”,但在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说、什么样的事情决不能说一类的原则性问题上,他们无疑是有过沟通的。哈茨菲尔德对访谈者的戒备也是心知肚明。在访谈过程中,他逐渐摸索出了一些小窍门,比如在提问时用“你们”代替“你”,会得到更充实的回答。但作者也不无遗憾地承认:“当聊到一些非常私密的话题时……我总在等待一个彼此更具默契的时刻,这个时刻通常出现在会面的尾声,因为那时我们已经相熟起来。”
哈茨菲尔德发现,屠杀者在讲述时相当平静,与幸存者大不相同。作者从口气和用词方面做了分析。幸存者会用鲜明精确、来源于自身生活中的词汇,而屠杀者倾向于讲平淡的官样文章,试图将屠杀与战争搭上关系。当然,中译本读者看到的文本已经是经过多次转手的产物:最初是原始录音,然后是两名当地译者将访谈者使用的土语“非常精细而忠实”地转述出来,形成书面法语的文本,最后转换为书面中文。如果说世上果真有不可翻译的内容,这应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吧。
尽管如此,中文读者仍然能够透过多重面纱,窥见幸存者与屠杀者迥异的心理状态。此外,对比阅读也能颇有收获,甚至发掘出一些隐藏在直接访谈对象外的阴影人物,比如尼亚马塔镇长。
参与屠杀的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说:“4月10日,西装皱皱的镇长和所有官员把我们胡图族屠杀者聚集起来,训诫我们,还提前威胁把事情搞砸的人……唯一的规定就是要坚持到最后一刻……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人,以及掠夺我们发现的东西。完全没法糊弄过去。”
而在《赤裸生命》中,幸存者伊诺桑·鲁维利利扎(Innocent Rwililiza)写道:“4月11日上午……我们图西族人聚集在院子里,等待政府的保护声明,等了两个小时。镇长穿着蓝色的正装出来了,对我们宣布:‘如果你们回到家里,他们会杀掉你们;如果你们逃到灌木丛中,他们会杀掉你们;如果你们待在这儿,他们也会杀掉你们。不过你们得离开这儿,我可不想政府门前血流成河。’”
还有问题吗?
克洛迪娜·卡伊泰西(Claudine Kayitesi)是一名死里逃生的图西族少女,上次接受哈茨菲尔德采访时住在表姐家,养育家里的十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她当时说:“我不是说今后一定不会结婚,但哪个男人愿意把他的钱用来抚育这些住在我家的孤儿呢?”两年后,当作者再次采访她时,她已经和小学同学结婚,一起搬到外地居住。见到哈茨菲尔德时,她问道:“还有问题吗?还是关于屠杀。您没完没了了呀。”
到了为《羚羊战略》准备素材的时候,执政党卢旺达爱国阵线已于2003年1月13日颁布赦免大屠杀罪犯的命令,释放了大部分囚犯,推行和解政策。屠杀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伤痕依旧清晰可见。
事实上,尼亚马塔村镇正是1959年图西族遭到屠杀的产物,当时难民一路从卢旺达北方逃到了南方。仅仅4年后,他们再次遭到了胡图族政府和军队的大规模进攻。但从1973年大批贫困胡图族人来到尼亚马塔开垦以来,两族保持了20年的表面和平,直到大屠杀发生。相比于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分子,胡图族杀手有一项重大优势:长年的共同生活让他们对谁是图西人,谁是同情图西人的胡图族了如指掌。
难怪克洛迪娜会说自己遭到了生活的“背叛”。囚犯被释放后,大部分人没有能力离开,于是胡图族与图西族回到了比邻而居的状态,但哪怕当年的表面和谐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正如伊诺桑所说:“和解是信任的共享。和解政策是公平地共享怀疑。”
在和解政策之下,公开发泄对胡图族的愤怒会遭到政府训诫。事实上,尽管胡图族人还会在酒馆里聊起当年的惨痛经历,以此排解疗伤,但大多数人都将精力投入到了新的生活中。有人像克洛迪娜一样喜结连理,有人开起了尼亚马塔第一家网吧,也有人放弃了护士和教师的理想。最有戏剧性的一章,当数图西族少女与胡图族杀手的恋情,两位新人和一位知情人分别给出了两个“互相补充,互相矛盾,隐藏着难解的谜团”的版本。
《与屠刀为邻》出版后屡获殊荣,包括2000年法国文化广播电台文学奖、2006年英国言论自由奖、2007年法国美第奇文学奖。《纽约客》杂志称赞哈茨菲尔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法国作家之一”。《出版人周刊》评论道:“若是在别人手中,当事人的讲述可能只是一些零散收集的故事,但哈茨菲尔德把这些故事汇集起来,赋予它们力量,迫使人们对这个时代的种族灭绝做出积极的回应。”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