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灾难到文明过程中的个人命运
美国历史学家康拉德·H.雅劳施(Konrad H.Jarausch)2018年的作品《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基于70多部自传与回忆录,描绘了德国普通人从1920年代到1990年代的生活图景。
对德国乃至全世界来说,20世纪都是一个变化无常的年代。尽管频频被战争与其他灾难打断,各个阶层、各个地域的男女德国人依然在挣扎着过上“正常”的生活,直到退休后才有回首人生的闲暇与意愿。在个人奋斗史的字里行间,我们也能看到内心斗争与有意无意的回避,尤其是如何面对自己在第三帝国时期的角色。
在断裂中追寻连续的人生
20世纪的德国与德国人,经历了一连串灾难性的事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始于1789年,终于1914年的“长19世纪”的尾声,20世纪前十年表面上延续着工业革命促成的技术与经济进步,为德国人民带来了持续进步的希望。但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创了德国的社会结构与传统权威。
1919年建立的魏玛共和国,虽勉力维持局面,却还是在横扫全球的大萧条中让位于崛起的纳粹势力,紧接着又是更加阴暗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德国先是被分区占领,然后又一分为二,形成了地域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对立格局,直到1990年两德统一。
从帝国变成共和国,从共和国变成独裁政权,又分裂成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在1914年至1990年的76年之间,德国历史的连续性似乎只在于不断的断裂与分裂。同时期的德国人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而这正是美籍德裔历史学家康拉德·H.雅劳施在《破碎的生活》一书中叙述、梳理和分析的主题。
雅劳施的素材,是70多部生于1920年代的德国人的自传与回忆录,涵盖了从上层中产阶级到劳工阶级的各个社会层级。这些一手材料不仅是第一人称的事件讲述,而且正如本书作者所说:“是为了弥合破碎的记忆而付出的叙事努力,一边是将自己标榜为受害者来脱罪,一边是自我批判式地承认对罪行负责,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这些材料大多撰写于晚年退休岁月,部分原因在于“二战”后的德国人埋首于个人关系与职业生涯的重建,无暇回望早年的动荡时光。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一种历史断裂之外的连续性。普通人总有一种追求正常生活,按部就班从童年走向晚年的趋向,尽管反复被超越个人的力量所裹挟和打断。埃迪特·舍夫斯基(Edith Schöffski)的人生际遇,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1928年,埃迪特出生于柏林的一个贫苦家庭。按照当时女性的正常生活轨迹,她要从小照顾弟弟妹妹,在女校学习基础读写算术和持家技能,毕业后恋爱工作,25岁左右结婚,回归家庭,相夫教子,度过平淡的一生。但战争的到来打乱了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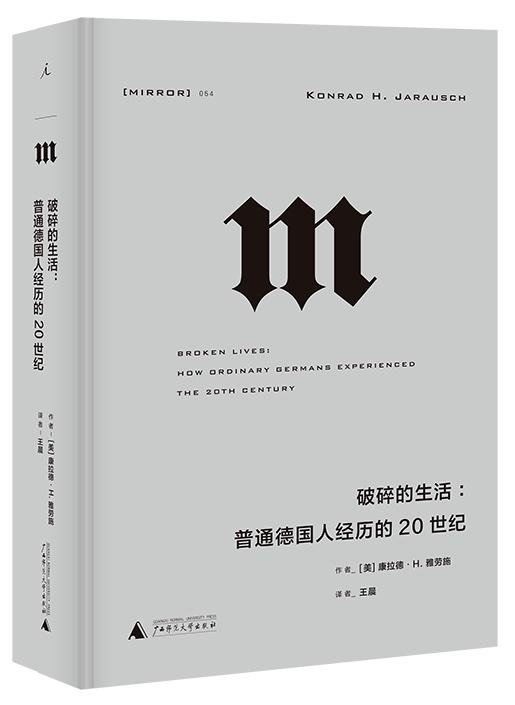
《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
1943年,随着德国战事每况愈下,女性不得不顶替原本男性的岗位。埃迪特先在一家银行的总部做记账工作,总部大楼在空袭中被毁后又转到中央电话局,成了一名接线员。战争末期,她与200万德国妇女一样惨遭强奸。在战争结束后的混乱与贫困中,埃迪特没有获得追求阶层上升与个人理想的机会,成为了一名售货员,并与一名难民建立了家庭。
但在晚年的回忆中,她没有像许多同龄女性一样将重点放在丈夫、家庭和子女上。她津津乐道于自己在平凡岗位上做出的成绩,诉说着看到一间美好公寓时的激动心情。
战争为十几岁的埃迪特带来了无可预料的变数,也留下了无法修复的心理创痛,而她的经历恰恰彰显了人类的适应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埃迪特在战后回归了预定的轨道,战争仿佛是一个痛苦的干扰变量。其他一些自传中同样能看到不绝如缕的连续性,比如子承父业的护林员、商人、医生。
更微妙的连续性则体现在个人思想、恋爱关系、家庭关系的动态变化中。每个人仿佛是多条连续曲线的集合体,历史上的重大节点“晕开”乃至隐匿于延绵的生命溪流中。同时,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节点又凸显了出来,比如德国犹太人在美国移民官面前改掉名字的日子,比如中产阶级男孩抛弃门第观念,在战争中与工人阶级女孩结婚的日子,又比如女孩开心地加入德国少女联盟的日子。
被蒙蔽的青少年
德国少女联盟成立于1933年,所有14岁的德国女孩都有义务加入,1944年时成员规模达到450万,1945年解散。在文化作品中,少女联盟成员常常被描述为战争的受害者。
2004年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中,有头戴钢盔、梳着两条长长的麦穗辫子的女孩英格·东布罗夫斯基(Inge Dombrowski)。当时,苏军已经攻入柏林,英格和四名少年、四名临时拉来的民兵、一名从未上过战场的年轻军官“守卫”一处街垒。当一名老兵告诉他们,“等到俄国人来到时,你们只能抵抗五分钟”时,面无表情的英格坚定地回答,“我们向元首宣过誓的。”显然,这些无知的年轻人是被愚弄和欺骗的对象,是待宰的羔羊,是无辜的牺牲品。
但是,通过解读当事人的回忆,《破碎的生活》揭示了德国年轻人在战争中扮演的更复杂角色,包括看似无害的少女联盟成员。正如雅劳施所说:“在民族主义家庭、纳粹化的学校和希特勒青年团思想灌输的共同影响下,大多数人成了纳粹镇压和侵略的顺从工具。”
尽管在第三帝国的高压统治之下,任何公开抵抗行为都会立即遭到压制,但同时也在通过柔性手段控制年轻人。1920年代以来,德国兴起了一场青年自治运动,提倡青少年建立自己的组织,摆脱家庭、社会与成年人的压抑控制,开展郊游、聚会、歌舞等活动。纳粹上台后将这些社团整合为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联盟,分别招收男性和女性。
尽管集体行军与意识形态灌输令许多青少年厌倦乃至暗自痛恨,但这些组织举办的朗诵、歌咏、远足活动仍然颇具吸引力,尤其是有组织的野营活动。小伙子们伴着鼓声与旗帜穿行于祖国的山山水水,在篝火旁高唱优美的传统歌曲。
1923年,卡尔·黑特尔(Karl Härtel)出生于布雷斯劳(二战后划归波兰,今称弗罗茨瓦夫)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在他的回忆中,野营创造了“一种与我们民族早已逝去的老一辈人真正交融的感觉”。
事实上,在当事人的回忆中,少年时代参加组织是愉快的,与家庭的狭小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稚嫩的心灵打开了全新的领域与可能性。简言之,纳粹当局为青少年精心构造了一个“正常童年”的虚假世界,作为灌输其反人类意识形态的工具。哪怕真诚信服的青少年未必很多,但正如雅劳施所说,大多数人“很难清楚地区分这些新掌权者明显的成功与可恶的强迫”。
因此,青少年确实是被蒙蔽和欺骗了,但不仅仅是在战争陷入绝望的最后阶段,也不完全是因为被“洗脑”。这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从纳粹掌权到二战结束,持续了十多年。更重要的是,德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的感受是复杂的,“从孩子般的热情到厌恶和疏离,无所不包。”不论是人们对正常生活的本能追求,还是当局对这种正常追求的操弄,都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政权之一的基底。私人史恰好擅长发掘这些具有普遍乃至永恒意义的精微教益。
战后的回忆与反思
对自传作者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生断裂的起点,努力重建生活的过程直到战后数年乃至十多年后才完成。大部分普通公民不愿反思自己在第三帝国中扮演的角色,而是将精力投入到寻找食物与住所,恢复学业或工作生涯之中。
战后德国的大片土地沦为废墟焦土,雇主少而求职者众,所以德国人在1945年之后直到1950年代都不得不努力求生。德国战败后,大约1000万国防军成员沦为战俘,分别由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战胜国关押或强迫从事劳动,最晚有人1955年才被释放。漫长的战俘生涯令许多人愤愤不平,比如前面提到的卡尔·黑特尔就抱怨道:“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受到被监禁的待遇,而其他人却在家里大摇大摆,尽情享受生活,也许还嘲笑我们。”对于惨遭纳粹荼毒的国家与人民来说,这是罪有应得,也是将功补过。
留在国内的女性不得不承担重体力劳动,在黑市上为家人获取稀缺的物资。例如,1926年出生于柏林的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的姐姐说:“父亲不在的一年半里……母亲……坐在市郊火车的车顶上前往乡下,带回一把土豆、一个卷心菜或一纸袋皱巴巴的冬季苹果。”此外,女性也成为了重建家庭与社区纽带的主要力量。由此,雅劳施将战后德国的混乱岁月称为“女性时刻”。
自传作者们大多将这段时期描述成一个克服逆境的过程。男人努力工作,建立了新的成功事业,笔下充斥着升职、盖房和买车。女人叙事多以家庭和个人关系为主轴,不管具体的态度是厌恶家庭束缚,还是婚姻美满。总之,“私人化”成为了普通人战后回忆的主轴。直到1980年代陆续退休以来,历经沧桑的德国老人们才开始回首自己的过去,尤其是将年轻时的错误与成熟后的批判进行对照。这不仅是自我揭露,也是记忆的提取与重塑,见证了被迫调和愉快记忆与灾难性后果的心理痛楚。
《破碎的生活》的渊源是作者另一本专著的亚马逊网站评论,评论者希望雅劳施写一部“你在德国城市的街道上能真正体验到”的历史。自2018年出版以来,本书获得了多项图书奖项,包括美国史密森尼学会2018年最佳历史图书奖。牛津大学历史教授尼古拉斯·斯塔加特(Nicolas Stargardt)表示:“康拉德·雅劳施运用高超的技巧,串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希特勒崛起之间出生的德国人的回忆……他的讲述充满历史的共鸣。”
ABOUT /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