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分散型城市”:城市生活的幸福悖论
从柏拉图对城邦的思考以来,尤其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化的席卷全球,城市与人、城市与幸福的关系,一直是从哲学到规划等诸多领域的一大课题。现代城市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和丰富的就业机会,但悖论是城里人未必比乡村人更幸福,大城市人也未必比小城市人更幸福。
与其说这是城市的原罪,不如说是当代的城市建设模板“分散型城市”有着严重的缺陷。为了克服这一传统模式的弊端,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到中国上海的一批全球城市已经切实行动起来。在“人民城市”理念的引导下,2021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为破解“幸福城市”这一全球问题贡献了新的中国方案、中国实践与中国智慧。
“分散型城市”:堵在路上的美国梦
分散型城市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城市地块开发模式。一座城市被分成了若干个功能单一的区域,比如住宅区、商业区和产业园区。住宅区的主体是配有大面积草坪的独栋住宅组成,住宅之间以蜿蜒的街道连接。商业区是购物综合体与大型连锁零售商店,周围是广阔的停车场,仿佛一片片黑色海域。这些名为“郊区”的地块之间,由宽阔的高速公路和主干道相连,这些道路又通往最近的市中心。
以分散型城市模式最盛行的美国为例,全国道路图就像一个人的血管,几条大动脉贯穿全身的各大交通枢纽,借助其他次级血管连接主要“脏器”(大城市),最后血液流入毛细血管,通达一个个郊区地块。换句话说,每个地块面前都是一条或多条断头路,地块中的人们无论是工作、购物还是送孩子上学,都不得不逆流而上,前往其他地块或市中心。
这就意味着人人都必须有车,车多则路窄;而就算修了新路,也必然会带动新郊区地块的建设,车流亦随之增多。这就是路越修越堵的悖论。除此之外,这种模式还有一种内在的矛盾:如果新建的郊区住宅、写字楼和购物中心商铺没有人接盘了,那该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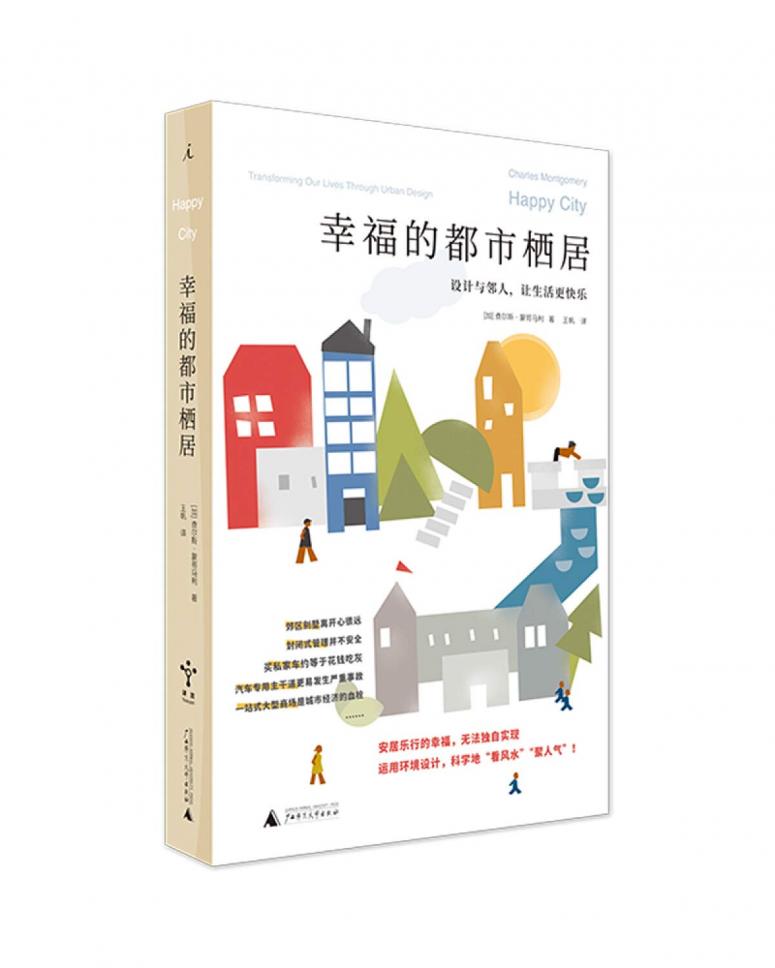
《幸福的都市栖居》
2007年次贷危机后的美国加州斯托克顿市,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全世界科技产业中心之一“硅谷”位于旧金山南部,斯托克顿市位于旧金山东部,相隔车程不到两小时,斯托克顿市于是成为了通勤上班族的理想场所。此地的建筑模式和遭遇都颇有代表性。
次贷危机过后,这里还不上房贷,房屋被银行收回的居民人数排名全美第二,仅次于曾经的汽车之都底特律。斯托克顿的房屋是美式大House的典型代表。一座废弃的高档豪宅,有能放下三台车的车库,门厅、饭厅、百叶窗一应俱全,可惜窗外的草坪疏于打理,已经枯黄成了稻草模样。过去几十年间,美国有四分之三的新建建筑都属于同一模式,这种房屋也成为了美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眼中“美国梦”的象征和实体化。
即便不考虑经济危机等“异常情况”,这种依赖通勤的生活依然称不上完满。加拿大著名记者查尔斯·蒙哥马利(Charles Montgomery)在《幸福的都市栖居》一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从斯托克顿的一处环路出发,最近的杂货店“优惠食物”在2英里(1英里约等于1.6公里)外,最近的健身房“形体健康俱乐部”在5英里外,最近的社区游泳池在6英里外,最近的公园在12英里外。这里距离旧金山市中心60英里,遇到塞车的话,往返就要4个小时。此外,通勤生活也意味着至少要多买一辆车,每个月还要承担高昂的油费。
时间和经济的硬性成本以外,分散型城市对居民的社会关系和心理健康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美国人近几十年来的社会支持网络在急剧缩小。1985年,美国人表示自己平均可以向3个人委托重要事项,而2004年时就降低到了2人。这一现象与分散型城市形态有着明显的关联。
虽然表面上看,人们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开车去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看望朋友,但事实上正如美国地理学家史蒂文·法伯(Steven Farber)所说:“城市不断扩张,我们越发难以进行社交互动。你如果住在一个大城市,除非就在市中心生活工作,不然就得付出巨大的社交代价。”
根据专攻幸福经济学的加拿大经济学家约翰·赫利韦尔(John Helliwell)的研究,人际关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高于收入,同时,信任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此基础上,他得出的结论是:卡尔加里、多伦多和温哥华是加拿大收入最高的三座城市,但也是最缺乏信任、最不幸福的三座城市,反而是遍布礁石的偏远省府圣约翰在幸福排行榜上位居前列。

加州斯托克顿,次贷危机后到处是等待出售的房子。
分散型城市不仅限于欧美发达国家,一个城市规划研究中经常举的争议案例是巴西首都巴西利亚(Brasília)。当时,巴西政府出于促进广袤内陆开发、克服贫民窟之类大城市病等因素,决定抛开老牌都市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到内地的高原建设新都。巴西利亚充分体现了有序、健康、平等的现代主义城市设计理念,规划简单而理性,功能分区明确,却抹杀了公共空间的内在社群感,为市民平添了心理压力。
公共生活与人的尺度
在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城市与幸福有过种种不同的关系,人们对两者的关系也有过深入的思考。
“集市”(agora)是任何一座典型古希腊城市的核心。虽然中文世界对agora的通用译法是“集市”,但它承担的绝不仅仅是货品交易的功能。除了摊位以外,议事厅、法院、神庙、祭坛、英雄雕像会围绕集市布置。
如果你来到的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很可能还会在集市外的廊柱下见到苏格拉底与市民交流哲学。“什么是幸福”正是他抛出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希腊人眼中,社会生活的必然载体和化身,就是城邦本身。人的幸福不止是财富、健康、权利等个人所有物,积极参与城邦公共生活也是必要的一环。正如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那无法在社会中生活的,或因能自给自足而不须在社会中生活的,不是野兽就是神明。”
事实上,现代共和主义哲人对当代市民社会的狭隘幸福观,也有过深刻的批判。在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看来,绝大多数现代市民的首要身份是“劳动动物”。与创造工具的工匠与投身公共生活的行动者不同,劳动动物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使用工具,从而加入生产—消费的循环。对劳动动物来说,他们追求的幸福寓于消耗与生产、劳作与休息之间的完美平衡。简单地说,终日劳作却饥肠辘辘的奴隶是不幸福的,但饱食终日而无所事事的领救济金者同样是不幸福的。
诚然,追求物欲并不是现代人或者城市人的专利,只是消费发达的现代城市生活凸显了这种追求的虚假性:既然人们能买到的消费品数量和质量越来越多,为什么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成比例地持续提高呢?对阿伦特来说,物质丰裕的现代城市生活遮蔽了生活的真相,同时也失去了超越的追求。在城市规划领域,这种思考的反映就是对社群性和参与性的强调。尽管城市规划中能达到的社群性上限还远远达不到哲人的设想,但几十年来的实践表明,即使要实现这样低水平的社群性也是困难重重。
除了社群性以外,健康与自由同样是幸福城市生活的关键要素。事实上,这两者正是分散型城市最初的核心吸引力所在。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一座座制造业城市在欧美各国拔地而起,这些城市的生活条件难称理想。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描绘了19世纪中叶伦敦工人聚居区的面貌:“在这里的一个大杂院中,正好在入口的地方,即在有顶的过道的尽头,就是一个没有门的厕所,非常脏,住户们出入都只有跨过一片满是大小便的臭气熏天的死水洼才行……下面紧靠着河的地方有几个制革厂,四周充满了动物腐烂的臭气。”

2021年10月31日,行人走过上海百禧公园“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人民城市”的广告灯箱。该公园的前身是货运铁路支线,后来变身为农贸市场和综合市场。如今,这里已成为一座独具特色的公园。
于是,一些现代改革家认为,幸福的秘诀是逃离城市。对于在乡下有大宅的英国贵族和富裕工厂主来说,这意味着如无必要,尽量不要进城。《魔戒》对工业城市艾辛格与乡村田园夏尔的描述,依然能看到这一思潮的影子。
进入20世纪后,在汽车工业大发展的促进下,“田园学派”创始人,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提出了“广亩城市”的理念。按照他的理想模型,一个面积为10平方公里的单元内,每名居民都会分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单元内设有工作、商业、休闲娱乐等完善的设施,出行完全依赖汽车。
讽刺的是,“广亩城市”的愿景从未实现,反倒是与其形似而神非的郊区模式成为主流。从大的空间布局来看,郊区模式同样是在原有城市中心周边建设了一个个庞大的独立地块。但每个地块内的功能单一,连最基本的生活工作需求都需要长距离驾车。自由被束缚在了路上,身心健康也因通勤、缺乏社交生活和绿色景观而受损。设计领域中有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大而无当的状况:不符合人的尺度。
幸福城市的实践
为了打破传统的分散型城市格局,全球诸多城市已经在各个层面行动了起来。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就是一个案例。恩里克·佩尼亚洛萨(Enrique Peñalosa)曾在1998年至2001年和2016年至2019年两度出任波哥大市长。20世纪末的波哥大是一个恐怖活动肆虐、遍布内战难民的城市,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初次上任的佩尼亚洛萨,没有开出全民富裕的虚幻支票,反而公开向“收入=幸福”的信条发出挑战。
在2006年联合国人居署举办的世界城市论坛上,佩尼亚洛萨表述了自己的理念:“我们对幸福有哪些需求?我们需要走路,就像鸟需要飞一样。我们需要他人的陪伴。我们需要美。我们需要接触大自然。最重要的是,不被排斥、孤立。我们还需要感到一定程度的平等。”
他在两届任期中践行了上述理念。他叫停了宏大的公路扩建计划,用省下来的预算修建自行车道、公园、步行广场、图书馆、学校和日托中心。他推出了“无车日”活动,有数十万名市民响应号召,步行、骑车或滑旱冰上班上学。
投资公共设施的宗旨是:既要客观的公平,也要让民众感受到公平。削减私家车道,增加快速公交系统(BRT),缩短了富人和穷人上班时间的差距。图书馆赋予了所有人读书和自我发展的机会。步行街营造出了一种微妙的温度感:无论贫富,所有人都走在同样的街道上。在这里,驾驶高档SUV的富人与挤着龟速公交的贫民,不再有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差距。
在打造人居城市的征途中,上海走在全中国的前列,始创于2015年的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以下简称“艺术季”)正是探索开拓、交流反思与展示成果的一个平台。2021年的艺术季主题是“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人民城市”。生活圈的目标,是让社区居民能够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获得基本社区服务,享受公共空间,实现社区就业。
新华社区的改造,就是一个卓越的案例。自民国时代开始,新华路成为上海的繁华地段,富有异域风情,域内有众多名人故居和花园洋房。但进入新世纪以来,空间资源有限、老旧建筑占比较大、老龄化程度高、基础保障不完善、精准配置缺位等老旧社区的弊病逐渐凸显。有鉴于此,新华社区大力挖掘利用不足的微空间,打造功能复合的公共空间,比如对居委会和物业用房进行改造,将尽可能多的空间开放给居民使用,同时提供相应的设施。针对老年居民较多的现状,社区建设了综合为老中心、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助餐点等设施,并结合智慧养老平台提升服务质量。归属感与认同感,同样是建设幸福社区的关键环节。为此,社区推出了社区导游活动,促进孩子们了解自己生活的地方,同时鼓励市民参与社区建设与管理。这些举措从微观层面对幸福都市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尽管分散型城市对个人幸福、城市财政和生态环境都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但我们仍然不惜投入自己的时间、金钱与活力。这种生活方式成为了一些人难以逃离的牢笼,也成为了另一些人难以企及的理想,即使是反对分散型城市的人也往往会归咎于社会形势、城市规划失误、资本作恶等外在因素。但是,生活的变化终究要落实到人自身的改变上,而这可能意味着态度与生活方式的转向。
正如《幸福的都市栖居》一书的末尾所言:“当我们选择自己要如何生活、在哪生活的时候……当我们在个人生活中追求幸福都市并推动城市与我们一同改变的时候,当我们要活出自己的新天地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为幸福都市添砖加瓦。”


